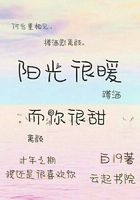辗转无眠,索性起身来到窗边,暮色沉沉泼墨天际泛着青色,疏薄的云丝闪过月亮娇羞的脸,她坐在窗边扶腮叹息:“敦煌郡?千里迢迢,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到那……”她立马从包袱里掏出那只于阗玉笛,寒冰曾对她说过吐谷浑地处西北,那里有流金沙漠和茫茫戈壁,它同突厥相连,有着中原不一样的景致。
他曾说过,有朝一日想去沙鸣山上看日出,到孔雀河沿岸看日落,那里有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这里已无留恋之处,莫不如流浪他乡,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不过,若欲去吐谷浑,总要过了敦煌郡和玉门关才好,将整个西域游历一番也算是完成了寒冰生前的一个心愿。
一个月之后,萨玉儿已经过了渭州,再过一个月估计便可进敦煌郡境内了,她坐在十里长亭内歇脚,马儿被拴在不远处的树干旁,晌午过后的空气凝结着闷热之气,像蒸笼一样叫人难以喘息,她斜靠在亭柱上喝水,汗水早已浸湿衣衫,这燥热的天气怕是要下雨了。
这时,从东边浩浩荡荡走过来一支商队,虽是中原人的打扮,可瞧着长相就不难看出是胡人。萨玉儿装作漫不经心的模样啃着馒头,可目光却始终在那些人的身上打转。
此支商队约莫十七八人,带着二十匹成马,还跟着两匹小马,从他们的装备上瞧去却看不出到底是做何生意。十几个人进了亭子,本是萧条略显惆怅的地方瞬间热闹起来。
商队之中大部分尽是胡人,说着萨玉儿完全听不懂的言语,其中有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老头凑过来对她笑道:“小伙子一个人出门啊?”说着老头从腰间拿出旱烟袋,坐在自己身旁吧嗒吧嗒抽了几口,三角小眼犀利闪光,形容枯槁可气质难掩,一看便知绝非平庸之辈。
萨玉儿连忙将口里的馒头吞下去,傻笑着粗声粗气道:“是啊,老人家,您是?”
“哦,我是这队伍的向导,那个是队长。”他随手一指,目光落在远处仰头大口喝酒的男子,侧面瞧着那人该是二十七八岁的模样,谈不上俊朗潇洒,可身材伟岸挺拔,倒也是风度翩翩,气质非凡。
那人转过身走到老者和萨玉儿面前道:“我们大概还要多久的脚程?”好一口流利的中原话,不禁叫萨玉儿侧目窥视,这个男子不知在中原呆了多少年,竟把中原话讲得醇正地道,好在他高鼻阔嘴,浓眉遂眼,一看便是胡人血统,否则单说这几句话也足矣以假乱真了。
“要是赶着走,大概也要个把月的时日才能到敦煌郡,过了玉门关也要走好一阵子呢,急不得。”老者在地上磕磕烟袋后收起来又对萨玉儿道:“小哥是要去哪儿?”
“我……我要去吐谷浑。”她藏起心底的好奇和不安道,这时天空一声闷雷传来,商队的人急忙将马匹上的货物卸下来搬到亭子里避雨。少顷后,豆大的雨滴坠落,好似无数珍珠坠入玉盘之内,虽是嘈杂可若细听上去倒也悦耳。
“哦,吐谷浑。”老者点头,又似是想起什么来说:“可听说近一两年且末和鄯善不太平,你一个人去那可是做什么生意吗?”
说着,老者上下打量她一番,目光透露出狐疑,这时商队的几个年轻男子也凑过来,用蹩脚的中原话问萨玉儿:“中原……不好?西域……去……何……”
老者不禁摇头大笑望着一脸茫然的萨玉儿道:“他是想问你,中原不好吗?为何要去西域?”
萨玉儿低头笑道:“去寻人。”
大家纷纷点头,原来如此。萨玉儿第一次接触胡人,以前只听说他们蛮不讲理,凶狠残暴,可如今亲身接触也并非如此,倒也平易近人,尤其是其中的几个年轻小伙子,笑容明朗憨态可掬,只有那个被称为队长的人,只是一个人静坐在远处望着乌云霭霭的天空,听着雨声发呆,他的眉宇中是抹说不清楚的哀伤惆怅,好像那冰冷的雨丝皆落入他的眼底心头,愁云惨雾尽是挥之不去。
雨歇后,天空中悬挂出一道彩虹,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如今被雨水洗刷一番过后的驿道两个尽是明亮闪光的翠绿枝叶,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野花也都在微风中摇头晃脑,展尽笑颜。
老者带着商队继续前行,萨玉儿也骑上马赶路。既是顺路,刚刚攀谈之时又算是相识了,所以一路上她也就不愁没伴前行,原来那老者是敦煌郡人士,人称老马,其实他本不姓马,而姓胡,只是大家都尊他为长者,而且见多识广,誉为老马识途。老马家自汉武帝至今祖祖辈辈都是西域商队向导,他们对整个中原地势了如指掌,进了西域也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畅通无阻。
那个队长,大家都尊称他为博公子,具体姓甚名谁不可得知,萨玉儿的泼皮性格太适合这种迁徙生活了,沿路风光无限,还能从老马口中听到许多新鲜有趣的故事,沿途休息的时候,他就会给大家伙讲讲以前做向导时的新鲜事,孔雀河仙女,胡杨林秘洞,还有白龙堆的死亡传说……那些带有西域特有神秘色彩的故事,让萨玉儿听得不禁痴迷。
一次讲到鄯善女巫的时候,萨玉儿听得如痴如醉,相传许多年前鄯善曾有一位貌美如仙的女子,名曰索菲雅,是古楼兰时的一个女巫后人,在楼兰同匈奴的一场战役中,她舍身取义,从十余丈高的佛塔上坠落,誓与正义和光明共存亡。后来,鄯善国人都对她顶礼膜拜,为其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太阳古墓,希望她能从此与日同升,永世光辉。
萨玉儿双手撑腮,两目泛光,面露傻笑道:“若我也是那样的奇女子,该有多好?正义凛然……”话还未说完,博公子已经走过来打断她的话:“这辈子恐怕是不行了。”说着,他上下打量萨玉儿一番,眼中尽是玩味之意,这一路上他虽然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可是言语中却又不失气度和礼节,想必也是出身望族受过良好教育的。
萨玉儿不解低头望了一眼如今的男儿装扮不禁哑然失笑:“是啊,怕是……不行了。”
“今晚恐怕要露宿野外了。”老马一边帮着大伙搬东西一边念叨着。
萨玉儿环顾四周,一片漆黑的野地时而传来狼嚎的声音,她不由得在心底打个寒颤:“好在和这么多人混在一处,否则自己这一路可不知要怎么是好呢。”心底想着便觉得安稳了许多,于是也赶紧前去帮忙,好在一路上天气不错,若遇到梅雨时节这一袋袋的茶叶带回去时,恐怕早就泡开成茶水了。
卸好货物后,她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水,几个人去喂马,几个人燃篝火准备做晚餐。萨玉儿拿出水囊抬头喝了一大口,冰凉感让整个人顿时神清气爽。
“给你。”她本能地接住眼前飞过来的东西,定睛一望原来是个果子,博公子坐在她身旁笑道:“跟着商队走是不是很辛苦?”
“很有趣。”她笑道,把果子往身上胡乱蹭蹭就往嘴里塞。
“从未听说过你要寻什么人。”博公子侧头望着她含笑道。
萨玉儿心底有些紧张,尴尬笑着:“是位故交,多年未见不知如今过得如何了。”
他点头不语,枕着手臂躺下来,透过头顶树梢露出半轮残月和点点星辰:“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萨玉儿也学着他的模样躺下来,只是嘴里衔着一个小草,瞥眼瞧瞧身旁的博公子笑道:“既是有缘相识,是否知道名字又有何妨,你随便叫什么都好,只要不是阿猫阿狗我倒是都能接受的。”
博公子不禁失声笑道:“瞧你那么喜欢鄯善女巫的故事,就叫你索菲雅好了。”
萨玉儿正欲满心欢喜接纳,又转瞬觉得哪里不妥,她腾地坐直身子不满道:“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叫这个?叫我寒冰好了。”
博公子意味深长地笑望着她一刻后幽幽道:“那好吧。”
“你的家在哪里?”萨玉儿想扭转这种有些尴尬的局面,随便找个话题来说。
“在北面。”
“我还以为在西域。”她歪着脑袋又问:“你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博公子面色淡然笑道:“早点睡吧。”言毕后,他便转过身不再理会萨玉儿。
她无奈只好再次躺下来,这种一天为盖地为庐的睡法着实辛苦,身下的小石砂砾总是咯得身上到处都疼,待周围皆是平稳呼吸,只留三个人轮番守夜的时候,她依旧辗转反侧,突然有些怀念弘圣宫的床榻锦被,人啊,总是在经历磨难的时候才会怀念珍惜过去的美好。还不等她感叹完人生,睡意早已袭来,也顾不了那么多,眼皮如千斤重一般垂了下去。
睡梦中似是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至耳畔:“玉儿……玉儿……”
她想睁开眼睛去看看是谁这么没有眼力价,自己都累成这样困成这样,怎么还忍心叫醒她呢?她固执地想着,眼睛就像被黏在一处,用尽浑身解数都无法睁开。朦胧中仿佛有嘈杂的说话声传来,只是听得极不真切。
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耀大地的时候,萨玉儿正翻身蹬腿,无比欢快地伸着懒腰。她打着哈欠睁开惺忪睡眼,心底狐疑着此刻是什么时辰了?
还未想清楚,朦胧起身时才发现商队的人早就开始整顿行囊,只有她一个人起得最迟,真是丢人。
她堆满笑意小跑到老马身旁,他坐在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抽着烟袋,漫不经心问她:“你是从长安来的?”
“雍州。”她也故作漫不经心地回答,长安的一切都如一场梦一样留在了过去,她不想再提及。
老马点点头不再言语,目光却闪过一抹难以琢磨的光。车马整顿好之后商队再次踏上征程,萨玉儿骑马同博公子并肩前行,他淡漠的目光似是世间万物都难以入他的眼一般,她反复思量一夜的话终于忍不住问出口:“若我从敦煌郡去吐谷浑,可是要途经突厥?”
他斜眼瞥她,轻笑:“怎么?不想去突厥?”
“没去过。”她皱皱鼻子又说:“不过听说突厥人有些凶狠,想避开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