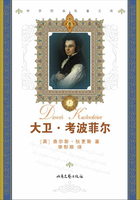白分局长在实施第一个政绩目标问题上与分局党委书记古大立发生了冲突。
白金水就职演说的偏激,意在给古大立敲警钟,并不想学古大立一当上代理分局长就开始大换干部。他想到的是稳定军心,不要一开始就犯众怒,自己给自己找被动。但有两个人必须首先安排。一个是他从中南站带过来的站办主任范明亮.一个是古大立代理分局长时的秘书虞虎彪。
古大立的提议是:副科级秘书虞虎彪任分局办公室主任;原中南站办主任范明亮任白金水秘书。
白金水的意见是虞虎彪只能任办公室副主任,不能让他一步到位,一步到位容易使其产生骄傲情绪,反倒工作做不好;范明亮任古大立秘书。
这样一来两人意见便发生了分歧。古大立心里在想:你白金水的算盘打得蛮精,把你带来的心腹安插到我的身边,无疑是要我踩着地雷过日子,亏他想得出,说得出口。而白金水也在想:你古大立也太精明了,不把你的秘书带到党委办去,反倒要留在分局办。而且还要当主任,不也同样是要我踩着地雷过日子么?白金水与古大立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虞虎彪任分局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办公室工作;中南站办主任范明亮任古大立秘书。
白金水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他自然要烧古大立的痛处。去年,古大立代理分局长时,没有完成运输计划,原因很简单,就是未能解决阴阳山弯道陡坡路段卡脖子口难题。他白金水要把解决阴阳山卡脖子口难题做为第一个政绩目标,也是向古大立挑战的第一发重型炮弹。阴阳山从地理位置上讲,它是中原与中南的南北分界线。古人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故名阴阳山。大山横断形成南北分水岭,一山南北两个天地。因此,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船到阴阳止(分水岭),马到阴阳死(马只能生活在北方),人到阴阳打摆子(适应不了两种气候的急剧变化),火车开到阴阳绕圈子。”当年铁路设计者们也提出过打通阴阳山近70公里的隧道,但当时在技术上达不到长隧道的施工能力,且工程相当大,只好沿阴阳山绕了一个80公里的大圈。古大立在实施铁道“多拉快跑”计划时,也确实做了一番努力,就阴阳山路段从运能技术上讲,完全达到了设计饱和能力运行,达到了极限。古大立认为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遗憾,是技术能力达不到,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及的。白金水认为那是书呆子的哲学,什么设计饱和能力,那是用一台机车牵引能力来考虑的。一台机车能拉动40辆车,用两台机车拉60辆,一台在前面拉,一台在后面顶,仅用几台机车就轻而易举的解决卡脖子路段的运能问题。白金水心里清楚,这个方案必须不声不响的先实施,后再拿到党政联席会上去通过贯彻执行。如先拿到会上讨论,古大立就会坚决反对,说出一大堆技术上安全上的问题,叫人听起来尽是道理,不好表态。先去实施,既成事实,又确实可行,在事实面前谁也没话说。他要用事实做给古大立看,做给局机关的干部们看,证明我白金水有能力解决古大立解决不了的问题,叫他们看看我白金水不是白吃干饭的主儿。
白金水带着虞虎彪来到阴阳机务段,找到老段长刘璞笏,将双机车牵引解决卡脖子口路段运能问题,实施多拉快跑方案交给刘璞笏执行。刘璞笏还未听完,脑袋晃得像个波浪鼓,连连摆手说:
“不行,不行!我五十多岁了,在铁路干了三十多年,没见过两台机车拉一列火车的事。再者说,多大马力拉多少吨位的车辆,什么路段行驶多高速度,这种基本技术常识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跑机务的大车有句行话,叫做拉万吨车,行万里路,一点也不差。差一点也不行。这种以两台机车牵顶列车的做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几十个车在如此大的坡道上行驶,万一爬不上去,滑下来那是要翻车死人的,这个险冒不得呀,我的分局长大人。”
白金水越听越长火,心里在怒骂:“他妈的乌龟王八蛋,就你们懂科学,别人就是科盲,胆小如鼠干不成大事,都他妈的小人见识!”白金水尽管怒火中烧,终究不好骂出口,一方面他要表现领导者的风度,不失大将豪气;另一方面,他有求于刘璞笏,去实践他的双机车牵引方案,不能一开始就搞成僵局,去计较那区区小事,而坏了大事。想到这儿,白金水便强压怒火,强装着笑脸,用商量的口气说:“老刘呀,你看这样好么,先按我的办法,你替我做个试验,用数据说话,用实践说话,行与不行得有个具体的说法。也好向局里交差,你看是不是这个道。”
“哎呀,我的分局长大人,这明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还用得去试验么?硬要去试,这不等于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因小失大,这种玩火的冒险傻事我是不会去做的。你另请高明吧。”刘璞笏回答得很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下白金水真的忍不住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另请高明”的话,这不是公开的跟他白分局长叫板吗?如此目无领导,这不比事情本身更具危险性吗?不按他的指示办,本身就不允许,公开的叫板,他白金水岂能容忍?白金水像一头急怒了雄狮,一巴掌猛击在刘璞笏的办公桌上,击碎了一块玻璃,怒吼着:
“占着茅坑不屙屎,我要搬掉你这块又臭又硬的老石头!”
白金水转过脸对阴阳机务段党委书记竺焱焐说:“请问贵段有比刘璞笏能干的么?”
竺焱焐怎么好在这种场合回答这种叫人难堪的问题呢,但又不能不开口说话,说什么呢?说什么都得罪人,不是得罪上级就是得罪同级,只好答非所问地说:
“白分局长,您先消消气,事情都得慢慢来,,总会找到好办法的,您先到我办公室去,我慢慢向您汇报。”
竺焱焐一边说,一边拉起白金水就往办公室跑。竺焱焐既给白分局长找了个打破僵局的台阶,又给自己寻找了一个逃避尴尬的机会,心里自然得意。
白金水在心里已下了决心,要换掉老朽刘璞笏,便与竺焱焐谈开了:“老竺呀,你是书记,是管干部的,刘璞笏是不能在段长位置干了。你了解阴阳机务段的情况,你看哪个去接替段长位置最好,你挑选个人给我。”
“白分局长,您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呀。当官,谁都想当,可是您要的这个官太烫手,没人敢拿得动呀!”竺焱焐右手摸着下巴,放慢口吻,略有所思的接着说:“三个副段长中,一个是管运转的范学鑫,年龄虽然只有四十出头,倒是个合适的人选。虽然与刘璞笏常常在有些观点上有分歧,性格要强,人光明磊落,他最反对落井下石之人。在刘璞笏这么不体面的下台之时,他是绝对不会去接段长那个位置的,这点我是可以打保票的。再一个是管后勤的老于头,去年就提出要退二线。考虑到他是老副段长,人老实本份,班子都同意他再干一年,他来接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还有一个嘛,是去年才提拔上来学习锻炼的董昕。他是大学生,是重点培养的青年一代,可眼下他黄口未掉,怎能挑起如此重担,就是我也坚决反对他现在就接班。”竺焱焐这样说实质上是在为刘璞笏开脱,言外之意非刘璞笏不可。
“这么说朝中无人罗?你找不出人选,那就由我乱点鸳鸯谱了,点到谁是谁?”白金水不耐烦地说。
白金水带着虞虎彪来到运转车间派班室,靠边坐在不起眼的位置上,仔细地观察调度员与司机之间的派班经过。白金水坐了一整天,未能点中意中人。快到下班吃饭时分,一个三十未出头的司机,接受调度员派班任务时,主动反问调度员关于行程、任务、安全三个方面的问题,引起白金水的注意。从外表上看,一米七多的个子,脸上挂着几分稚气,却又深藏着稳重老练。从性格上看,是个急性子,急性子好,办事效率高,而且他还能够主动反问调度员的问题,说明他有高度的责任心,至少说不是马大哈式的角色,而是很有心计的人。用人就要用急性加责任的人。白金水抓住时机,主动上前与之交谈起来。
“请问尊姓大名?”
“南线3564机车司机关海焘。您是……”
“他是白分……”虞虎彪替白金水作答,被白金水及时制止。
“你先不要问我是谁,你先老实告诉我,你想不想当段长。”白金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这位老师傅开什么高级玩笑,开火车的司机与管司机开火车的段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事,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呢?我说你是发高烧说胡话,还是吃错药了,要不,怎么这么没谱的取笑人呢?”关海焘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
“我没有取笑你,说的是真的,我是分局长白金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白金水说得有板有眼,严肃认真。
“你别拿分局长吓唬人,这年头我最清楚,说了算的不说,说了不算的乱说。真要是分局长来了,他才不说这话呢。再者说,想不想当段长,那是想的事吗?这个玩笑您老开大了,没人听得懂,哪儿凉快你上哪儿去吧,我要出乘了,没功夫听你胡言乱语。”关海焘说完转身就要走。
白金水抢先一步,拦住关海焘说:
“慢着,今天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把你留下。调度员!你把关大车换个班,就说分局长把他带走了。”
白金水在说话的当儿,虞虎彪马上将分局长白金水的工作证递给值班调度员看,调度员照白金水的吩咐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