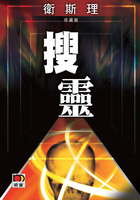1
推开门,见阿佩脸色煞白坐在他的竹床上,路北平大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开口问话的却不是他,而是阿佩,四眼!你这身上……出什么事了?
路北平脸上、身上划开了一道道血痕口子,慌慌张张说道:我撞邪了……
撞邪?阿佩听若一抖,无阴功,又撞了什么邪?
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他惊问,阿佩,那边山出什么事了吗?
两人一时都大喘着气,接不上话来。路北平回身放下挎包,一件件掏出包里的东西——油盐酱醋、灯油火水,极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又猫身到锅灶里舀了一碗水,给阿佩递过去,说:先喝口水,我们都慢慢讲……
季节在悄悄改变着巴灶山的风景。秋日天凉,正是橡胶出胶水的高产时段。山下台风扫刮之后幸存的那些育龄胶树们,便成了向革命“献礼”的乳母——那年月时兴讲“献礼”,“劳动节”、“党生日”、“国庆节”要“献礼”,“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基本路线教育”也要“献礼”。胶树少了,“献礼”多了,牛和橡胶忽然形成了一条奇特的生物链:牛栏里的出肥数、施肥数,成了全队胶水产量的指望。往日是一两个月村里才派人进山来出一次牛肥,如今是一两周就要一次。连一向听话紧跟的队长都在抱怨:这样“等鸡下蛋”,无异于“杀鸡取卵”。更不必说,“莺歌燕舞”的“形势教育”之后,风灾里一度停摆的师团开荒大会战又拉开了“大干快上”的阵势,环绕巴灶山的四山五岭,早已是一片鼓角连营、旌旗蔽天了。如今,“守着牛屁股榨屎”成了路北平的日常功课——牛群要吃草多才能有屎,牛栏里要垫草厚才能有肥。偌大的巴灶山里,路北平日日轰着牛群追着草色草情跑,肩头还得时时担着两担草山,夜夜忙着为牛们铺草垫栏。往日那种悠闲写意的放牛郎读书生活,变得有点咄咄逼人,简直让他喘不过气来了。
逼人之处还在于,出肥次数一多,队长带人入山的机会就多。山里山外的两个世界,常常便要两相搅缠了。
首先搅进来的,是金骨头。本来这些个月来,路北平早把那个什么“种私烟”的话题淡忘了,也一直没有在意,没有了“私烟”,八哥、阿佩他们的水烟筒里都拿的什么打发——记得阿木说过,有时他们就把木瓜叶晒干,切成烟丝来抽的。却没想到,这一阵子赶牛车入山走得勤,算盘很精的金骨头便又开始悄悄从山外为八哥他们贩卖烟丝、日用品——那年头,烟卷、肥皂、草纸都要凭票证供应,金骨头便让八哥他们将开好的木板木料送到山外的固定地点,他再为他们换一点烟丝、肥皂之类的日用品进山。这本来是山里各种流散户日常的生存之道,金骨头不过就是想从中赚一点小利罢了,可在那个年头,闹不好就是“犯天条”的罪名。金骨头虽然一直瞒着路北平和这几个“白沙流散户”发生关系,一来一往,似乎就从中看出阿佩和路北平之间的一点什么蹊跷端倪来了。总想拿捏别人的把柄,又生怕成了拿捏在别人手里的把柄,于是就更加使劲嗅闻、记录身边一切人的一切可能的把柄——这是那个年头派给金骨头的专长。天不巧地不巧,金骨头在寨子里边出入又被路北平撞见过一次,疑心加上心虚,就使他成为日后那一连串风波的呼风唤雨人。
……用凉水抹了一把脸,平息下心情,路北平已经猜透了阿佩的几分来意,问道:是不是金骨头,今天进山来过?
阿佩点点头,叹了口气,却忙着问:四眼,你先讲,你今天又撞的什么邪了?
金骨头不算什么东西,路北平拂拂手,沉声说,阿佩,我讲出来你别慌,是撞见队长……
什么队长?哪个队长?
就是山下,我们村里的支书兼队长。
支书队长?
我告诉过你的,就是他们一家,硬硬派给我的这个“阴府女婿”……
四眼四眼!阿佩叫了起来,找你来,就是为着这件阴邪事呀!
两人停顿之间,听得门外的流水声,哗啦哗啦狂响起来。
对于路北平,金骨头或许不足虑,但是,这些日子以来,队长——这位“阴府岳父”的频频眷顾,就不能不让路北平时时拎着一颗心了。
笑容很多,话也很多。阿路长阿路短的,赞牛群放养得好,赞牛肥出得多。讲过革命生产人类贡献的套话,又问对招工招生有什么想法,扎根表忠书交给班长了没有?阿彩总夸你是广州仔里最吃得了苦的,她是怪怨我这个队长让你吃大苦了呢!阿彩说她看见你常常赶着牛群往十二号段那边走,那边夏天的草是旺呀,现在入秋了怎么样?阿路你山里的日子难过,山外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山里头闷了乏了你可以过山去找那几个白沙流散户搭搭话,山外头,我有时是连一个搭得上话的人都找不着哇……
他现在,成了那个“搭得上话”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一句话搭上过——阿娴,队长和他,似乎都在小心翼翼绕过那一层似有若无的“亲戚关系”;倒是常常有意无意地搭上——阿彩,队长的深深浅浅的话题,总是故意盘桓着离不开这个——阿彩。
这天的后半日,路北平借着牛吃食的空隙,回村里供销社去置办一点日常物件——糖票、火水票、肥皂票什么的,不用就要过期了。回程时想抄小路穿过溪谷,忽然听见隔岸胶林里传来一阵阵嬉戏的喘息声。收住步子,他认出了这是阿彩割胶的那个林段。透过木麻黄防风林边的树丛,他陡然一惊:他看见赤条条的队长,和光着半个身子的阿彩,搂滚在一起。
尽管村里时时传闻,阿彩(或者别的谁谁)和好多男人都打过胎、生过“野仔”;夜半割胶的林段,其实是众多异梦鸳鸯们成全好事的温床。但是,这种时候,队长与阿彩的私情,又绝非只是增加一段胶林艳史这么简单了。莫非是阿彩的日常碎嘴泄露了什么底牌,生怕队长追逼,她便把那件“姣婆蓝”像着了火的蒲扇一样扔给他,然后才有队长的染指,意图以裤头下的方寸,为阿娴的谜团把关封门?抑或是,平日言词放荡的阿彩本来就和队长有私,私情越深,那件“姣婆蓝”就越成为夹在两人中间的火媒头,阿彩才迫不及待像推卸责任一样地把“姣婆蓝”扔给他,从此撇清与自己的关联?总之,一时间他明白过来:阿彩那天匆匆塞给他那件“姣婆蓝”以后,为什么从此总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远远避着他。男女性事,如今也可以成为另一种封口的利器了。
压抑着的浪声秽语,浮滚在向晚胶林的一片寂静之中。
他生怕被两人认出,从原路悄然退出,越想越慌,便穿过密匝匝的箭竹刺藤,抄小路疯跑回来。
——唉,我还当是什么事呢!听罢路北平慌慌说完撞见队长和阿彩的经过,阿佩却咯咯笑了起来,四眼,你有眼镜隔着,难道还怕生挑针眼?撞这种邪,有人还叫作有眼福呢!
不不,阿佩你不知……
阿佩却又敛住笑,正色道:可是这一回,四眼,金骨头真是把事情惹大了!无阴功啊……
路北平咬咬唇角,把已经溜到嘴边的关于“姣婆蓝”的话题咽了回去。骂道:丢,金骨头,他还敢惹什么事?
你真不知轻重?阿佩扳着他的肩膀,话音哆嗦着,他……他把你入山来的底底细细全兜给八哥了!什么时候结的鬼婚,怎样做的队长家的阴府女婿……
他不是已经告发过一回了么?路北平仍旧不屑,八哥还听他炒这种冷饭?
唉呀!你怎么听不明!阿佩急了,上回一句“身上不干净”,就惹出了那么大场风波,那是八哥以为,你只是在外头犯了什么事贬落的深山;你是知道八哥的阴阳忌讳有几多几重的!现如今,金骨头向他撩起这个无阴功的话头,那才真正叫做撞大邪了!
路北平似乎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暗暗庆幸自己刚才敏感,及时为“姣婆蓝”收住了嘴。
阿佩拍着胸脯:偏偏阿木今日入山,又……你过山来就知道了——你今晚,一定要跟我过山走一趟……阿佩有点慌不择言。
路北平狐疑起来:为什么是今晚?
阿佩声音里忽然带着哭腔:四眼四眼,你是真不明真不懂呵?
路北平定定瞅着她,万万没想到,等待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如此骇人的答案。
四眼,我有了……阿佩眼里泪光盈盈,忽然捂住脸,有……两三个月了……
一瞬间,路北平已经雷击一般明白过来了,退一步,瞪着阿佩似乎隐隐隆起的肚腹,忽然猛力摇着阿佩肩头:你说什么?!你说的什么呀?!
……上回我说装病,其实我就知道,我又不想让你知……阿佩忽然破涕一笑,我讲过要给你生一个仔仔的,我讲过……
别讲了!别讲了!路北平暴怒地打断她,像一头失了缰的骡马,在棚屋里冲来撞去。
阿佩收住泪,冷冷盯着他,冲着他横走的背影,喃喃道:是我要生仔,又不是你们生……我知道你们男人……她忽然扑上去搂住他,嘤嘤哭着,四眼你今晚一定要陪我过山去,八哥他,他他他要逼我打掉我们这个仔仔!……
阿佩伏在他的肩头,呜呜呜放声号哭起来。
路北平挣脱了她的手,颓然跌坐在床沿上。
他忽然把脸仰向晦暗的棚顶,我丢戳你老母烂臭海呀!……
时间是一张网。凛凛然地向他们围拢过来了。
2
到水头迎住他们的,是阿秋和阿扁。
阿秋一脸忧郁,压低声对路北平说:你不要入屋,跟我来。
天已经黑齐。抬起头,初升的新月像是一盏灭灯,投照着眼前这一副似曾相识的情景:那张粗木饭案又像那晚斗鸡一样,搬到荔枝木下那片地场上来了。合了窝的那一大群鸡仔又簇拥着在案下抢食,鸡母鸡公,各安其命,显然已经和平共处多时。可是今晚的阵势非同寻常:老老嫩嫩,所有人都围在饭案边喝粥,一声不响。一大锅菜粥显然是阿佩下山以前就煮好了的,八哥和阿木这时候已经喝完了,见他们过来,用筷子往一块原木上点了点,示意路北平坐下。阿秋和阿扁便都回到各自的位子上,埋头把刚才碗里的剩粥喝完。阿佩却径自折回屋,一忽儿提着一盏油灯走过来,强撑着笑意,仍像往日一样悠悠说道:四眼,你先喝粥。
八哥也瓮声瓮气说道:先吃,吃完再讲。
灯挑到了树丫上,那个平日用马钉固定在荔枝木上锯木开板的粗木架,在月光下拖着黑魆魆一若绞刑架似的影子,更平添了案桌前这种等待审判一般的气氛。他这时才觉着腹空如鼓,也不多想,低头呼噜噜的,几口就把一大海碗的菜粥喝光。
阿扁想帮他再添一碗,被八哥寒碜碜的目光止住了。
阿木和阿秋从马灯上借过火,咕噜咕噜在一边抽起水烟筒来。
肚里有了点荤素垫底,路北平觉得自己不该像一只等宰的死鸡,况且他也略略知道八哥的脾性,便平静地开丁腔:八哥,听说你找我过来有事?有话你就讲吧。
八哥板着脸,忽然闭上眼睛,像是在压抑着胸腔顶上来的一口气,缓缓再睁开眼,说:阿木,你把那个木桶拉过来,给四眼看看。
阿木走过去,从树下拎过来一个快要松箍的大木桶,嘟囔着说:四眼你自己看吧。
月影下,那个木桶张着黑洞洞的破口。路北平满腹疑惑往里面望了望,看不出个什么名堂,也不知那破桶里藏着什么要命的东西,心上便有点发紧。
八哥几步走过去,一脚踢翻了木桶,里面的细碎家什儿哗地倾倒在地上。路北平第一眼没看出个究竟,再一定神,他愕然退了一步,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倏地抖麻开来——那是一条蛇,不不,是一片巨大的蜕下来的灰黑蛇皮,蜷曲起比水桶还要粗的虚圆,松松软软地摊了一地!
先是几个猴儿头,吓得哇哇乱叫起来。
阿木撞邪了。阿佩在一旁插话,用着这个热词,他连续两日入山,都撞见住在碗角里头的神明……
又轮得上你多嘴!八哥喝断她,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你懂得多少?八哥顿着水烟筒,阿木是撞的神明,有幸撞见那个龙神移位……
我没有撞见,我是听见……阿木呜噜呜噜应着,话音含混:一架山打雷公一样,几座山林都好似发冷打摆子,吓得我……今早入山,就见林木里头,地上树上,拖着这蜕下的龙鳞,我见到就拜呀……
黑地上,那硕大的纹鳞,耀着幽幽的荧光。
不是阿木撞邪,是我们一山人都撞邪了!八哥转向了路北平,直逼逼就进入了正题:古人讲,麒麟出,天下福。我们一进巴灶山就听人讲,巴灶的龙神蛇怪万万不可惊动,它一现身,人畜就有祸!那一年端午,阿扁他阿大入山,见到它的蜕衣不知拜祭,第二天就被木方压扁了,头哥是在代我们受祸呀,头哥……八哥合起巴掌往黑墨墨的碗口方向拜了拜,冷不丁一个转身,喝道:四眼,今晚在神明面前,在头哥的神位面前,我要你,站出来!
路北平望了阿佩一眼,真的站了起来。
好!八哥狠狠说道,四眼,你敢堂堂正正站出来就好!阿木,你上去——
阿木嗖地就跳起身来,二话不说走过来,猛地一发力,将路北平两只胳膊往后一拧、一收、一扳,再勾住脖子往下一压——
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路北平拼力挣扎着,可是身、肩、腕、臂,每一个部位都像被铁固定了似的,动弹不得。
阿木毕竟是阿木,简直是个铁铸金刚。路北平惊奇的是,没有一个人显出慌恐的神情——连同阿佩、阿秋和阿扁,一个个都是木着头,沉着脸,仿佛一切早已排定说妥。
八哥走到路北平面前,拱了拱手,仍旧是一脸严峻:四眼,难为你了,是你,难为我们了。今晚要你受一点皮肉之痛。我要叫阿木先将你绑到树上,再和你有道理好讲。
你们……路北平把求援的目光投向阿佩,八哥也把凛凛的目光逼向阿佩,阿佩低下了头。路北平便再不反抗,顺着阿木的力推走到荔枝木下,两只手被他背着绑到了那个木架的粗柱上。站定,他极力平息着内心的惊悸,静静等着听八哥的“道理”。
月光把那张饭案耀成一片惨白。树底下的斑驳月光沉静下来,雾一样的,拢住了他,也拢住了八哥。
八哥望着他,默默点点头:四眼,你总算是有担当……忽然就把声调提高了八度:上次就想赶你走,原来我没有讲错!你想想,自从你落脚到这山边头,出了几多阴阳古怪?要不是金骨头今日向我们交底,我们这一山人,就真真要被你招引来的阴邪阴毒害惨了!害死了——呸呸!他忽然想到“死”的忌讳,连忙抹了抹嘴,你你你,为什么要一直诓瞒我们?四眼你讲!
路北平咬着嘴角,他知道他无话可讲。
——臭脚!哼,好听!为了臭脚!八哥马上发觉这个不雅的话题打乱了他说话的气氛,连忙把头脸扭向阿佩,你你你——你还有脸笑?
阿佩只是低头抿了抿嘴。这边,路北平却忍不住,嘿嘿笑出了声。
我丢!这笑声,彻底把八哥激怒了。他骂着,一俯身嗖地从饭案后面抽出一根藤鞭来——是用几支细簕竹砸酥砸扁了扭结起来的鞭子,八哥下午亲手打造的利器,——啪!一声狠抽,鞭子落在饭案上,发出裂帛一般的锐响,惊得蜞仔虱仔哭了起来。八哥不理会,抖着鞭子走到路北平面前,切齿说道:四眼你笑?我怕你笑不出声来了!如今所有古怪都天光大白了,那个跑进碗角背来烧冥纸的,那块带入山来的死鬼木头碑,都是为着你!——做了鬼女婿,瞒着骗着你撞入这边山来,你知道你给这碗角背,带来几多阴损!我们头哥留下的这份家业,眼睁睁就要被你克掉了!他忽然长叹一声,我们这些流散户命贱命薄哪,我们谁也冲犯不起。我们避官怕官,才跑出来做流散,可是官家官人就是钻肠破肚也要追着你——队长女婿!还是结过鬼婚的阴府女婿!嘿嘿!他干笑两声,——我们敬神怕鬼,可是生生猛猛的神鬼就是要追着你!唉,如今这巴灶山里的孽障已经太深了,连神明都给惊动了!阴阳失调的尽头,必定就是血光之灾啊……
山风很猛。四面山原默默含吐着天顶上的那片月光,游移着深浅明晦,像是八哥一样的面有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