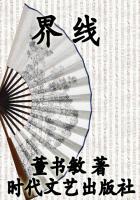1
他像豹子一样在林间跳跃着,追赶着他的慌乱的牛们。夏日摇荡着一种醉熟的气息,巴灶山成了一座大酒窖。所有藤叶、花果、山岚、夜露都发酵着熏人的酒味,连蝉鸣里,都仿佛滴着酒香。路北平日日顶着一张烧猪脸在烈日下奔扑,早把开初入山时的那些无名悸惧、空虚烦恼扔到爪哇国里去了。就像山里的林声、水声、气味伴随他内心感受的微妙变化而发生了某种变化一样,山外的世界,似乎也在发生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变化。空气里不时可以闻到焦煳味。惶惶然的鸟群蓦地落满巴灶山林,又蓦地像炮弹飞屑一样炸满天空。巴掌溪水在每天的某一个时辰会奇特地变得浑浊起来,傍晚下工,他的溪边窝棚柱脚常常可以看见撞到岸上来的翻着白肚皮的龙虱鱼。有时逆向刮来的山风会送来一阵阵遥远含混的嘈杂声,那嘈杂声响像是由多种声波混合在不同层次的时间里,被重重叠叠的山体播送出来的。时响时弱,时远时近,往往没待他分辨清楚,又一切遽然而逝。云不动,天不走,巴灶山依然那样豪横地在他面前躺卧着。只是牛们似乎最早知觉到这种变化,它们脾气暴躁,无心吃草,一个山坡一个林子地散游,没事就寻衅角斗,忙得路北平像一片落叶一样满山飞跑。头顶追着的毒日头更把人烧成一块火炭,一身“官服”便十足一身结满盐霜的盔甲,汗透了一层又一层,硬结如壳。
于是,便也想到了——“露阳”。
他把粗厚的牛仔布上衣工作服脱了,卷成筒条绑扎在腰间;贴身那件汗斑点点的白背心,便像电影里那些陕北老农的“白羊肚手巾”一样,打个卷盘结在脑袋上。手里仍旧挥舞着那根长杆砍山刀,仍旧是“彼得!”“犹大!”地喊得山鸣谷应;可是,从肌肤上煎沸着的汗珠里,从胸脯上拍击着的山风里,他感受到自己和这大野山原之间,确立了某种全新的、奇异的联系。他一时很难明了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只是那天傍晚洗澡,他把自己坦荡在一片落霞里,他听见了坚硬的水珠从自己铁块一样黑实的肩头咚咚滚落溪水的铿锵的声音;他忽然从自己往日被重重包裹着的体肤上,闻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味道——是太阳味。对的,就是八哥说的——阳气。那味道有一点蛮悍,有一种类似钢炮上的烤蓝的色彩,一种长河上细细吆喝着的号子的音调,一种马匹驮着辎重穿越关河边塞的杂沓的铁蹄的声音。他畅朗地洗着。那味道让他从自己的童年回溯回去,从长长的梅雨天后第一道出现的阳光里妈妈晒晾被子的笑靥中回溯回去,从外祖母飘飘的白发拂动着他的小脸颊讲述的那些会飞的猫狗和会说话的花草的故事里回溯回去。仿佛是撞开了时间之门,他最近时有一种恍偬:他赶着牛群往山里走,从巴掌溪的第一个指头往山窝口的第二、第三、第四道河曲里走,就是往时光里走,往过去里走,往自己的内心里走,往一个冥冥中未知的维度里走。他听着流水声,感受到一种烧红的铁块在清水里淬火所袅起的快意,他想:一直走到尽头,那会是什么呢?
是朱弟他们,最早让他明白了自己身上发生的这种微妙变化。
昨晚天刚落黑,朱弟领着老某、阿丁几个知青伙伴摸进山来看他,除了带进一片放肆的嬉闹声,还提着两斤连部加莱分的水煮猪头肉。原来山外又到了落实某某最新指示大战某某月的时候,朱弟他们要出门远征参加农垦兵团全师总动员的开荒“大会战”。这猪肉,还是专为这“出征誓师会”开的荤。哈,我以为只有我的心重哩,朱弟说,一说加菜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可不能把我们山里的放牛郎给晾了呀。谁想呢,人家队长那边,早把那上好的猪头肉为你留下了,大家分的是一斤肉,贴上我留的,你可是两斤。毕竟是队长的自家人哪,哈哈。窝棚里响起一片哄笑声。真是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呀,老某说,阿路,你想不到吧,这一回出征,我们朱弟升官当排长啦,还是什么——武装排长呢!排长排长,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谁说了一句什么老片子里的台词,于是火塘边又笑得火星四溅。
他在火光中默默望着他们,仿佛隔着一道史前的冰河,突然觉得异常陌生。大家七嘴八舌向他述说着村里近来发生的各种杂事:评比“割胶神刀手”谁谁做了假被发现啦,广州知青谁谁谁又和某某潮汕仔打了一架挨了处分啦,今年城里的招工招生分到村里可能会有多少多少名额啦……他发现这些话音在他耳鼓上滑来滑去,硬生生就是挤不进脑门里去。那些“最新指示”、“誓师会”之类的字眼儿像是储存在好几个世代以前的记忆里的,从朱弟嘴里吐出来,袅袅散发着一丝丝潮锈之气,那“班长排长”“师团连营”的,更仿佛是天书一样的呓语,混沌莫名而又与他毫不相关。他抱着双手站在一边,目光散漫。那些话音像枯水期的水流一样在他耳边挤撞而过,他偶尔笑笑,哼哼两声就像岸边踯躅的游人,随手把几个无所谓大小的石子扔进了无所谓深浅的流水里。
咦,阿路,你为什么不穿衣服?突然惊叫起来的,又是朱弟。奇怪,他记得这是那天在水边,他向阿佩发问过的同样问题。才不过几天,怎么这话如今听来,已经像是卖着陈年老醋了?他这才发现火光中的知青伙伴们,一色都是下工后的清爽打扮,的确凉衬衣或者蓝条纹的海魂衫,军绿、普蓝长裤,“海陆空”凉鞋(一种汽车旧轮胎做的风雨鞋),还配上不时装点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字样的草帽。相映之下,他的黝黑光裸的脊梁,坷坷坎坎的,在晃动的光影中一如史前的动物。啪!听见谁在自己脸上拍了一巴掌,好大的山蚊子!阿路,你身上光溜溜的,就不怕这蚊叮虫咬么?大家便顺水推舟地嚷起来:是呀,山里入夜寒气重,不怕着凉?小心哪,小心哪,村里的大队伍一走,就把你一个人孤零零扔在山里啦。他们总算找到一个话题了,他想。便苦笑着摊摊手:习惯啦,光膀子晒足了太阳,我身上阳气重哩,蛇虫鼠蚁的上不了身。他知道自己抄袭的也是阿佩那天的句子,可它就这样顺着嘴边溜出来了。你修炼出来啦!你修炼出来啦!窝棚里响起一片潮水样的漫应之声。
实在是话不投机。他记得他们也是像潮水一样退去的,手电们在黑林子里晃出一片白炽的光柱,随后便被山梁封满了一层墨浆一般的黑寂。他知道,是自己冷落了伙伴们临行前的一片热心。他并不想开罪这些以往或是亲昵或是疏远的农友们。可他搜索枯肠,实在是找不出一个可以像从前一样调笑、打闹的共同话题。他才发现,这巴灶山,具有一种奇异的剥夺能力。虽然,自己究竟被剥尽了什么又还原了什么,内心是并不明晰的。
不过,一整晚在火塘光影前的那重隔山如隔世的恍惚雾障,还是在最后一刻,被一句话刺穿了,现实像礁岩一样,突兀在水雾里。他把杂沓的人声脚步送过水曲,朱弟突然在黑影里一把扳住了他的脖子。
阿娴的事情不单纯,朱弟低声咬着耳朵,你可要当点心。刚才入山前阿彩把我拦到一边,说了一大串古怪的话:她说千不该万不该,你阿路不该做上鬼女婿又进山放牛来。阿娴死得不明不白呀……
——阿娴。阿娴是谁,谁是阿娴?这些时日——自从阿扁把他带入了另一个世界以来,他简直早把这个话题淡忘了。他提着马灯,站在窝棚竹门前,目送着山梁那边渐渐消隐的人声光影,忽然发现:这死鬼阿娴,现在反而成了他和山外世界之间搭建的一座惟一的桥梁。阴府的人物,反倒是引领他回到阳间俗世的印辙。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油然而生。他把马灯挂到牛栏门柱上,顺手抱了几捆夜草抛进栏里。灯火幽幽,暗影里的牛们或站或卧,瞌睡中并不忘向他发出亲昵的哞哞回应。安东尼的红脸白鼻像是氤氲着一重融融的光晕,犹大的驴脸却冰结着一脸的寒气。仿佛是站在地狱门口看见了内里的牛头马面,阿娴的面影在那一瞬间突然变得异常清晰。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
一片薄薄而带腥腐气的黄雾飘过来,他闪身避进了窝棚里。山里讨生活,最避忌的就是这种潮湿的瘴气。很久很久以来,他已经忘记了,夜半的林间水畔,最是需要提防这些不时袭来的妖氛了。
2
午后的定时雨,是海南岛夏日特有的一种景观。热。满世界里都是可以把生铁煮熟、把死猪烫活的毒热。早晨太阳刚露脸,林间露水滴落脸上,还带着沁人的凉意;太阳才升高一个巴掌,那草尖树叶,转眼就变成银戟片片,一阵干风吹过,只听见林间发出一片星星桑桑的脆响,你已置身庄一场杀声震天的热浪重围之中了。就像是川菜里的一堆肉,在“铁板烧”、“炸子鸡”、“辣油火锅”之间滚来滚去——麻、辣、烫,哪一样你都逃不了。连树阴都是专为你设下的陷阱。毒日之下,身上的汗水一冒出来就马上被灼干,让人想起北方极地哈气成冰的酷寒;可是一踏进树阴里,那汗水便像缺了堤,涂了胶,如同糨糊一样把你每一个毛孔死死封住,人就像煮在烫壶里的饺子,要喘喘不过气,要吐吐不出口。随着太阳升高,四面空气已经烧成一面面炙红的铁障,随时准备把人烫掉一层皮来,连青碧的天顶,也撑持不住这冲天热气了。于是,定了一个时辰,只要任何一片云彩飘过——哗!劈头盖脸的,总有一场瓢泼大雨浇泻下来,你甚至可以听见雨水在四野热土里淬起的吱吱声响。运气好时,碰上飘过的是厚云流,那雨下透了便四下爽凉,更多的时候,飘洒而过的骤雨只是蒸起了漫天热雾,熏蒸闷逼,那落日前的光阴就更费煎熬了。——定时雨,这每个白昼里顺延一个小时如期而至的雨,这海南暑天里让人又爱又恨、又盼又怕的定时雨!
这天午后,雨下透了,路北平便轰起牛群,往巴掌溪靠近连部的第二个指头边上那几个橡胶老林段里赶。这些日子,牛们已经热得没了章法,给个起走口令它偏给你趴下,吆喝它回栏歇息却又四散里奔突疯跑。燠热的山里已经难找到一寸它们愿意安心吃食的林坡。老胶林里草稀,平日是呆不住牛的,可毒日头下的高树重阴,空间疏朗,却可以让牛们有个透风喘气的处所。况且,他最心疼的是怀着牛犊子的“玛丽亚”,每日驮着沉重的大肚子,鼻口喷着白沫,在暑热中醉酒似的蹒跚。好几回在水边,它似乎一卧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路北平总担心它会中暑倒在毒日头下,需要为它找一个白日里可以安歇、随时方便生产的阴凉地方。他知道村里最近正摆着空城计——大队伍全被山外的开荒大会战拉走了,他可以很方便地避开与连部留守的人丁打照面。他甚至也不在乎什么“鬼女婿”的闲言碎语了,虽然阿娴之死愈加成了藏在他心底里的谜。回到这几片老林段,毕竟让他想起了往日和阿芳和朱弟他们闹闹腾腾度过的那些日子。八月酷暑,最难得的是雨后清凉,管它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呢。
果真,牛们一进胶林就哞哞地欢叫起来,三三两两懒卧在刚刚收过胶水的胶树下。林段呈几何形的树矩方阵显得深而空阔,一时间弥漫了牛们游荡的活气。他拿出多日来淡忘了的书本——那是一本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可是泉涌而至的汗水很快便打湿了书页。他又想起好些日子已经淡忘了的口琴,便从挎包里掏出来,呜呜吹了几声,忽然听见林段深处有什么声响,令得牛们突然骚动起来。
他停住手,侧耳听听,胶林里只有一片聒噪的蝉鸣,听不出任何动静。牛们却一个一个抖起身来,摩肩碰角地显得异常兴奋,往一个什么方向聚拢若。可是很快它们又垂耷下脑袋,卧回到树阴下。显然,那个刺激它们听觉嗅觉的动静,消失了。
莫非林子里有什么蛇虫鸟兽出没?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闪,随即,便被老胶林里愈来愈透出的一股山里久违了的人腥气所淹没了——这气味大概是从混合在胶树底下的汗酸味、废胶味、肥料味里透出来的,人腥气重的地方,可以生长苍蝇蟑螂老鼠,不容易碰见蛇虫鸟曽。果不其然,闷热中嗡嗡飞绕在他眼前鼻尖的,正是一只绿头苍蝇——这也是山里久违了的品种,怎么赶拂都不肯飞走,让他腻味得再也读不进一页书去。正在懊恼之中,忽然又察觉,牛们里似乎叉一次骚动起来,又在朝着一个什么方向聚拢。那个隐而不现的动静(声音?气味?),又一次把它们牵制了。
他狐疑地站起来,向着领头躁动的安东尼走过去,就在这时,他在胶林边的木麻黄防风林段后面,看见了一方浓阴遮蔽却又荒草茂密的林地。
萋萋荒草之间,有一片开着黄绒球小花的凤藤草。还有旁边长出了高秆的鸡毛草、鱼腥草,都是牛们最爱吃的。
他不禁惊喜起来:八月酷暑之中,这不是天赐的一片既避阳又丰茂的好草地么,牛儿们,你们是为此而闻风雀跃的吧?
安东尼!彼得!犹大……他吆喝着,把牛们轰过来。多好的凤藤草、鸡毛草、鱼腥草!吃你们的去!怪事发生了:牛们被轰到林边,对着满目荒草却迟疑不动。去去!他手上的细树枝往安东尼的花屁股上敲了一记,安东尼竟然领着牛群,哞哞哞地尖叫起来。
牛们犟抗的叫声在林间发出昂昂的回响。
直到今日,这对我还是一个谜。多少年后,路北平这样对阿苍说:牛们究竟是看见了什么?或者是知觉到了什么?它们就是不肯走进这片荒草里去。他吼着骂着,它们就是不肯!往日,看见这么一大片又嫩又长的鸡毛草,它们早就抢疯了!
他穿出木麻黄防风林带,站在齐腰深的乱草边,默默琢磨起来。
这是一片被四面老胶林和防风林围护着的荒地,巴掌溪第二个指头的拐角水潭,就远远地挂在它的边上。在四面浓绿之下,它的荒芜显得非常人为——这显然是一片曾经垦植而又被荒弃的老林地。他记得这些橡胶林段都是编了号的,便凭着记忆列数过来……八号段、九号段、十号段,不错,河沟那边是十二号段,这片丢荒的林地,应该是本来的十一号段。仔细看去,齐腰的乱草之间,似乎隐约露出了几棵胶树的残桩。这是台风掀掉的、还是山火毁掉的林段?他想着,抬眼望着林顶漏出天光的割口,此刻正烧着一盘巴灶山特有的蛇云。
牛们的抗闹声,更显出了这片荫蔽废林的荒寂。路北平心里突然闪过巴灶山中他遇见阿扁的那片林间空地,一种古怪的预感连同一丝莫名的悸意,突地袭上心头。
就在这时,他惊觉:牛们又一次为了什么骚动起来。
这一回,他终于听清楚了:
哩哩罗罗哇,哩哩罗罗哇……
是谁隔着这片荒弃的林地,在蛇云笼罩下的列面胶林里,发出低低的、尖细的、一阵紧一阵慢的吆喝声?
牛们的耳朵竖起来了,还没待路北平缓过神来,安东尼已经欢声哞叫着,领着牛群向那个声音发出的方向踢踏而去。
回来——安东尼!路北平发怒了,彼得、犹大、安德烈!你们给我回来!
他嘶吼起来。
我从来没想到牛们也有为难的时候。多少年后,路北平对阿苍说,并且,为难得非常哲学——它们为选择而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