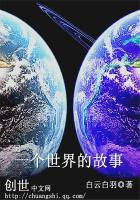1
西天上盘着血色的蛇云,橡胶林像烧着了大火。路北平数了数新荒地上自己今天挖下的树穴,报数,收工,开始从班长的记工表上寻找阿芳打勾的笔迹。
空白。阿芳不见踪影。班长也从地头儿上消失了。一扬手,他把凑过来逗趣的那个脑袋敲了回去。
少给我新闻联播!朱弟,你不就是想告诉我,阿芳又被班长找去“一帮一、一对红”了等等之类么?
“一帮一、一对红”是那个年头儿的时髦叫法,或者叫做——革命谈心。
不对,朱弟猴样地笑着:“阿芳让我告诉你,今晚加菜,她要你帮领她的份儿,猪下水,还有白马港拉回来的冰鱼。”
就差没让我帮她领她们女人家的“份儿”呢!路北平悻悻想着。她总是这样,恨不得连她们女生这年头儿分配的卫生纸、月经带什么的,都要让他代领“份儿”,好向全世界证明她的从一而终、义无反顾,妈的。
不过,收拾起地头儿上的挎包、书本,他心里还是为这“份儿”的代领资格,略略觉得松快了起来。
班长让你为“大战红五月”写一篇表扬稿。
丢那妈,我还想写一篇《养猪场的喜讯滚滚来》呢!
班长是个胖子。永远的知青标兵。和路北平比,可算是其貌不扬。
他说他不在乎,其实他顶在乎。
暮色中的山道上拖着各式各样的长影子。他落在了队伍的最后,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前面老农工们说的荤笑话。这是每晚收工的例行功课。男女农工们嘴无遮拦,每每把自家、他家的床上事加油添醋,说得学生哥儿们满脸飞红。路北平告诉阿苍,他是那年月知青堆里少数几个修炼得嘴上最敢放肆的。他说他现下锄头上吊甩着的挎包影子,怎么看怎么像一只母猫趴在一条瘦老狗的屁股上干着那种事体,逗得人堆里嘎嘎乱笑,都推搡着凑过来看。干完了,人家早干完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走得两个影子抖抖索索的,真像刚完事的样子。人群里更笑得浪响。就轮上你去干一干吧!有哪位老女工——像是阿彩,尖着嗓门儿说。那,阿彩,你就同他干一干吧!人群里一阵乱喊,学生哥儿,童子鸡呀!细路崽,好嫩的白斩鸡呀!
远远传来连部猪圈杀猪的尖叫声。
低级趣味,你们就是摆脱不了这些低级趣味。班长圆滚滚的身影忽然从后面追了过来,却不见阿芳,匆匆就从他身边滚了过去。
朱弟凑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损话,他没听见。
他木着脸,故意远离人群慢腾腾地走。你看,他们又干开了。他指着挎包锄头的影子,冷笑说,那老狗和母猫……
就是在这时候,他和朱弟都同时瞅见,那老狗屁股下面,有一点什么暗红的东西在眼前一闪。
“对的,就是连部村头儿那片我们刚刚走过的橡胶林。”多少年后,路北平对阿苍说,“那年头儿把所有的农场建制都改成了军队编制:生产队叫连,农场叫团。整个海南岛的国营农场,就统称为农垦兵团。”路北平说。
一片小红纸帖子,这时候要命地刺入了他的视线。
他顺手拈起来看了看,纸角儿边上沾满泥渍,打开,红纸上潦草着几行趔趔趄趄的、被露水打湿了念不通的墨笔字,觉得古怪,正要扔掉,队长老婆球婶已经拍着巴掌哈哈笑着从树林后面跳了出来。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呀。恭喜你,恭喜你呀。我的娴女前世无修三生有幸呀。你阿荣兄弟来世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你的福恩呀。你有大福大德千千万万不要客气计较呀。你来你来你来洗把手擦把汗,朱弟你也别跑!你喝一口番薯酒,为了等你猪头肉早炖烂了呀。你们广州知青知书识礼,我的阿娴阴间有福有运呀。你无要害怕,为人救世光明正大,你无要客气,你已经是自家人呀……
什么你都可以嘲弄,但你不可以嘲弄偶然。多少年后,路北平这样对阿苍说。
阿苍是在一段乏味的旅途终端,决定把路北平选择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当然,这个选择也纯属偶然。旅途的乏味,是为着陪同一位乏味的美国教授到海南岛作一个乏味的研究题目的田野调查。供职外事办的路北平算是旧地重游,却偏偏又是这么一个平庸透顶、乏味透顶的人。所谓平庸,比方,一路上除了醉心于阅读美国教授带进来的那些港、台书刊,向我们复述所读到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域外异闻,他几乎就找不到任何别的话题。那时我说,活得没劲透了,我干脆去写小说吧。——写什么呢?他随口问。我说写什么都行,比如就写你吧。我当时望着比我显得更加疲惫不堪的他——虽然永远西装领带、字正腔圆的。在日常人群里,他一定属于你我都最不会在意的那一类人——话里不无戏谑。
就是这么偶然的一句话,他开始给阿苍讲他的故事。
真的,你真的不可以嘲弄偶然。路北平说。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糊里糊涂被球婶精瘦的五指抓拽着像抓小鸡一样抓进了队长家的茅草伙房的,他也忘记了雾气腾腾的暗影里都坐了些什么人,他是怎样被按到了那张惟一空着的矮凳上腹空空汗津津就喝上了这通轮番浇灌的番薯酒的。他只记得红迷迷的眼前球叔的儿子阿荣被球婶推着向他鞠了个躬敬了碗酒,球婶让他跪下他不肯跪下,直到老爸队长球叔不知何时慢腾腾走进门来他才弯下了半个膝盖;球婶又用鹰爪一样有劲的五指抓捏着阿荣要他向他行一种什么礼,好像是被球叔一摆手像是行纳粹军礼一样地止住了。球叔忽然响声响气地说了一句什么把他的酒意闹醒了一半,只听得满茅屋的烟气里一片混声叫着:“加菜!加菜!”(夹菜!夹菜?他实在记不清了。)
——结阴亲。
这是一大通呕吐以后咀嚼着满嘴烂番薯味儿跳进他空落落的脑壳里的第一个字眼儿。
恭喜你呀。全连人加菜,都是沾了你老人家的光呀。
滚你妈的蛋!没等朱弟从门边探出头来,已经被他骂了回去。
床头吐出的酸酒腐肉,连汤带汁,早已水漫金山。
2
事情的原委,他是直到大半夜酒醒了以后把对铺上的朱弟揪起来,才理出前后头绪来的:
队长球叔要为他的儿子阿荣找对象结婚,可是却被他们的死鬼大女儿阿娴挡了路。听说阿娴是他们知青下乡那年得疟疾死的,那一年的疟疾像是发瘟疫,巴灶山的山里山外都死了不少人。阿娴死时小学刚毕业,算来现在也该有二十出头了。也不知应的是哪一方水土的俗例——客家?还是海南岛本地?球叔是客家籍老退伍兵,球婶却是本地临高人,说是只有为地底下未婚死去的兄姐结一门阴亲,才能为后面弟妹的婚娶消灾解难。否则,阴间的人要挡阳间的路,是儿子的断门绝后,是女儿的生出蛇鼠猫狗,总之是合家不得安宁。
队长就是那时候的连长,路北平告诉阿苍,可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叫他连长,都是叫队长。
据说,为这一门阴亲,球叔一家很是费了点踌躇。队长兼党支书的球叔显然很在乎“影响”,这年头,谁不怕“迷信活动”、“阶级斗争”、“党纪国法”之类的?球婶说:“儿子在先,还是党国在先?”堵了回去。为这件家事,听说球婶不依不饶地吵到了支部会上,弄得会计、文书一个个都出来圆场。那张阴府择婿的红纸帖子,还是球婶托人翻过山那边去,请出地方上有名的临高师傅,查过通书、择了吉日,才扔到那片橡胶林边上的。落日朝西,好像连撂在什么方位也有个讲究。上面写的是阴府阿娴妹的生辰八字,只等哪位阳间的阿憨哥拾着了这张红帖子,便成就了这番阴间阳界的通媒伟业。一大早,球婶便端着竹凳抱上一堆竹篾出去编畚箕,日晒雨淋,在胶林里已经猫了一整天了。明里说,今晚全队加菜是为了“大战红五月”开荤,其实,都知道是为了给队长家结的这门阴亲助兴。反正有酒有肉,管它为的是红的还是黑的?没想到这边头一屋的酒客早喝足了时辰,过往的人丁却无人对这胶林边上扔的红纸帖子留神识趣——哪怕是让个尿屁股的小男孩拾着了呢;女孩子拾着了却是不算数,守在林子里的球婶会马上扔出另一个红纸帖子来。眼看太阳落山,晚风习习,村子里四下响起一片开荤吃肉的杯盏之声,求婿心切的球婶,真的急得几乎要憋出屎尿来。
“天晓得我是撞了什么邪缘,撞上了这一门阴亲!”路北平对阿苍说。
“出事了,出事了!”朱弟后来告诉他,在他被队长老婆拖走去那个闹哄哄的茅草伙房以后,他曾经跑去通知一同从广州来的高中老某——老某可算是知青堆里的头面人物,想要老某出面搭救他。高中老某撇撇嘴说:“咳,阿路他主意大,就让他见识见识吧。”
你抢走了我们的知青女皇阿芳,老某要看你的好看,哼哼。朱弟恨恨地说。
一夕之间,成了队长家的阴府女婿。路北平在那个恶吐后虚脱得仿若一个纸人一样的夜晚,听见巴灶深山里的木轮牛车声咿咿呀呀唱了一夜。
3
当五月早晨的第一道阳光射到路北平铺盖上的时候,他睁开眼看到的第一张脸是——阿芳。
听说你结婚了?昨天晚上?阿芳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和鬼结婚,真好玩,真好玩。
她的这种略带夸张的天真表情,往日总带着某种撩人的妩媚,此刻,却透出阵阵冰冷,声音像钉子落到空荡荡的冰湖上。
遗落在出工钟声后面的连部村庄,可不就是这样一片冰湖。
连井台上传来的吊桶上下的咿呀声,也带着冰冷的回音。
现如今,一村人都拿这个当开心话题呢!阿芳说。
他闭着眼。
你说话呀!你成了鬼丈夫,那我成什么啦?
你昨晚上哪儿去了?一收工就找不着你。
你管我上哪儿去了?我上哪儿去用得着你管吗?
她又那样撒娇了,她知道自己最可人的时候是微微发怒的样子。他想。
我的冰鱼呢?我让你帮我领的那份儿呢?
路北平突然发作起来,人都要被整死了,你还记着你的臭烘烘的冰鱼!话音刚落,他忽然看见阿芳其实是捏着鼻子在跟他说话的,眼神里的新奇戏谑,直像是欣赏着一只掉进颜料罐里蹦跶着的青蛙。他突然闻到了空气里还弥漫着的馊酒精味儿和腐肉味儿。昨晚那场不堪的恶吐以及种种种种随之而来的不堪,一下子全涌上心头。
那我走了。阿芳头也不回就出了门。
她依然扭动着她的每一道线条都圆润得让人心疼的身肢。
好久好久以后他才回过神来,阿芳这是特意在“第一时间”里找他来了断什么的,并且同时并没有忘记那冰鱼的“份儿”——了断和他残存的最后一点干系。他突然奇怪地笑出了声来。
阳光有点刺眼。他想到井台上洗一把脸,走出门,觉得踩在一片虚土上,脚边软乎乎的满是尘灰。他提着水桶咣当咣当地走,知青宿舍的每一个窗户都像是伸着探头探脑的人头。这是我的错觉,他想。但是他清晰地听到了哄笑声。他走到连部伙房边凹下成盘状的井台,觉得整个斜面上的连部村落像是一个大会场,坐满了沉默的人群,等着听他发言。他站在井沿边上,突然破口大骂起来。
我丢戳你烂春袋呀,我丢戳你老母烂臭海……
他骂的是广州话里那些带色带味的最脏的脏字,平素里哪怕是三角市巷子里的流氓揪着他耳朵逼着他说,他也说不出口的。
那连串的脏话像落进了软软的棉花团里,村子里静得没有一点回音。
他从井台走回来的时候见到了连部的文书,他好像是在昨晚烟气腾腾的茅屋里灌他番薯酒的其中一人。文书对他笑笑:“没开工呵?”腋下夹着好像是文化夜校的小黑板,匆匆走了过去。
他突然停住步子发了一会儿愣怔,似乎若有所失。对的,他本来以为全连全村的人都会等着欣赏他的痛苦——他的糊里糊涂就当了“鬼女婿”的痛苦。他忘记了他新增加的一个身份是:队长家的女婿——虽然是“阴府”的,没有任何人敢公然挑衅把玩他的这种痛苦。加过菜的连部如同没加菜以前一样地了无尘埃。这了无尘埃的麻木反而使他觉着了反常,觉着了羞辱,可是,他无以应对。
他在推开宿舍屋门的时候,侧眼瞥见了不远处的橡胶林边,一张小竹凳上坐着一个目光幽幽的黑衣女人。那是球婶——他的(妈的!)强揿着他结了阴亲的“岳母娘”(哈哈!),正在默默地、小心翼翼地盯视着他(守护着他?还是监视着他?)。他想他应该发作一场,有点什么表示,一闪念又觉得无聊(是要对“岳母娘”发威吗?),便装着没看见,砰地撞上了门。
一夜之间已经改变了他的世界,确确实实就已经改变了。他从自己感觉异样的心底里,感觉到了整个世界对于他的异样。
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改变了,路北平对阿苍说,荒唐就在于,它竟然并不显出荒唐。
一整天他都拂不走林子边那个幽幽的黑衣妇人的影子。
因为那个影子,他甚至不由自主地——妈的,脑子里不时掠过那个叫作“阿娴”的他的阴府媳妇的假想的面影。
他在写日记。他知道朱弟今天帮他请了事假。
结婚大事,班长不准假,队长他还能不准假吗!天亮时他才昏昏睡过去,听见朱弟在他耳边拖长着声调阴阳怪气地说。
他忽然又哇哇地呕吐起来。
在那场恶吐醒过来的第三天,路北平,赶着一群黄牛,进了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