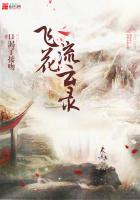将近结束了
我以上说的只是日本暴行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我见到的一部分,还有那许许多多我不知道的呢,它们就像一粒粒的尘埃飘散到空气中,就没有人记得了。而且,我的一些好朋友,也牵涉到日军的暴行中来,我怕把他们的秘密揭开,他们肯定会痛恨我不留情面,很大可能还会和我绝交。
读者在读着我写的这些故事时可能会说,我怎么只写别人的故事,而对自己的故事则很少着墨呢?你可能会问,我的上司每月给我多少报酬?这个问题我可以如实回答的--我的薪水很少,到后来连养家都觉得困难了。日本人答应给我每月1400块钱的报酬,但是他们并没有履行其诺言。第一个月是给了我全数,第二个月是半数,第三个月是三分之一……过了6个月之后,我拿到的报酬少得可怜。有时我会催促上司给我报酬,但他总是说一套老调子:“等交代给你的事情解决了,我们付全数给你。”但他们交给我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因此渐渐地我连钱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到现在他们欠了我52000块钱。我对他们会付薪水给我早已不抱希望了。
“满洲国”的很多雇员,和我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些警察、军官都得不到饷银。所以有门路的警察和宪兵只能靠抢劫、走私、赌博、贩毒、开妓院去弄钱。其他没有门路的人,只能穷困度日。
1936年3月末,我已经走到走投无路、家里快没米下锅的地步了,于是我将自己的一份房产卖了12800块钱。当我去收这笔钱的时候,法院通知我现在还不能收这笔钱,我还需要在报纸上做一个正式的启事,因为也许会有人出来提出异议。
公布了启事一个月后,我又被告知手续还没有完成,先让我交一种强制税,付2500块钱,我无奈跟朋友借了钱付了。接着又让我再把启事登一遍,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我还是一一照做了。一个月以后我还是收不到钱,官方的理由是也许哈尔滨以外的一些债主,还没有看到那启事呢。
我不过是无数出卖房产的人中间的一个,我的遭遇也是很多人的遭遇,而其中有些人的产业价值好几十万呢。8月初,我再次试图从法庭那边把我卖房子的钱拿回来(如果我雇用一个日本律师,我必须付给他1000元)。
我屡次跟我的上司说:“我需要钱养家,假使你们不能给我付薪水,你们就应该放我走,让我好找其他的谋生之道。”但他们说的都是一套陈词滥调:“给我一些时间,日本军方维持满洲的治安开销太大,我们现在也没有钱,等满洲走上轨道,我们一定会把欠你的钱全部归还你的。”
有一次,我一再地追问付钱的时间,上司生气地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欧洲人做了东方的主人之后,他们给东方人多少薪水呢?就我所知,在欧洲人手下做事的最高雇员的薪水,每月不过50到100而已。现在是我们做中国人的主人了,凭什么日本人要多付那么多呢?”
听到上司竟然说出如此无耻的语言,想到日夜从事各种鬼鬼祟祟的工作,结果是靠了自己的私蓄来维持生活,简直让我愤怒得疯狂了。
我知道自己为日本人所做的事是罪恶的,虽然我没亲自动手杀过一个人,但我也参与了很多屠杀人民的事件,这种罪恶感时常折磨着我。再加上我已经对大多数日本人--不管是我的上司还是同事,他们的嘴脸让我感到恶心,我无数次地想过一走了之,但想到家眷捏在他们手上,自己的性命捏在他们的手上,我内心的软弱又占了上风。
老“影”的“叛逃”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与老“影”相识5年时间,他不时跟我抱怨内心的苦闷,虽有抱负却没有施展的地方,为日本人做事谋害自己的同胞,也让他时常感到愧疚。1936年6月16日,郁闷已久的老“影”终于做出了他的重大决定:他率领着他所有的部众,袭击了一列火车,杀死了火车上的21个日本兵和两名日本军官,还抢走了30万元款项。从那天开始,他宣布了对日本人的独立。
日本军部听到了此消息,自然是非常生气的,他们也派了人去围剿老“影”,但老“影”是土匪出身,在深山里躲藏起来,与日本人打游击,日本人也无可奈何。老“影”叛逃的事突然间也给了我勇气--既然对日本人这么不满,为什么不能用实际行动对他们说“不”呢?老“影”的“叛逃”给我增加了勇气。
话又说回来,我也有聊以自慰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人把我掌控在他们手心里,他们把我的家眷作为人质,他们羞辱我、愚弄我,但我也用自己的“小聪明”回报他们。我在很多地方给他们玩了花招,他们根本没有识破。凡是经过我手里的情报,我都会秘密地送给义勇军以及日本人的敌人;特别是关于袭击义勇军的情报,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前告知义勇军。在日本人又开始准备行绑架之事时,我常常会在暗地里提醒被害者,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躲避。
在满洲政府的雇员中,有几百个中国人是像我一样被迫为日本人服务的,但他们中间的大半都参加了中国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暗杀日本官吏和汉奸。在这期间,有几千个日本人被这些中国秘密组织暗杀了,很多汉奸也因为出卖灵魂而丢了性命。“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曾经三次遇刺,他的皇宫也被人放火而毁去了一半!在长春的日本陆军航空站也被一场大火毁了,齐齐哈尔的空军站被纵火两次,哈尔滨的空军站被纵火一次,日军管辖下的绥芬河车站也曾遭遇两次大火,但日本警务当局始终没能发现谁是纵火的人。
满洲的局势是越来越坏了,到处人心惶惶,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处在危险当中,而且我的妻子每天都在这样不安定的生活中担惊受怕,为了她身心的健康,我也必须当机立断,立即离开此地。我让医生开了一张证明,说明哈尔滨气候太差,不利于她休养身体,所以她必须换个环境生活。但是被我的上司拒绝了,他坚决地说,“哈尔滨的气候是非常良好的,你的妻子无须离开此地。”看他口气如此斩钉截铁,我只好作罢。
8月10日这天,我的上司突然问我是否在1934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叫李善恒的人。我告诉他,我是在日本人未占领沈阳之前认识他的,他是军校的历史教员,但是在满洲沦陷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上司眯着眼睛注视了我一会儿说:“现在也有一个叫李善恒的人,在哈尔滨被宪兵逮捕,逃入松浦洋行后从五楼窗户跳出去自杀了,他是你认识的李善恒吗?”
“我怎么会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我镇定地说。
听了我的话,他又注视了我一番,拿出一张白纸说:“我要看看你的中文签字,写下来。”
我便把我的中文名字写了出来。他看了看那张纸,没有多说什么,把纸折起来放进了他的口袋中。他接着问:“1934年有两个被迫降落在满洲境内的苏俄飞行员,你和他们交谈过吗?”
“你指最近逃走的那两个飞行员?那两个人被严加看管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和他们交谈。”我说。
“不要说谎话了!”他严厉地对我说道,“你非常清楚他们并不是逃亡者,我们这样对外宣称,不过是为了羞辱那群苏联狗。有好几个人告诉我,你和那两个飞行员进行过一小时以上的谈话。”
我说:“这是造谣,我没有和飞行员谈过话。谁这样告诉你的,谁就是中伤我的人。如果你不信任我,你为什么还要雇用我呢?我为你们工作那么久,所获得的,除了欠薪,便是耻辱和污蔑。你如果要听信中村和拉查伊夫斯基这两个窝囊废的谗言的话,你就让我走吧。像他们那种样子,我是做不到的。”我愤怒地说着,装作要走的样子。
我的上司叫住我,笑着说:“别激动,万斯白先生,我知道这肯定是有人跟你作对造的谣,我绝不听片面之词,你是我的得力助手,我相信你。”
几天以后,我的上司和我讨论到19岁青年阿伯拉罕维奇的绑票事件,由于他的父亲迟迟没有付赎金,阿伯拉罕维奇已经被宪兵队的日本兵杀害了,但宪兵队依然向他的父亲索要赎金,否则就不把孩子的尸体还给父亲。上司问我,那青年的父亲有没有能力付那三万元赎金呢。我叹了口气,回答说:“就我所知,阿伯拉罕维奇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现在他的孩子已经被杀害了,他就更不可能出这笔赎金了。”
“关于这件事,外面有人开始议论了吗?”
“当然,市民已经在议论了。”
“他们说了些什么呢?”
“大家都说,绑匪实际上就是日本宪兵部队雇用的人员,而之前很多绑架事件中的赎金都流入了日本军事当局的私囊。根本无法阻止人民的议论,我们又不能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这天晚上我去找我的日本律师,去问问我变卖房产一事的进展。为了尽快拿到钱,我花了两千块雇了一个律师帮我办这个事情。他说,要拿到钱还有许多困难,他建议我最好去找审理此案的日本法官山崎,给法官塞个红包,这样我就能拿到钱了。
我不得不再上一次圈套,那律师便带着我到炮队街的法官家中去。我们在夜晚9点敲开了法官的门,山崎开了门,先从头到脚、冷冷地打量了我一遍才让我进门。我在山崎家里驻足的时间不过10分钟,谈话的结果是只要我给他3000块钱,我就可以领回我变卖房产的钱了。
第二天我签了一张300块钱的期票给我的日本律师,返回来的消息是答应在一个星期中就可领到我的变卖款了。明知是被山崎抢劫了,但现在我却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样的感觉真是很耻辱。
在8月末的时候,日本律师告诉我可以到法院里去领钱了。法院给了我一张通知书,上面写着,我变卖房产所得应为12800元,其中扣除2500元税金,750元审判费,最后给我的钱是9550元。我拿了这张通知书,去法院会计处领款,但日本会计员却告诉我说,我的证明文件手续还没办完,叫我等一会儿,我只得等。一直等到他们下班前,那会计员跟我说,你明天再来吧。
这真是一个不妙的信号,我心里想,难道他们又要讹诈我一笔钱?怀着满腔的气愤回到家中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疲倦感、屈辱感一下子涌了上来。我的妻子正在生病,我只能默默地把自己的委屈放在心里,强作欢颜。我的14岁的女儿琴纳维佛看出了我的不愉快,她跑到我的身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摸摸她的头,看着她天真烂漫的脸,把最近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都跟她说了。她静静地听完说:“爸爸,快活些吧!相信我们不久以后就可以离开满洲,离开这群野蛮的人了。即使我们现在失去了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能干的爸爸,你不久就可以把日本人抢去你所有的一切拿回来了。”听到我女儿这么说,我心中的不快立刻化解了一大半。
这一天晚上我的日本律师来找我,说山崎法官让我过去一趟,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没想到,山崎刚见到我就谦和地鞠了一个躬,热情地欢迎我进客厅。我心中大为惊讶,但一想,我是要给他钱的,看在钱的面子上,他自然会对我客气一些。
问过了我今天在法院的情况,用过了茶和烟后,他告诉我,其实我的证明文件已经办完了,只要我给那位日本会计员500块钱,我马上就可以领到支票了。我听了他的话,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下来了,我原以为会计员也要敲我3000块钱的竹杠。我当然连连答应了。
第二天我再到法院的时候,那位会计员也同样微笑地欢迎我,他说我文件中的不正确之处已经改正了,并且给了我领款的支票。告辞了会计,我在法院大堂上见到了山崎和一个俄国保镖正在等候我。我们一同到银行去领款,到银行的时候我还担心着银行会不会再发现支票上有什么不合格的手续,再敲诈我几千块钱。幸而支票很顺利地兑现了。我从款项中给了山崎3500块钱,用作给他与会计员的报酬。
敲竹杠真是无处不在,当晚日本的两份俄文报,《我们的路》和《哈尔滨时报》分别派人到我家,让我给他们捐500元的“办报费”。我把他们骂走了。没过两天,《我们的路》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警告我说,在三天之内必须给他们500块钱,否则他们就要在报纸上说我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特务,还是中国义勇军的耳目。《哈尔滨时报》也同样打电话威胁了我一番,我对他们都说,你们爱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我是不会给一分钱的。
我把那两通威胁电话都告诉给了我的上司,但他说,就他所知,这两份俄文报的编辑都是正直之人,一定是有人在冒充他们进行敲诈。我看跟他投诉毫无效果,便跟他告辞。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在我身后冷冷地问了一句:“那么,这两份报纸对你的指控是真的吗?”
我转过身,也冷冷地说:“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和义勇军的耳目,也太看得起我的胆量了,我不过是一个只想拿薪水养家的普通人而已。”我没等他回话,便又一次告辞,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转身出门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后背阵阵发凉,虽然上司已经看不见我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那双老鹰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扑上来把我撕成碎片。为日军服务这几年间,我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我清楚日本人已经在明明白白地怀疑我了,说不定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必须迅速离开满洲,否则性命堪忧。
走出日本军部的大门,我去见了一个C上校的亲信,让他把我的情况告诉C上校,并让他转告C上校,如果我确实要逃走,请给予帮助。
坏事一件跟着一件来了。当天晚上几个月前在寺庙前跟踪我的侦探福托普罗来找我,说中村最近手头紧,让他跟我要1000块钱。我拒绝他了,说我的钱全都用光了。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中村对我的拒绝很生气、很受伤。我无动于衷。
福托普罗“哼”地冷笑了一声,对我说:“我早料到你会拒绝。不过,我现在要提价了。过几天我还会来找你,到时候你要给我2500块钱,否则我就要把你私通中国盗匪的秘密告诉日本当局。你去寺庙里见的那些人,我都仔细调查过了,其中有些人是与盗匪有关联的。”
我心里一惊,但还是镇定地说:“我去见寺庙里的人,是奉了上司的命令,你觉得我的上司会相信你的所谓‘告密’吗?”
第二天,9月3日,在日本军事总部任职的我的一个友人急匆匆地来找我,跟我透露了一个让我大为震惊的消息:今天晚上,日本军事当局、宪兵队的队长和我的上司将开会讨论我的罪状。我的这位友人是与会人员之一,他答应开完会就告诉我会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