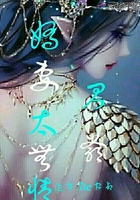墨西哥的教训,未来中国司法制度变革时,非常需要注意吸取。中国大陆的一些法学者,由于缺乏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知识,缺乏对法制与宪政本身的整全理解,在中华法系和大陆法系双重思维的影响下,动辄用大陆法系的思维去理解普通法系。这也可以理解,中国人生活在自己的司法制度之下,基于自由民主的刻骨追求,喜欢鼓吹程序正义与司法独立。然而,对欧洲大陆的“法德模式”的反感,他们习惯的知识图景却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普通法系式的生活经验则停留在中华法系和其他法系的奇怪结合之中,由此导致一种不伦不类的、并非导向多中心秩序和正义一元论的启蒙系法学观。因而,他们鼓吹的司法精英主义、主张司法与“民意”隔离、认为司法响应民意体现“多数人暴政”等系列观点,是需要被反思的。不过,在中国,这种局面只能靠基础教育的逐渐进步和人口的代际更替等系统发展才有可能改变。道理在于,如果缺乏信仰(不是法律信仰,而是根本性的救赎),那种持精英主义而不是专业思维的法律人,一定没有能力超越特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既得利益。
可以这么说,英美国家实行普通法系对其经济发展的促进给了我们远远超出司法制度变革的启示。制度与程序的“可操作”,前提是制度与程序的确定性、易于理解性和无法取巧性。必然不是针对超越性的多元论和怀疑论的彷徨。缺乏决断的人生是不存在的,缺乏决断的法治是在创造一种谎言。世界需要在在场性中落实超越性。
为此,一种成功的司法制度,它至少包含着诸多层次的一元性。首先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必须选择相对适应自己民情民风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这样一种一致性,有利于这个社会形成坚定的法治文化。最好莫过于这个国家的各种小共同体都是以法治正义为导向的。强大的政府很多时候是对法治的威胁,这里的小共同体还能为普通人提供尽可能的福利,以减少这个社会由于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对全能政府的需求与依赖。第二点,司法正义应该成为这个国家主权决断的底线,绝不允许存在超出法律允许的政治权力之运行,如以立法和行政代替司法的决断。立法必须体现出普遍的爱,司法则必须以独立与公正的方式体现普世正义的原则。第三点,这个国家的法律条款之间,必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能在形式逻辑上互相矛盾,或者形成多样性标准,以致守法者无所适从,为了生存被迫知法犯法,执法者依据丛林法则为所欲为。如果法律随着人事的变化而任意变化,或者被选择性执法,弱势群体势必被纳入到对他最不利的法律解释中去。法制史上着名的“造法失败的八种可能”即讨论这个基本原理。第四点,这个国家的司法运行规则必须具有确定性和一致性,除了对特定强势主体(如政府及其官员、强大的经济集团)等实行有节制的有罪推定,对广大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最终确立起一种充分保障普通人,尤其是弱势个体的自由权利的程序正义原则。
五、宗教文化与市场选择的一种对应关系:为何我们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
人的有限不等于不能有所作为,对政府来说也是如此;人的有所作为不等于可以无法无天,对资本来说也是如此。市场与资本仅仅是利益的一方,不是正当性的来源和标准。甚至不存在抽象的市场与资本。具体说来,任何资本与市场自由的鼓吹者,难免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这样定性,并不意味着剥夺资本与市场的代言人以及他们所代言的那个利益群体的基本权利,并不意味着剥夺资本与市场的自由,而是说,人们在倾听他们为资本与市场代言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彼此的有限性,本身从来就不是全民、更不是绝对正义的代言人。然而,这样说,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机制,更多只是理想色彩浓烈的盼望。资本以利益为核心,虽然不能证明雇佣劳动制为不正义,但却天然害怕超验价值的质疑。市场与资本的互动,以及由此兴起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在一个宗教和传统色彩日益淡薄的时代,尤其是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运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个“自由秩序原理”赋予了资本与市场反专制反极权的代言人角色之后,拥有了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频频上升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理解的无止境,呼唤扩大我们的知识图景。然而,每个人都倾向生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思考、判断、言说与选择之中。如果历史定格在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的言说者就会比今天确信某些命题,而不确信另外一些命题。以世界金融中心在世纪初期的分布为例,我们可以判断这些金融中心都采用普通法系,也可以指出普通法系与基督教传统、小共同体法治传统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是,也有足够的事实能被用来反对上述命题,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强制之下也可以有普通法系,就不是这些东亚城市“自生自发秩序”运行的结果。在这里,既没有多少基督教传统,也说不上丰富的小共同体法治传统一一“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在这里的解释力显然有限,“信仰法治正义一元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也未必行得通。这里的“正义一元论”只能“蜕化”为更加世俗化的“制度程序正义一元论”(也即法治的唯物论版本)。
论及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历史性。由于教义见解等多种因素,基督教分为了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大教派,新教分化为了改革宗、安立甘宗和路德宗三大宗派。从核心教义上说,改革宗与安立甘宗多少相对接近;从组织上来说,安立甘宗相对比较接近天主教;从公共参与而目,改革宗最积极,路德宗和安立甘宗次之。改革宗主导的政治体,更加倾向实行民主共和制;路德宗主导的政治体,几乎都曾由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执政,多数实行各种君主立宪制和国教制;天主教曾经主导的法国、意大利实行大陆法系,政体分布为半总统制和议会共和制;另外一些天主教曾经主导的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实行大陆法系和君主立宪政体。然而,基督教正义一元论似乎不能正面论及的是亚洲的部分法政体,可以说是在欧美强有力引导下的:日本实行大陆法系,迄今主流价值仍在排斥基督教文明;韩国转型为新教和天主教为主导,实行深受美国法文化影响的大陆法系;新加坡实行普通法系,这个城市国家以佛教为主要宗教,基督教只是小宗教。此外,全世界还有大量天主教主导的国家,如亚洲的菲律宾和东帝汶,实行各种不成熟的君主立宪制或者是民主共和政体。这些国家都实行大陆法系,常常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但至少,相对另外一些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如俄罗斯、德国、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这些天主教国家没有经历过哈耶克所批判的“极权专制”。另外一些被哈耶克批判为曾经“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天主教或东正教为主要宗教,至今仍在实行大陆法系,政体为各种形式的民主共和制。原因在于,经历过苏共主导下的政治控制,这些国家旧有的王朝势力丧失了政权,传统已经中断,只能采取民主共和制。
目前经济全球一体化日益明显,世界被视为密不可分的“地球村”。然而,政治上、文化上、司法上,尤其是核心价值观上,世界远远未达到“地球村”的欣赏者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在政治发展和司法制度上,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各个主权体仍然有不同的看法。即使都将“人权保障”列为国家基本宗旨,世界各国的人权标准仍然是不一样的。
然而,经过本文的叙述,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1世纪现存的国际金融中心,几乎都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里。最着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属纽约和伦敦,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直接成果。另外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即香港和新加坡,诞生在东方国家,相对更多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曾被英国纳入殖民地体系。日本的东京至少也是个金融中心,算是大陆法系中极少的例外,但却与其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此外,还有更多的发展中政治共同体,现代化的金融和经济也在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并未明显表现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所叙述的英美国家的某些政治发展态势。
既然世界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基督教一法政系”这一范式的解说能力就仍然是相对有限的。它的大量细节和一些结论,很难被更多认可。亚洲国家的基督化至今仍然是基督徒的理想。有些特殊的东方民族,如日本,曾经经历宗教大屠杀,加之自身民族传统的根基之深与顽强,基督教迟迟发展不起来。基督教在日本的小规模传播,更多是在“二战”之后,是日本民主化之后的结果。而就一方面来说,日本民族的宪政民主化,却多少以美国长期的基督教文明为“原因的原因”。基督教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些细节关系,显然并非几篇论文即能说清楚。“宗教文化与市场选择”之间的这种看似确定、又有颇多模糊不定的一致性,如果根据严格的科学分析来看,也许多多少少具有“假说”的一般特点。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更加踏实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仍然值得我们探究。
不过,至少可以确认,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互动才是文明的常态,才能确保个人自由与社会自治的空间不受侵犯。国家掌握暴力,经济掌握财富,社会往往是孱弱的。只有以传统价值为纽带的小共同体才能坚持不懈地超越于世俗化的维权中司空见惯的利益原则来维护社会自治。只有让国家和市场相互制衡,以社会自身的力量(例如集体抗争)来维持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相对平衡,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
市场经济、社会公正、司法正义与基督教传统,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由基督教正义一元论所延伸出的“节制资本”的法理学结论,直指经济自由主义的僭政本质,加之对法正义的制度落实,促成普通法系国家产生出国际金融中心,从而成全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基督教正义一元论所试图归纳的“正义”在多个层次的“一元性”,在法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科学上直指价值多元论的僭政本质。基督教会对社会公正与公共福利的参与,无论在路德宗立国的国家还是在加尔文改革宗影响深远的社区,都是有效节制劳资矛盾、避免“通往奴役之路”的坚定基础。对比制度崇拜情结深厚的世俗正义一元论版本,基督教正义一元论深刻地体现出了“可回溯性正义”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