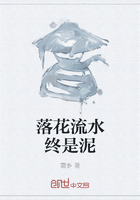留儿姐姐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有些泛红。
我知道是为了什么。
她方才给我擦洗身子的时候,我看见她又是悄悄用手指尖在我脚心处试探。我一向怕痒,脚心一直是半点也碰不得的地方,轻微的呵痒也会让我唧唧咯咯疯笑好大一阵子。可如今,我却感觉不到分毫,也动弹不得分毫。
我已经不想哭了,反正事到如今哭死也没用,还不如就当是已经忘记的好。于是我抓过枕边的九连环,故意狠狠地拆,扯得金属环子不断发出铮铮的磕碰声,心里反倒觉得有些解恨。
早饭后又睡了会子,醒来后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于是就拿了宇哥给我的布偶人开战,左手是黑胡子的张飞,右手是有雉鸡翎的吕布,你来我往缠斗正酣的时候,听见四师哥进屋来笑道:“哟,正开戏呢。”
我一见是他,也笑道:“澜哥你来的正好,我这会子刚好饿了,快说带了什么好吃的给我?”
四师哥摇摇头:“小馋鬼,见面就要好吃的。”说着话就从怀中拿出个小布包,摊开来,是手帕包着的十几颗大大的枣子。
我拿过一颗最红最大的,咔嚓咬了一口:“还好,挺甜。”其实这枣子不仅很甜,而且很脆,只不过我一向更喜欢点心糕饼,所以即便这枣子再好吃,我也不肯多夸。
我一连吃了四颗枣子,才发现自己身边竟然还坐着个活人。虽说这个四师哥不会跟赵飞似的是个话痨,但每每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和我说笑,可今天,他竟然就一直坐在一旁静静看着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登时觉得心口一堵,瞪着他道:“澜哥,你这是也要学大师哥的做派?”
他却犹豫又犹豫,过了好一会子,最后才有些腼腆地开了口:“风儿,这几日你见到大师哥,可曾觉得他近来是不是……是不是有些异样?”
我含着颗枣核,有些莫名其妙,“异样?有啊,这半个多月他都没骂我没打我,还没逼着我背书写字折腾我,我还以为他要做大功德成仙得道呢。”
“风儿,你正经些。”顾澜生竟然朝我皱眉,“大师哥病了,你难道就当真半点也瞧不出?”
“他病了?”哼,大师哥那样的金刚菩萨还会生病?顾澜生你哄谁呢?再说了,就算是真生病,大不了也就是受了个风寒,他又跟着师父学了不少医道,还治不了他自己的头疼脑热?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顾澜生就朝着我沉下脸大惊小怪,真是比九师姐还狗腿!一想到此,我更加不耐烦起来,赌气说道:“那你就赶紧去照顾大师哥好了,还来看我干吗?我命贱,死了活该!”
我原以为他会好言好语哄我,哪料想他竟然也上了火:“风儿,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大师哥生病是为了你,你瞧不见他如今脸色有多难看?你瞧不见他这几日瘦了多少?他日日来瞧你,你对他不理不睬也就罢了,还只跟着暮宇那小子嬉笑混闹,你……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这个四师哥素来温文可亲,对我更是一向迁就,我从未曾见过他对我说出如此重话,一时心中委屈大生,狠狠一口把枣核啐到他身上:“呸!我就是天生来的没良心,我就是天生来的不知好歹,那天他没下死手一顿板子拍死我,我没对他感激涕零是我的错成了吧?大师哥生病与我何干?我有多大的胆子敢去招惹他?”
四师哥显然也是恼了,一双过于秀气的眉毛紧紧蹙起,却咬牙不再说话,把眼睛避开不看我,自己坐着生闷气。
我见他不肯过来哄我,还摆出这样一副脸色来恶心我,心下更是光火,抓起枕边包着枣子的帕子,狠狠往地上一掼:“谁稀罕你来看我!你们都一天到晚去围着大师哥那尊大菩萨打转罢,何必还到我这里来浪费光阴?我如今已经是死了半截的,便再想出去闯祸也是不能够了,你们日后倒是省心了……”看着那一把枣子落地便四散滚开,各奔东西,我也是越说心里越难过,只觉得一腔子眼泪都哽住在喉头,死死咬住下唇,强忍着不肯大哭出来。
眼见着四师哥生气离去,我抱着枕头大哭了一场。偏偏他全不理睬我,弄得我愈发窝火难受,于是在留儿姐姐送来午饭的时候,我咬定了说头疼心口也疼,说什么也不肯吃饭。任凭宇哥和留儿姐姐好话说尽,我仍旧只是赌气发脾气。
我说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如此难受。
午睡醒来,铅灰色的天空里落下起了雪粒子,轻轻的啪啪声打在窗上墙上屋瓦上,像无数穷极无聊的指甲在轻轻扣击,听得人又闷闷欲睡。留儿姐姐坐在我床边,正专心致志地绣一朵水仙花,她绣完一条丝线便抬眼看看我,见我仍旧傻呆呆看着她,便抿嘴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仍旧低下头理线穿针,继续不紧不慢地绣着。天光略暗,却尤其柔和,将她的侧影映得静美如画。
我看了很久很久,心里生出个不着边际的想头:我很希望有一天我睁眼醒来的时候,看见我娘也像眼前的留儿姐姐一样,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我身边绣着花,也这样看看我,也这样朝我一笑……将墨玉攥在手心里,贴在心口上,也不知何时就沉沉睡去,却是浑然无梦。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坐在我身边静静望着我的不是我娘,也不是留儿姐姐,而是大师哥。
我好一阵子才醒过神来,便认命地叹了口气。
过了好一阵子,大师哥果然还是一言不发,我实在闲极无聊,趁着他目光沉下去的时候,偷偷打量他,才发现他当真是病了。看他那副青白的脸色,还有凹陷下去的两颊和眼窝,似乎还是病得不轻的样子。犹豫再三,我还是觉得该说句什么,可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想抬起身子,下半截仿佛已经被截去了一般,全没有半点儿知觉。
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师哥上前来轻轻扶着我略抬起些身子,又仔细给我仍旧整理好被子,便仍旧又坐回到床边,继续沉默。
我张口试探着小声叫了一句“大师哥”,他猛然回了神,柔声问我:“要喝水么?”
“我……大师哥是病了么?”我大着胆子问出这一句的时候,后心上出了一层冷汗。
他显然也没想到我问他这个,一时也是一愣,赶忙将眼神避开我,只瞧向窗外,迟疑了一下才道:“只是偶感风寒而已。”
他不瞧着我,我才敢看向他。师兄弟当中,四师哥是生得最秀气最好看的,二师哥是生得最高大健壮的,我宇哥是生得最有灵气而且对我最好的,而这个大师哥呢,说良心话,是生得最为俊朗最为沉稳的,也是最像师父的一个。依旧是平素穿的半旧青衫,依旧是素日的淡然神情,我第一次发现即使他此时形容憔悴,但仍旧是风骨矫然。
他朝窗外望了好一阵子,方又瞧向我,我赶忙又低下头去。等了好一阵子,才听他开了口:“风儿,下次可别再闯祸了,你身子受不住。”他声音很低,毫无训斥之意,倒是颇有些肺腑之言的意味,我正心生感激,却听他又道:“不光我们看着心疼,师父也心疼,那日师父来瞧你的时候……”
师父来瞧我?
难道说那日不是梦,而是师父当真来看我了么?
难道他真的心疼我了么?难道他不是趁我昏睡的时候丢下墨玉就走了?
不!我宁愿那是一场梦,一场永远不会被打碎的梦!于是我咬牙狠狠摇头道:“我一个人嫌狗憎的野娃子,师父怎么会心疼我,他厌弃我还来不及呢。”
大师哥深深叹了口气,仍旧沉声缓缓道:“风儿,你听谁说的师父会厌弃你?这些年来师父一直都是心疼你的。这回你闯了这等祸事难道就不该受罚?你若是肯早些认个错,何至于把师父气成那样?又何至于自己又吃了打?”
我一听之下登时心口憋满厌恶之情,心中所想冲口而出:“为什么逼着我认错讨饶?就因为我没爹没娘?没爹没娘就活该给人家欺负了回来还要挨打挨骂受冤枉?谁让我不过是你捡回来的野娃子,给冤死了打死了也活该!”我就知道大师哥跟师父一样根本就不疼我!
“风儿!不准你胡说。”大师哥低声呵斥我,让我心里愈发恼火。很多窝在心里许久的话一旦开了个头,我哪里还停得住?反正已经方才那一句就必定已经惹恼他了,干脆就图个痛快算了。我也就彻底豁出去了,瞪着大师哥高声道:“师父怎么会心疼我?他不过是恼我在外面丢了他的脸面,又恼我不肯狗儿一般地讨饶乞怜,更恼我没在外面给人打死了大家清净,所以就叫你们下死手打我。我在外面没给人家欺负死,回来倒要给你们打死,我不冤枉谁冤枉?还说你们心疼我,除了宇哥,你们哪个不是拿我当做个野猫野狗来看待?高兴了就来哄哄我,其实根本没人是真心疼我,平日里个个口里仁义道德,都是好人堆儿里的好人,等我受委屈的时候,还不是都往死里打我?师父是伪君子,你们是小伪君子……”
我心口里的恶气还没发泄痛快,背心上陡然被狠狠拍了一掌,恍惚听见他喝了声“你住口”,背心上的剧痛还没有清晰,胸中一阵翻涌,一口甜腥之物已然冲出喉咙,却是一口鲜血,喷得枕上床头都是点点殷红。
我眼前一花,天旋地转间两耳嗡嗡作响,险地立时便要晕去。只是好在心下并不迷糊,我狠命定下心神,转过头去恨恨死盯着大师哥,此时满心口里憋满了怨恨,奈何背心剧痛胸口闷疼翻涌,无数句痛骂只化作牙缝里艰难迸出的三个字:“我恨你……”
大师哥似乎是全没料到他这一掌拍得如此之重,愕然一愣,随即赶忙上前一把扶住我,抓过帕子便要来擦我口边的鲜血。
我此时已经厌恶他到了极处,咬死了牙狠命推开他,拼尽所有气力往旁边躲去。岂料就在这一瞬时,忽觉下半截身子深处骤然传来一阵彻骨的剧痛,却是我从未遭受过的万般苦楚,急疼之下,我双手乱抓尖声号哭:“啊……痛……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