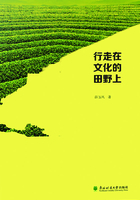中午,儿子轻轻敲打我微凸的肚子,说我发福的样子好难看。这本是很琐碎的生活细节,全无所谓,或许还可以得到些须家庭祥和的甜蜜,可是心里禁不住一阵揪心的酸楚。想起儿子小时侯也这样闹,可是阿婆马上觉得舍不得,不绝口地劝阻。幼小的孩子刚刚扬起他稚嫩的手掌,她就接上:“哎,打伤,打伤。不要。”说完弹起泛白的眼珠,装出吓人的态势。听她惶急迫切的语气,当时想阿婆肯定是老糊涂了,怎么这么笨。这样通情达理,这样坚强刚正的阿婆,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孩子的嫩手,即使再加几分力量,我这样粗厚的皮肉,还不能经受吗。心底里甚至嘲笑她,三代亲,亲不过第二代。玄孙亲,亲不过孙子亲。当时只是傻傻地笑,现在回想起来,那份自然到没有一点做作的话,体现的那份纯粹的爱情,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呢?
在她的眼中,我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直到我们成家立业,我们还是这样愚笨,什么事情都需要由她来支撑,离开她,我们将一无所成。就是建造房子,需要壮劳力的工作,她也要抢在我面前,把应该属于我的份额,一声不响地完成了。当我回家,看见两楼地板粘着的已经僵硬的水泥,居然被铲平了,我讷讷地无法说出口,不知该赞美她的勤快好,还是责怪她不珍惜身体好。当我回家,听说在没有灯光的夜晚,她要进入没有浇平的地墙,结果一连摔了三跤,那份痛楚有什么可以形容呢,问她去干什么,竟然是防备材料被偷,去捡几斤水泥钉当废铁卖。我心因无法安置她而焦急如焚,皱着眉头黑着脸,很难看的,她却好象伤害了我一样,谦和地笑。想把她骗进城里,说是照顾玄孙,被她一眼识破,然后简直是商量的语气:“老了,一分也没有用了吗,难道让我烧烧开水,也帮不了你吗?”想着几十年来对我绝对权威的腔调,竟至如此谦卑,一直在我面前是老大的架子,竟至老到象我的孩子一样,我还有什么理由让她远离他所牵挂的家庭大事呢。好几次对她说:“你的任务只是好好保重身体,你力量太小,几天的工作,我化一百元,就会搞定,如果身体劳累,至于生病,就会害我化好几百元。而且人在外地,照顾不着,会心无着落的。”当着我面,喏喏连声,可是转过身,事体照样是她做,生病了也没有化什么钞票,就静静地远离了我,如果不太劳累,她可能真能混上百岁,按她的身子骨来看。我本来可以强制她来城里的,其实吵一架,她就会听我的,可是胡乱地顺从了她,或许心里存着一丝自己也没有察觉的自私,人手确实不够,顺水推舟,就让她管理建造房子杂乱的事务吧,到今天我的心里只剩下内疚。
每次回家,总是欺骗我说身体健康,在我面前大口地喝啤酒,还夸奖地用手撮起龙虾,吃得渍渍有声。后来在乡邻的口中知道,用啤酒和流液充饥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只是单单瞒着我。还要表演一样,在道地里,把老房子拆下的烂栋梁,用大砍刀劈开,一片一片整整齐齐地码起来。看着她苍白的脸色,自己好不懂事,还开玩笑地说她年轻时候一定是个大美女,理由是缠小脚,瓜子脸,瘪着嘴,双层的眼皮,说得她骄傲地笑,可是伸出那张手,因为劳动,骨节粗大变了形的,好象唯一使她害羞的样子。等我知晓真相,芝麻糊已经喝不下去,没有什么可以充饥,吃下的东西,总要呕吐,身体衰败的样子全显现了出来。这时站在她的面前,木呆呆地,不知道该责怪她,还是劝慰她,看着她装出的笑脸,毫不在意的样子,心里有多后悔啊,几年之前,强迫她来医院检查身体,照x光,已经发现肺叶布满血丝,当时只以为是伤风感冒引起的,那位女护士说,你奶奶的身体比中年的妇女差不到那里去,当时牵着她的手,简直欢呼雀跃了,想不到不起眼的病况,拖延至今,终于无可救药。
想起,前年弟弟造房子娶媳妇,花费不少,她再也不肯上医院的事情。躺在床上病体支离时,一听要医治,拉都拉不起。舍不得花费钞票,说是九十五高龄,应该叫寿终正寝。我知道她是这样热爱生命,真的牵挂着我们兄弟俩,牵挂我性格卤莽总要吃亏,牵挂弟弟懦弱可欺也要吃亏,她是真的留恋着这刚刚起色的家。可是她害怕因为她生命的延长会浪费兄弟俩的钞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她在生命的延长和减轻兄弟俩的负担之间,选择了后者。那天终于被骗到城里,说是九十五高龄的老人上医院不花钱,全部由国家补贴。看到照x光,付费竟然要500元,转身就走,还说吞钡粉介难吞,还要介多钞票,医院简直是谋财害命。那个老头医生说:“还开刀,开什么刀,回家去吧。”我站在门口是多么无助啊,真想和医生吵一架,就凭着他说这样的话,打一仗也无妨。
知道阿婆大去之时已经不远,基本上是每周日回家看望,可还是不能满足啊,于是禁不住思念和牵挂,半夜八九点骑摩托去老家,祖孙两人说话至半夜,想到她的定期已近,可是自己回天乏力,象无头苍蝇一样在堂前四圈地走,半夜回城,让夜风吹拂自己懵懂的思绪,也不是有效的放松。偶尔和她睡在一起,想要半夜里可以照顾她,略尽孙子的孝义,可是梦中醒来,反而是她在照顾着我,她为我在轻轻地拉着被头,就象小时侯一样,总要把被角塞进我的身子底下,说是别被风吹进来,受了凉风感冒,要裹住我的脚底,说是寒暑之气,这里反应最敏感。大去的前夜,她竟然很用力地想把枕头塞进来,把我的头垫起来,三十年了,总怪我睡相不好,不垫枕头不聪明,不知是哪里得到的理论。也不知道饿了好几天的她,哪里还有力量坐起来,要管这不相干的细稍末节。醒过来的我默默地看着她,她也默默地看着我,终于露出惯常的笑,可是她的嘴角微微抽了抽,怆凉的笑意就隐然散去。灯光下,相对无语,都知道大限即至,相互亲近相互爱怜相互扶持相互依傍的日子从此远去,不会再回来。相互之间定定地观望,看着她绵长的深邃的关爱的依恋的痛惜的不舍的眼神,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那天早上,我还懒睡,进来探望的人群不绝,他们只是称赞祖母的勤劳善良,乐于助人,无私关爱,她开始还端坐着,“然啊,然啊。”“应该的,应该的。”这样唯唯地应和着,可是我知道她终夜未睡,憔悴的身体不堪于亲戚友人的探望。照我的性格全想推出门去,可是按她一贯的谦和,终于无法回绝这许多的亲情。我牵着她的手,她的目光正定定地看我,散淡的眼神忽然强烈,继而呼出最后一口气来,头一歪,把我的肩膀靠个正着,恰象我小时候,喜欢靠着她肩膀睡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