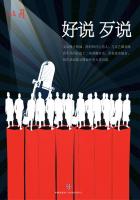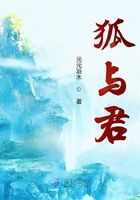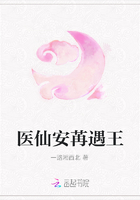我对竹的爱好始于它给我的实惠。印象之中,父母常为自家经济的拮据而激烈地争吵,我便借机离开他们,躲到乱槽洋中的小竹林中,王维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我没有这技艺,但能享受一份难得的安逸和娴静。现在脑子中还有模糊的印象:夕阳西下时,淡淡的阳光从竹林的那一头射进来,透到这一头,撒在身上,一片斑驳的影子。风吹过,摇摇晃晃的光圈笼罩着,便感到生活是如此的安闲和自在。手里抚摸着绿得发黑的嫩竹,说是嫩竹,其实已经是一年生的竹娘,是明年丰收的希望。望着黄得发出褐斑的老竹,想象着庄稼地里的茄子垄,又有篾片可以支撑尼龙布,老房子的道地里就堆着很多使用过的已经烂得发黑的茄子撑和带豆竿。回想起来,自己是懂事的孩子,我小时候喜欢买连环画,奶奶给我的壹分贰分钱,积聚起来,仍然不够我使用,又不便向父母伸手,于是经常在田垄里挖些拇指大小的嫩笋,剥了皮,结成一束,七分八分地卖给人家,稍稍能够满足读书的愿望。
后来,读的书多了,有关竹的知识也便了解得多了。佛家寺院多栽种修竹长篁,给人的心灵以宁静。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传说松梅竹有岁寒三友之称,竹是坚强和刚劲的象征,唐太宗说:“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有时写作时默想把自己的笔名取作“竹青之”,不过和奶奶一起时,我常和她开玩笑说两人都是田洋畈里的青头钻。田洋畈中泥土层薄且坚硬,但是有竹龙根(竹茎有龙的筋节,俗称之)从地下经过,总会有竹笋倔强地钻出来,我们当地就叫它青头钻。由于缺少养分,它的皮黑中泛青,毛细长且粗糙,肉瘦且干勃,但往往上得了样,成为竹林中一棵不起眼的瘦竹,老且劲朘,内行的人往往把它当作大材来用,如制作竹席的边角,畚箕的后部等容易磨破的部位。每当这时候,两个人总会心地笑。
奶奶的一生是其艰辛但自豪的一生,30岁守寡,凭着十几亩贫瘠的薄田旱地,硬是把孩子拉扯大了。看着她慈祥的笑容,心里充塞着洋洋的温暖,仿佛阳光普照着心窝;抚摸着她手指粗大弯曲的关节,听她历数劳动的快乐、生活的艰辛,心里就充满无限的关爱。
她也爱竹,她说竹有取之不尽的财富,每当暮春季节,竹笋已经上样,山地上便堆满了自然褪落的笋壳。笋壳可以做沙发席梦思,有人收购,至今还记得,那天拖拉机装得实在太多,倒了好几次。剩余的,已经打包的笋壳一捆一捆地甩进水池里,浸没,时间长,烂得透,然后在昏暗的弄堂里,大家在扎丝,一辆小纺车摇得嘎嘎地响。因为她白天要上班,便每天早起去捡。有一天星光灿烂,她从细小的木窗框里看出去,启明星已经高高地吊在天边,于是起床出发,到了山脚,却是黎明前的黑暗,被黑暗笼罩的竹林里看不清一张笋丝,她坐在山脚下的一块凸出的粼峋的崖石里,心里的害怕和美好生活的希望总是在心头交替荡漾。
她告诉我竹林的来历:四位叔舅公爱着她,常常从二十几里远的老家赶来帮她,替她收拾庄稼,后来看到乱槽洋一片废弃的碎石地,用了几天的工夫,捡得石块,垒起石墙,替她栽种这一片竹林,说是可以防老。奶奶常说感念兄弟的亲情,又说庄稼地里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天不会凭白无故给你收获,便更加珍惜这片竹林。因为竹荫遮日,草木难生,除草松土之类的工作是可免的,但是正因如此,地块容易板结,需要不断追土施肥,猪牛之类圈栏肥舍不得,她就常年挖阴沟里的肥泥,捡烂草秆,拾地上的畜粪,给它追肥。我常见到竹林经年绿黝黝地发黑,绿意被亲情包裹着。
八十年代,邻居在竹林旁边的地里种了很多橘子,由于很少莳弄或者缺乏经验的缘故,每一年总是稀稀拉拉地结几个青黄的果实。正月里相聚,她们便责怪我家竹林掩映,遮了橘子林的阳光。奶奶听说也没分辩,回去就默默地斫了它们,改作种植金柑。当时我想着竹子给我买书的便捷,硬舍不得,拦着阻着。奶奶说:“竹笋可积小钞票,金柑也可积,而且你能品尝到甜美的口味呢。小钞票重要,远亲不如近邻,亲情更重要呢!”我于是默默离开了,看着它的被砍伐直觉得心里酸楚。真舍不得呢!
三年前,为生活劳碌奔波而远离家乡的我,偶然回家,看着家里仍然略显得贫穷的景况,总想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从方家岙进一车的雷竹娘,种植在老地方,现在已经郁郁葱葱,铺满面积不大的自留地,奶奶说今年出的第一株笋,能卖到十二元钱一斤呢!我听了心里不禁感到一丝甜甜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