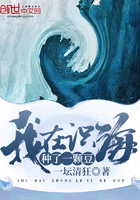杜奇嗤笑道:“是谁想去啊,是谁说的等我满了十六岁带我去开荤啊?明明是自己想去又不好意思说,老是拿我来当晃子,还假正经。”
姚富贵道:“什么假正经真正经,这叫此一时彼一时也,再说了,我老人家要去还怕谁说三道四?就你小子鬼心眼多,你倒底去不去啊?”
杜奇跳起来边换衣服边嚷道:“去,去,怎么能不出去呢?穿帮服未免有点惊世骇俗了,看来只好穿新衣服将就点,我们爷儿俩先出去吃顿好的再说。”
姚富贵也急忙跟着换上最好的衣服,看见杜奇正要走将出去,叫道:“等等,我老人家可跑不过你。”
杜奇叫道:“快点啊,再晚就没得吃了。”
姚富贵把那叠银票藏在墙角的稻草中,忿道:“就知道催,慌什么慌?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两人来到大街上,但见街灯闪烁,人来车往摩肩接踵好不热闹。来到市中心,杜奇看着四周大大小小的酒楼饭馆,问姚富贵道:“贵叔,我们去哪家饭馆用餐?”
姚富贵失笑道:“用什么餐?说话不要这么文绉绉地好不好,弄得我老人家的牙都酸酸的,你知道老子最爱吃阳春面,就一人来两碗吃个饱!”
杜奇哂道:“阳春面确是好东西,以前想也不敢想,不过今天我们却不用急着去吃它,先去弄两个小菜,我们爷儿俩喝两杯。”
姚富贵闻言不由瞪大了一对老眼,舔了一下嘴唇,吞了一口唾沫,似有点艰难地道:“我老人家有好久没喝过酒了,现在被你一说把酒虫勾了出来更想弄点来解馋,但你还小不宜喝酒,我们还是简单地弄两个小菜来尝尝算了。”
杜奇不依,找了间不大不小的饭馆,硬拉着姚富贵走了进去,一个店小二忙堆起笑脸,殷勤地上前招呼道:“哟,难得杜公子光临,请楼上坐!”
那店小二话虽如此,但站在杜奇前面却没有让路的意思,杜奇早瞄准角落里的一张空桌,好意地道:“你去忙,我们自己去那边坐。”
那店小二仍站在原地,挡在杜奇的面前,脸上挂着职业式的笑意,淡淡地道:“请问杜公子准备吃点什么呢?”
杜奇这才发现那店小二的异样,心中虽然不快,却并不表现出来,掏出那一两重的银子砸在那店小二的手里,微笑道:“不要以为老子是来吃白食的,这个你先拿着,来四个菜一壶酒,都要你们店里最好的,然后一文不少地把剩余的钱算还给老子。”
那店小二掂了掂手中的银子,确认不假之后才又堆起分不清真伪的笑容,客气而热情地将二人往里引去,找了张空桌让两人坐下。
酒菜上桌,两人毫不顾及形象,似作战般狼吞虎咽,杜奇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却也能与姚富贵杯来盏往喝个不亦乐乎,不停地连连呼叫“痛快!”。
只片刻时光,桌上的酒菜就被一扫而空,两人意犹未已,忽见一人急急地赶来,还隔着老远就叫道:“杜公子,万舵主请你马上去见他。”
杜奇见来人是刚分手不久的谢相法,不由大感讶异,走到门外无人处问道:“是谢大叔啊,可知万舵主找我有何事?”
谢相法四下看了看,见无人注意他们,仍凑到杜奇的耳旁,用只能让杜奇听到的声音道:“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好象是有什么事需要与公子商量。”
杜奇心中明了,不敢耽搁,把剩余找回的银钱和钱袋一古脑地交给姚富贵,与姚富贵互道珍重后立马随谢相法去见万长青。
万长青早在一间小偏房内等候,见到杜奇,忙道:“公子请恕属下打扰之罪,可事非得已,万望公子莫怪。”
杜奇心想你都说完了叫我说什么,我既然答应你当那什么供奉,自然一切听你的安排,便道:“万舵主不要自责,有事请吩咐。”
万长青忙道:“属下不敢,这事本想等明天再向公子禀报请公子定夺,可事情紧急,今晚必须出发,所以属下才冒昧请公子前来。”
杜奇道:“到底是什么事呢?”
万长青道:“是一件护送客人远行的任务,那客人指明要公子随行,如果公子不愿意去,属下便推掉即可。”
杜奇心想如果真能如此你们又何必找我,还给我一个供奉来当?口中却淡淡地道:“可知那客人的身份来历,将去何处?”
万长青道:“是京城一大户人家的管家,说是准备回京。”
杜奇道:“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万长青道:“如果公子愿意,现在去见过客人后便可出发。”
杜奇道:“我走后,烦请万舵主用心照顾照顾贵叔如何?”
万长青忙道:“属下必定不敢稍怠,公子不用心。”
杜奇和谢相法跟在万长青的身后,来到一间大厅,厅内已有不少人。杜奇被万长青领到主位首座坐下,这时他才有时间和心情打量厅内情形。
紧挨着他下首坐着一位胸前绣有六个金马蹄的年轻汉子,坐在那里似是比坐在他旁边的万长青更有气势,谢相法坐在万长青的下手,硬比其他人高出一截,颇有鹤立鸡群的模样。
他对面的椅子上端坐着一位身着淡黄衫裤的秀丽女孩子,大约十三四岁的年纪。杜奇乍见她的面容,不由瞪大了眼睛,一颗心更是激荡地跳动起来,她正是杜奇曾在渡口见过且令他念念不忘的那位美丽小姑娘。她的旁边坐着一位老儒生,杜奇乍一见到那老儒生,更不由暗惊,那正是他和姚富贵今早跟蹑过的肥羊,他的下首坐着五个镖师模样的汉子,杜奇认得那五个人都是这对面襄阳镖局内有名的镖师,领头的那位名叫方正明,人称“平山刀”,手中刀威振襄阳,鲜逢敌手,其余四人都是江湖中的一流好手。
杜奇发觉那小姑娘一直似笑非笑、似嗔非嗔地瞧着自己,心中暗道:“难道这小娘匹也看上了老子,所以才暗耍手段准备把老子弄回家去?”
杜奇正思量间,忽听万长青道:“由于事情紧急,必须漏夜起程,所以才急着把大家请到一块商量有关事谊。”
那老儒生道:“请万舵主布置各人的任务,其它的事我们上路以后再说。”他虽然极力装出平静的样子,但杜奇却看出他心中焦急万分,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又不便多问,只好把一切藏在心中。
万长青正容道:“本帮三人:供奉杜奇,巡护刘桤,管事谢相法,一切任务皆由阁下安排。”那五个襄阳镖局的镖师自是那老儒生另外聘请的保镖,其任务自当由那老儒生安排。
杜奇估计那老儒生就是什么京城大户人家的管家,却不知那姑娘是什么人,但他知道自己只要跟着身旁的马车就行了。
那姑娘坐在马车中,车由谢相法驾驶,其余众人皆骑马相随,在夜禁前即将关闭城门的那一瞬间经过关检,奔出“拱宸门”,马不停蹄地涌向码头。
夜沉沉,车辚辚,马萧萧,走在熟悉的道路上,杜奇忽然感到十分陌生,在暗淡的月光下隐约看到前方江面上黑压压的舟船,嗅着江水的气味,想到即将远行,虽然早已心驰神往,但他的心还是跳荡得十分厉害,感到既神秘刺激,又紧张不安,还有一丝莫名的兴奋,也有一点无端的失落。
正行间,杜奇忽听一束悦耳至极的声音低唤道:“喂,喂,公子!”
杜奇循声望去,只见那黄衣姑娘正透过车窗向他招手,对此,杜奇颇感意外,一时又不由心神激荡,忙驱马来到车窗旁问道:“姑娘是在叫我吗?”
那黄衣姑娘道:“是啊,公子真的是骆马帮的供奉吗?”
杜奇奇道:“你不知道?”
那黄衣姑娘低声道:“你小声点不行吗?我知道什么?你会武功吗?”
杜奇闻言不由迷糊起来,原来自己当供奉的事她并不知情,难道是那老儒生暗中搞的鬼?想来定是如此,于是低声借用一句套话,虚应事故地应付道:“浪得虚名,不值得一提。”
那黄衣姑娘释然道:“原来你真的很有名啊,那么你的绰号叫什么呢?”
杜奇闻言不由心中一乐,笑道:“我的绰号挺长的,不太好记。”
那黄衣姑娘好奇地道:“吓人不?告诉我好不好?”
杜奇想了想道:“说起我这绰号,还真的有点吓人,听别人说专门有人拿来吓唬晚上啼哭不休的小孩儿。”
那黄衣姑娘兴奋道:“真能止小儿夜啼啊?快说来听听!”
杜奇道:“你真的想知道?”
那黄衣姑娘点头道:“当然,否则我又何必问你?”
杜奇忍住笑,正色道:“你记好了,我的绰号是:拳击五行脚踏三界独闯三十三重天的霹雳五彩玄龙成黄易天傲世大真人。”
那黄衣姑娘“扑哧”笑道:“确实够长的,却未见得怎样吓人,嗯,也还挺有意思的,大真人!”
杜奇暗道,瞎掰的你也信?还当真的来分析一通,老子本来不想骗你的,你偏要挤过来让老子骗骗,看来老子骗人的道行越来越精深了,当即随口问道:“你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又回城里来了?”
那黄衣姑娘道:“我只是去接人,早回城了,到哩!”
杜奇这才发现已至江边码头,只好暂时把想问的话吞回肚中,随众人正欲奔上就近的渡船,忽听得那老儒生道:“上那艘插有黄旗的渡船,快!”
众人闻言,不由望向江边众舟船,见下游不远处的一艘渡船上有一面小小的黄色旗帜孤独地在两根火把间的暗影里跳动,如果不是有心相寻,根本不易发现。那老儒生说着,领先向那艘渡船驰去,众人无奈,只好跟在那老儒生身后登上那条渡船,众人刚上船停好车马聚在一处,渡船便飘向江心。
随着渡船的启动,杜奇的心猛地一紧,似跟着这渡船的飘离江岸而离开襄阳飘向他方,一时之间漫无着落,空荡荡的满不是滋味。
船到江心,忽然一阵江风刮过,船上的火炬光焰一阵起伏摇晃,船上顿时阴暗明灭不定。就在最暗的那一瞬间,杜奇蓦地发觉一条人影似一道闪电般由船仓暗处窜进由谢相法驾驶的马车中,众人皆似未觉。
虽在惊鸿一瞥间,杜奇仍然清楚地看见那人身着白衣,头戴重纱覆面,身材小巧玲珑,显是一年少女子。杜奇正欲向众人示警,忽听车中那黄衣姑娘喜悦地低声叫道:“小姐,你怎么才来啊?”
另一丝声音道:“我早想上车,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那个少年是什么人?”这声音比那黄衣姑娘的声音更为清脆悦耳,杜奇估计那是个与那黄衣姑娘差不多大小的姑娘,听那黄衣姑娘的称呼,显然这位姑娘才是此行的正主,只不知刘桤、谢相法事前是否知道?
那黄衣姑娘应道:“是骆马帮的供奉,好象挺有本事的。”
另一姑娘道:“什么好象挺有本事的,刚才我上车时,被他锐利得如有实质的目光扫了一下,到现在我还寒气直冒,真想不到他那么年少修为就那么精深,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黄衣姑娘天真地道:“他真的很厉害啊?想来他的绰号定是真的了。”
原来她也并未尽信杜奇瞎扯的绰号,另一位姑娘问道:“什么绰号?”
黄衣姑娘道:“他说他的绰号叫什么拳击五行脚踏三界独闯三十三重天的霹雳五彩玄龙成黄易天傲世大真人,你说这绰号长不长,有意思不?”
杜奇不由暗笑,自己都不一定能重复的那所谓“绰号”,想不到她居然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真难为她了。另一姑娘笑道:“哪有这样的绰号?这分是他胡乱编来骗你开心的,到现在他还不一定能记住,真亏你还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