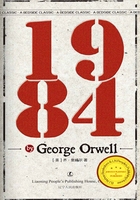章第中趁周末请假回了趟榆树坡。
他径直找到大伯家,“老大,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花儿唱得特别好?”他知道在父辈当中,大伯不仅经历的艰难最多(比如下陕西当过麦客),而且跟爷爷生活的时间长一些(比如跟爷爷跑脚去过省城),对爷爷了解也更深一些。
大伯不满地看着侄子,“你不好好念书,问这些闲事做啥?”
“啥闲事啊!我们课堂上都讲花儿呢。”
“你说啥?”大伯很惊奇,“学校里也给学生漫花儿?”
“对。花儿迟早要成国宝的,像京戏那样。”章第中夸大其辞。
大伯疑惑地低了头,吧吧吸着旱烟锅思想什么,将皱纹缠绕的脸面和华发覆盖的头颅笼罩在朦胧之中,吸得屋子里弥漫了呛人的烟雾时,突然梗起脖颈,用嘶哑的嗓子唱道:
韭叶镰刀打一张
陕西坝里赶麦场
不是哥哥爱赶场
光阴穷者没法想
……
调子细嚼慢咽,悠扬凄婉,只不知为何刚开头就煞了尾,可大伯好像唱累了,双眼微闭,神情黯然。章第中没料到平日蔫兮兮的大伯竟藏着这一手,早惊得有几分呆了。忽听大妈在院里说:“你个老不死的,跟娃娃胡唱啥呢?”
大伯在炕边上一下一下磕掉烟灰,满脸严肃地说:“还能唱啥?唱往蛮年的苦歌,娃娃听了也不懂!”
“那我奶奶去世的前几年,唱的也是这些苦歌了?”章第中说。
大伯愣了,闷闷地想了想,然后默然点头,有泪花从眼角涌出。
大妈倒接过话茬儿,“人心里的苦啊,有啥歌能唱得出来呢?”大妈的嗓门像人一样五大三粗,“你奶奶一辈子嫁过俩男人,可俩男人除了生下四儿一女五个娃娃,都没能陪她走出头!”
泪水从大伯脸上潸然而下了。
章第中知道,大伯的泪水里,包含了对奶奶的真切怀念和无尽痛惜——
奶奶是生下大爷爷遗腹子的第二个秋天,在太爷爷的主持下跟爷爷结婚的。大爷爷求学之路上的猝然惨死,给了家庭毁灭性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太奶奶悲伤过度,几月功夫含恨而死。太爷爷虽然坚强些,也卧病在床百医无效,自觉将不久于人世,才苦口婆心劝说和督促爷爷跟奶奶拜堂成了亲。
可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十多年之后,奶奶又一次成了寡妇,并且肚子里也怀着孩子,六个月大的孩子!——奶奶越到老年,越对自己的遭遇伤心不已,叹息,痛哭,惊梦,诅咒……可归根到底,奶奶又认为是她的命太硬,不仅克死了两个丈夫,两个兄弟,而且也拖累两个儿子连亲生父亲的面都没能见上。
奶奶说的两个孩子,一个是章第中二伯,一个是章第中父亲。
提起没能见到爷爷这件事,父亲章太华更痛惜不已,觉得是人世间最难弥补的遗憾,“你爷爷死得可怜啊,为了全家人活命,他不明不白走上了死路。”
而对爷爷的死,二伯和大伯更多是内疚,“老人家是被我们哥俩给拖累死的。”
章第中不知道哪种说法更符合事实,私下请教过三伯。三伯认为两种说法都有些道理,“反正啊,你爷爷死了几十年了,说起来只能惹后辈伤心。”
爷爷是一九六零年死在他跑过脚行的驿道上的。
经历连续变故的章家,几乎陪耗光了全部底气,在埋葬太爷爷之后,爷爷不得不重新拾起祖上的行当,替别人做跑脚伙计……轰轰烈烈的土改中,章家被划成了贫农,应该属于革命的中坚力量吧。然而不幸的是,大爷爷为章家埋下了难以拔除的祸根——他就读省城师范期间,经老师介绍,以班级的名义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那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这无疑是糟糕不过的尾巴了。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大爷爷,虽然早已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得灰飞烟灭,可他的两个儿子,即章第中的大伯和二伯,却由爷爷和奶奶抚养在身边,何况奶奶是这两个儿子的母亲,是大爷爷曾经的结发妻子……榆树坡新兴的当权者明察秋毫,很快采取断然措施,在攸关性命的食物配给上提高坎儿,没了两个“狗崽子”的份。当时三伯和姑姑也七八岁了,全家人合起来六张口,却隔三差五只能领到四份定量粮,食不裹腹饥肠辘辘,不时面临断炊的威胁。庄里庄外的树皮都剥吃殆尽,白花花立在太阳底下,邻近庄子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爷爷毕竟是脚行出身,见多识广,又在大爷爷的熏陶下识文断字,头脑比一般人更活便,不愿睁着双眼坐以待毙,于是瞅机会偷偷出了门,想沿着当年跑脚的路线找熟人碰碰运气,为儿女觅一点苟延残喘的食物。
爷爷压根儿不知道,他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
二十多天后的某个夜晚,有个行色匆匆的中年人潜入榆树坡,自称是爷爷的脚友,砸给奶奶一个惊天噩耗:爷爷死了!
关于爷爷究竟是怎么死的,几十年来始终悬而未决。据爷爷的脚友说,爷爷死的前几天还在他家吃过两碗糠菜团子,然后继续顺古驿道去寻找食物了。可当时的西北山区,哪里还有家存余粮的地方呢?爷爷的脚友曾劝爷爷就地折回,即使饿死也能跟家里人在一起,可爷爷感谢并作别了他的脚友。
几天以后,爷爷的脚友听庄里风传,后塆垴死了一个外地人。爷爷的脚友有预感似的,急忙赶到后塆去,确认死者正是爷爷,尸体已经有了异味,无数绿头大苍蝇旋起旋落,嗡嗡乱叫。爷爷的脚友考虑了一下,回家拿了把铁锨,纹丝不曾挪动尸体,原地挖黄土掩埋了。
爷爷的脚友冒险给奶奶报了凶信。
这一年,爷爷才三十刚过;而奶奶,还不到四十岁。
“可怜的奶奶啊,是咋活过来的!”章第中泪流满面。
白发苍苍的大伯眼睛红红的,湿湿的,孩子般只是点头。
“你们得知爷爷的死讯后去上过坟吗?”章第中问。
“那时候奶奶正怀着你爸爸,走不动;你姑姑还小,我跟你二大领着你三大去的。”大伯说。
“没想过把爷爷的坟迁回榆树坡吗?”章第中又问。
“想过。可没迁成。”大伯说。
“为啥?落叶归根哩!——”
“这娃娃,真像个高中生了,叽叽喳喳那么多问不完的事。”大妈已经做熟了章第中最喜欢的洋芋糊糊面,热腾腾端上桌,“快吃吧,明天要赶着回学校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