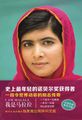“此一时,彼一时也!”祖象升把茶盏一放,激昂慷慨地,“当时,皇太极初登汗位,羽翼未丰、国力不强,百姓缺衣少食,皇太极故有议和之意;而今,夷虏称帝,东征朝鲜,西灭蒙古,又数次入关掠我大批财物,其国力已十倍于前!皇太极历来野心勃勃,意欲图我中原,此番又挥兵南下,连破我数城,他怎肯甘休罢手呢?再则,前些时皇太极主动议和,遭我拒绝,皇太极已恼羞成怒,在此情况下,如我因战败而议和,必然割地偿银,大明将名誉、财物、人心、土地尽失!况且皇太极已得传国玉玺,志在吞我大明江山,做中原之主,即使此刻他应允议和,也必是“佯和而实战”!放松我朝戒备,更利于他侵吞中原!”
崇祯连连点头:“依爱卿之见?”
“至今,唯有中原逐鹿,拼死一战,方可保我江山社稷!”
祖爱卿所言,正合朕意!”崇祯听着祖象升那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大受鼓舞,情绪也随之振奋起来:“请教先生,此次中原决战,如要聚歼满夷,需得多少兵马?”
祖象升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此次多尔衮所率清兵共计十三万,我方如能调集三十万兵马,可一举全歼;二十万兵马,虽不能全歼,但可大胜;十五万兵马,则也可驱逐清兵,获取小胜,但最低不能少于十万兵马!”
“朕当然要一举全歼!”崇祯兴奋地走到剑架前,拿起尚方宝剑,递给祖象升,“朕特赐你这柄尚方宝剑,统领全国三十万人马!一切便宜行事!来人!”
秉笔太监王承恩应声入内。
“传旨温体仁,十日内调齐南京、山东、宣府、大同三十万兵马,归祖将军统辖。十五日后决战中原!”
祖象升伏地泣拜:“臣定将喋血沙场,决一死战!”
熙春院里一所幽静的包厢内,毛云龙正拥着两位美姬在饮酒。这是个不谙政事的风流情种,昨晚本想借为祖象升接风之机尽情淫乐一番,但谁知那个油盐不进的家伙不仅扫兴,自己又反被温体仁骂了个狗血喷头。今晚他要彻底冲冲这股晦气,他特意将昨晚那两名美女找来,左拥右抱、极尽淫邪。当他扯去一名美姬的外衣,正欲将手伸进这美女兜褂时,突地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毛大人,户部尚书陈演陈大人来了!”
“快请进!”毛云龙连忙推开美姬,站起迎接。并随即将其中的一位美女拉到陈演的跟前:“等你许久了。快,陈大人,来一道享此人间尤物!”
陈演虽也是个贪恋女色之徒,每次到此熙春院都纵情放浪、不拘形迹。可这次,面对迎风杨柳般袅娜轻盈的美艳秀色,他却伸出双手阻拒道:“毛兄,为粮草事陈某正火烧眉毛,哪有时间来此处消遣?”
“忙里偷闲嘛!”毛云龙见陈演愁眉紧蹙,一脸阴霾,便示意美姬离开,关紧房门,“陈大人自从妥娘嫁给洪承畴后,再没来过吧?”
“圣上令十日内为祖象升筹齐三十万兵马的粮草,陈某现今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啊!”
“卑职正是为此,才借此密室与陈大人谈几句私房贴心话。”
“噢?”陈演一愣。
“陈大人请坐!”毛云龙为陈演斟上酒,“说起祖象升,陈大人印象如何?”
“此人不同凡响!皇上八天之内,连着两次赐授尚方宝剑,本朝决无仅有!”陈演呷了口酒,侃侃谈道,“老夫细细想过,祖象升的确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有胆有识,勇于任事,朝野上下,有口皆碑,是位忠于国,孝于家,诚于友,能于军,守其正,全其节,仁义天下的将才帅才啊!”
“可有一点,他不是首辅温大人的人。”毛云龙冷冷地插了一句。
“这……?”陈演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前些时,不是听说温大人在圣上面前表示要摒除私见,尽释前嫌,与祖将军精诚合作,共退满虏吗?”
毛云龙把手中的酒杯一放,余怒未消说道:“温大人本想尽释前嫌,与祖象升修好。温大人为此在这里隆重设宴,亲自布置、亲自过问。当朝首辅屈尊如此,应是给足了祖象升面子了吧?可他竟然不识抬举,来了个麻衣拒宴!”
“那温大人让你找我的意思……?”陈演是个极会察言观色、见风转舵的角色,他一面目视着毛云龙,一面急速地沉思着。
“祖象升桀骛不驯、狂妄至极!现今仗还没打,就如此不把温大人放在眼里面,若是一旦成功,全歼满贼,实现大明中兴,那时功可齐天的祖象升,朝廷还容得下他吗?”毛云龙狠狠地用鹰一样目光盯视着陈演。
陈演怵然一惊!
野外。风雪肆虐,被吹折的枯木断枝,在风雪中挣扎。
衣衫单薄的士兵,一个个地从外面抱着雪块走进营帐……
范景文不由得停下脚步,怔怔地看着他们。
进到祖象升帐内,范景文好奇地问道:“祖大人,那些士兵往帐内抱雪做什么?”
“煮水充饥啊!”
“用雪煮水充饥?”范景文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皇上的十日期限已过,可陈演调集的粮草却一粒未到。将士们粮秣已尽,唯有如此了!”
“岂有此理!陈演这不是违抗圣命吗?”范景文愤然说道。
“他是奉温体仁之命,把粮草全部转往关东了!”
“又是温体仁?又是关东?”范景文喟叹地:“范某此番也是有辱使命,甚为愧疚,特来向祖大人致歉的!”说着,施以大礼。
祖象升慌忙扶起:“这是为何?”
“皇太极为策应多尔衮进犯中原,亲率大兵袭击关外,致使已经调集的关宁五万人马,被温体仁统统扣住,无法前来与祖大人会合。范某办事不力,无颜再见祖兄啊!”
谁想祖象升竟平静如初:“此已在我意料之中!”
“怎么祖兄早知如此?”
“大同、宣府的十万兵马已先被截留了!”
范景文更为惊讶:“大同、宣府的十万兵马也没来报到?这是为何?”
“拱卫京师去了。”
“那大人手下,现有多少兵马?”
“两万。”
“才两万?”范景文激愤地叫了起来,“名为中原决战,十日期限已到,却将兵马纷纷调离。大战在即,怎么能全歼清兵?怎么能大获全胜?请问祖大人,这调令,是不是又出自老贼温体仁之手?”
“除他,谁能有权有胆改变圣意?”
“难道这些都有皇上旨意?”
“温体仁一向巧舌如簧。他以拱卫京师、解京师之危为名,圣上焉能不允?”
“这明明是釜底抽薪,以报私怨嘛!皇上圣明如此,怎么竟然连这点都看不出呢!”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嘛!一听说皇太极进犯京师,满朝文武均谈虎变色,惶惶不安,温体仁便可私售其奸了!”
范景文长哀叹一声:“那现今,唯有指望南京一路的十万兵马了!”
“南京今晨倒送来军报,说十万兵马已集结完毕,明晨即可启程。
“从南京到这里,需要多少时辰?”
“只需两日。”祖象升自我宽慰地:“有南京这十万兵马,虽不能全歼清兵,总可以和多尔衮为之一战!”
谢尚政自出卖袁崇焕得以娶妻进爵后,京师已无法驻足,经过温体仁的斡旋筹划,谢尚政得以迁移南京就兵部侍郎职。依照圣谕,明日一早将率十万兵马起程北上,参加中原决战,故今夜谢尚政早早便已脱衣入睡。因此次战事系明清的生死决战,加之这又是两人婚后的第一次远别,所以滢儿今晚极尽温存缠绵,以致引逗得谢尚政兴致勃发、翻身上马、正欲一展雄风之时,突地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谢尚政本想不予理睬,可谁知外面的敲门声又重新响起。谢尚政不情愿地坐起身来,厉声喝道:“谁?”
门外答道:“大人,是我,毛管家。”
“什么事?”这次是滢儿的声音。
“有人来拜访谢大人。”
“这么晚,还来打搅?你不知谢大人明晨天不亮就卒兵进发中原,需好生休息吗?”滢儿颇为生气。
“是,夫人。可客人是从北京星夜赶来的,说有紧急公事。”
“北京来的?”谢尚政插言,“是什么人?”
“首辅温大人派来的毛云龙毛大人。”
“哟!是二叔!”谢尚政一听是毛云龙,顿时怒气全消,他慌忙地边穿衣边说道,“快请至客厅稍候!”
待谢尚政来到客厅时,毛云龙正悠闲地坐在那里喝茶等候,及见谢尚政后方站起拱手致礼:“深夜打扰,实为冒昧!因公务紧急,实在是万不得已。”
“哪里!”谢尚政慌忙还礼,“二叔千里跋涉,侄婿怠慢不恭了!不知此时前来,有何见教,”
“温大人受命皇恩,十分关注中原决战的进展,不知尚政的十万兵马筹措如何?”
“请转告温大人,我已遵旨调齐十万精兵,明日一早启程,两日内便可抵达,投入中原决战。”
“此去,当可全胜喽?”
“军兵士气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坚甲利兵,士饱马腾,相信此仗定可大胜!”
“尚政想过没有,大胜之后,会是如何呢?”
“全歼满夷,永绝外患!当可实现皇上宏愿:国泰民安,大明得以中兴!”
“功莫大矣!”毛云龙望着激动的谢尚政,狡黠道,“可尚政是否想过,这功将记在何人身上?”
“身为大明朝臣,一切皆为圣上效命,我岂能尚未出师就斤斤计较功禄?”谢尚政对毛云龙的问话,怫然不悦。
毛云龙没有理会他,径自说道:“别忘了,此次统率全国兵马的主帅是祖象升。”
“这又有什么?祖象升是我共事多年的袍泽,情同手足。”
“说句知心的话,恐怕与祖象升更情同手足的是袁崇焕吧?”毛云龙又阴冷地甩了一句。
“这是何意?请明示。”谢尚政对毛云龙的阴阳怪气甚为不解,他不满地追问了一句。
“试想想,此次中原决战,如大败清兵,大明中兴,这再造江山之盖世首功,当祖象升莫属,祖象升是个不计较功名利禄之人,最看重的当属情义!昔日他冒死违背圣命,领兵出走,继之回师京城,可又抛舍军功;后又擅自脱离边关,跑到北京寻衅刺杀你谢大人和温大人:再之后他又弃官而去……上述种种,都是为了替袁崇焕鸣冤!他对袁案,一直耿耿于怀,如若此次决战得逞,便功可齐天,到那时,他能不为袁崇焕翻案吗?袁案一翻,追究罪源,首先遭杀身之祸的,一为温体仁温大人,另一个就将是你了!”
出卖袁崇焕,这是谢尚政人生中最为愧疚、最见不得人的丑行。谢尚政常常为此而夜间惊醒、头冒冷汗。谢尚政不是那种敢作敢为、阴险毒辣之人,他几年来一直想瞒天过海、首鼠两端,乞望人们忘掉这桩记忆。可怎知今天是怕鬼偏见鬼,遇上这个一心要为袁崇焕鸣冤报仇的祖象升!他听完毛云龙这番话以后,就连握着茶杯的手,竟也不由得颤抖起来,他连连擦拭着头上流出的虚汗,只觉得浑身骨酥筋软。
这时,一直躲在里间聆听的滢儿,一掀帘子走了出来,问道:“二叔,事到如今,您说我们该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