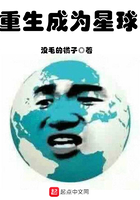大年初一的早晨,成雨妃便早早地被姐姐和姐夫硬拉着加入了他们的“团拜会”,实在推脱不过,她只好随他们一起走下楼来。
他们的第一站是去姐夫的大表姐殷夏家。殷夏曾经是一位红极一时的名模,在天津有着“五朵金花之首”的美称。五年前下海经商,凭着一副颀长迷人的身材和满脑子精灵古怪的掘宝奇术,横扫圈内一切劲敌。于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如同流水般地滚进了她家的保险箱,她家的豪华程度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差搬架飞机回去摆着了。
来到殷夏家的楼前,姐夫忽然喜滋滋地转过头来说:“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咱们不去表姐家啦,由我上去把她叫下来,让她请我们出去消费那多过瘾!”
说罢,他便将车停好,自顾跳下车,乐颠颠地向楼里跑去。
走上三楼,他径直来到表姐家的门前,伸手连连摁着门铃。
“谁呀?”里边传来表姐恶声恶气的声音。
“是我,表姐。”殷夏听出是表弟的声音,这才气呼呼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过去将门打开。
“过年——”不待表弟将“好”字说出口,她便又气哼哼地扭身走了回去。
成雨妃的姐夫咂咂嘴巴,跟着笑嘻嘻地坐到了她的身边:“这大过年的,你这只母老虎又在向谁发威?”
殷夏也不说话,自顾阴沉着脸,将自己的一副花容月貌气成了猪肝色。
成雨妃的姐夫连忙伸出右手往上托了一下她的下巴,嘻嘻笑道:“省得掉下来。”
殷夏不但没有被他逗笑,反而更加生气地将脸扭向一边,左腿紧跟着翘在右腿上,甩给表弟一个斜后背。
“唔!”成雨妃的姐夫伸出手指刮了刮自己的下巴,抬起眼睛瞄着坐在对面沙发上一言不发的表姐夫。
表姐夫这才起身递过来一支烟:“二爷,吸烟。”
“二爷”伸手将烟接过,笑着问他:“这又是怎么了?”
“唁!”表姐夫连连摇头叹着气,“不就是因为我给我妈买了一条项链嘛!”
“什么?不就是一条项链!”殷夏立即横眉立目地转过脸来尖着嗓门嚷道:“你说说,你买的是一条什么项链?钻石的!你妈的,拿着我的钱给那个老不死的买钻石项链,68000块哪!她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能戴出朵花来不成?你倒扳着不心疼的牙,你干脆回去和你妈过好了!”
她越说越生气,竟“呼”地站起身来,走到靠着小卧室的梳妆台前,一把抓起放在上面的那些珠宝首饰,奋力地扔了出去。就听“哗”的一声,那些首饰像天女散花般地撒落在了屋中的各个角落。
她的丈夫见状,连忙走过去蹲在地上往回捡,一边捡还一边回过头来叫着表弟:“二爷,快,过来帮忙。”
“二爷”皱着眉头,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极不情愿地走过去帮他一起捡着。这时,就见表姐夫整个人都趴在了地上,龇牙咧嘴地伸长了胳膊,使劲地够着那枚滚落在沙发角里的钻戒:“二爷”也正猫着腰,把头伸到了饭桌底下……
等两人将那些首饰全部捡起,重新按原样放回到梳妆台上之后,“二爷”连连呼着气,从茶几上拾起一张面巾纸擦着手,一边径直走到衣架前,将殷夏那件雪白的貂皮大衣取了下来,递到她的面前:“快点穿吧,燕子和老妹还在楼下等着呢。”
殷夏将大衣接过去穿在了身上,嘴里仍余气未消地嘟囔着,“二爷”见状连声笑道:“这下,母老虎变成北极熊了!”一边又侧过脸去对表姐夫说:“表姐夫,你也快换衣服,一起去。”
“不准他去!”殷夏立刻又横眉立目地转过头来阻止,她一边系着大衣纽扣,一边低声骂道:“瞧他那副矬德行,我怎么看怎么堵心,准是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妈被日本鬼子强暴过才生出他这么个矬墩子来的。”
尽管殷夏后边的话近乎耳语,还是被她丈夫听得真真切切,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冲着殷夏破口大骂:“那你妈就是被八国联军强暴过才生出你这根电线杆子来的!”
“放你妈的屁!”殷夏随手抓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照着丈夫的脑袋便狠命地砸了过去。
丈夫躲闪不及,那手机不偏不倚,正砸在了他的额头上。那个地方立即便鼓起了一个大包,他伸手一摸,正触着那痛处,心中立即窜出一团扼制不住的怒火,只见他怒不可遏地直冲到妻子的面前,双脚一跳跳上沙发,又从那沙发上跳起,一把抓住妻子的头发举拳便打,殷夏立即尖叫着喊作一团。
“二爷”明明知道是表姐不对,可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吃亏,便连忙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了表姐夫扬起的那只暴起青筋的拳头。
表姐夫正在气头上,便没好气地说:“二子(”二爷“的乳名),这里没你的事,你最好少管!”
那“二爷”本来只是过来拉架的,只要不让表姐吃亏也就算了,哪里会想到表姐夫竟会把气撒到他的身上,他本来就是个性情中人,一见这情形,便也立即沉下脸来回敬道:“这事我管定了,你怎么着?把你的手放开!”说着便去掰表姐夫的手。
对方哪里肯放,抓着殷夏的头发左右躲闪着,殷夏疼得大哭起来,扯着嗓门又尖叫:“二子,打他!打这个矬王八蛋的!”
“二爷”粗着嗓门又问了一句:“你放不放?”
“不放!”表姐夫的话音未落,就听“啪”的一声,一记耳光重重地落在了他的脸上,直掮得他两眼直冒金星。
他放开了妻子,转身像只疯狗一样直冲着“二爷”扑了过来,两人立即扭作一团。
殷夏止住了哭声,抹了抹眼中的泪,看着丈夫和表弟从沙发上滚到地上,又从地上一直打到大卧室里的床上。这时,就见表弟整个人骑在了丈夫的身上,他的头却被丈夫紧紧地卡在腋下,表弟使劲地往外挣,丈夫拼命地向里卡,表弟情急之下抡起拳头猛擂丈夫干瘪的两肋,丈夫伸出双脚如暴风骤雨般地踢向表弟的肥臀……
她立即发了懵,不知该如何是好,少时,也顾不得自己新盘好的头发被丈夫扯成了乱鸡窝,转身扭搭扭搭下楼去了。
一见殷夏走出楼门,成雨燕连忙从车中迎了出来:“表姐您……”她的笑容在看清楚殷夏这一副狼狈相之后慢慢地凝固了,她立即变得紧张起来:“表姐,二子呢?”
“唔……”殷夏转过身抬起脸向自己家的窗户望了望。
“表姐,没出什么事吧?快说,二子呢?”
“唔……他……和你表姐夫,在上面打架呢。”
“啊?”成雨燕定了定神,连忙转身向楼里跑去。成雨妃紧跟着也跑了进去。
当俩人跑到殷夏家的门前,只见客厅的门大敞着,站在门外便能一眼看到地上那些被砸得粉碎的各种玻璃器皿和各种被踩得稀烂的水果。
成雨燕一脚跨进门坎,正看见丈夫骑在表姐夫的身上,满脸涨得通红,双手死死摁着表姐夫的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躺在地上的表姐夫被他摁得再也动弹不得,嘴里眼里呼呼地向外喷着怒气……
“二子,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成雨燕连忙将丈夫拉起来,又赶紧俯下身去将表姐夫扶了起来。
此时的表姐夫气得几乎要昏厥了,再也顾不得男人的尊严,竟然放声嚎啕大哭起来。
成雨燕好不容易才把他扶在了沙发上,一边拿过纸巾为他擦着粘在头发上的各种果汁,一边伸出手在他的胸前轻轻地为他顺着气,连声安慰道:“表姐夫,别这样!二子他不懂事,您别和他真生气。”
表姐夫委屈得什么似的:“燕子,你不知道这里的事。我……我……他们家太欺侮人……”话未说完,声音便哽咽了下去。
成雨燕连忙站起身来走进卫生间,将毛巾用热水烫好后拿出来递给了表姐夫。
表姐夫接过那热毛巾,顿觉一股酸楚又涌了上来,竟掩着脸在那毛巾后面又呜咽起来。
成雨燕转过脸去嗔了丈夫一眼,一边又连忙转回头来对表姐夫极尽好言地相劝着。许久,表姐夫才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将那毛巾从脸上拿开,仍旧带着哭腔道:“燕子,你说,她什么钱不花?我就只给我妈买了一条项链,她就这样!”
这时,成雨妃的目光恰巧停在梳妆台上的那些首饰上,她立刻明白了,这又是一出因为这些没有生命、没有灵魂却能将生为万物之灵的人玩于股掌之间的“破铜烂铁”而引发的闹剧。她不禁感觉有些好笑,她实在不明白,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好,竟能让那么多的人为它而痴迷癫狂,甚至是不要命。
“我花多少钱那是我的事,你拿我的钱给你妈买钻石项链就是不行!”殷夏不知何时也走了进来。
“那些钱我花了又怎么样?省得放在家里熏人!你的那些钱全他妈的是靠着卖得来的!”表姐夫立刻暴跳如雷地回敬道。
“是又怎么样?我倒卖给你十几年了,你又给过我多少钱?”殷夏寸步不让地反击道。
“表姐,少说两句吧!小妃还在这里呢。”成雨燕连连劝阻。
“呸,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死也别在天津死,你死了得臭八亩地!”就这样,夫妻俩你来我往地又是一场恶战。
成雨妃看看表姐夫那因极度气愤而变得扭曲的脸,再看看表姐那张如翻江倒海般涂抹的血红的唇,忽地,她感觉整间房子开始左右摇摆起来,接着又向她这边重重地倾了过来,最后,竟开始飞速地旋转着……她看见屋中那些金碧辉煌的装饰物和各种金灿灿的珠宝首饰,霎时都变成了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怪物,它们龇牙咧嘴地冲她狂笑着:“谁说我们没有生命?谁说我们没有灵魂?看看吧,人们为了我们不惜抛弃人格,葬送爱情,汩没是非!哈哈,我们才是这世界的主宰者呀……”
这场昏天黑地的恶战直到殷夏的一位深谙“周旋之道”的朋友的到来,方算告一段落。那人三言两语便将殷夏哄得眉开眼笑,两人在一旁又叽叽咕咕了一阵之后,殷夏立即便一脸春风地走到梳妆台前,重新快速将头发梳好,对着镜子左看右看之后,甚是满意地转过身来对表弟笑道:“二子,我们走!”说着话,又笑嘻嘻地一把拉起了成雨妃的手径直向门外走去。
刚走出门去,不知谁讲了一句笑话,整个楼道里顿时笑声飞扬。
成雨妃刚才还在想,表姐被自己的丈夫骂得那么难听,一定难过死、伤心死了,可现在一看到她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地和身边的人轻松地说笑着,时而还发出一阵阵开心的大笑,不禁为自己的幼稚感到可笑起来。
来到楼下,她再也不愿和他们同行,便撒谎道:“表姐,我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去老师家,我答应他今天过去看他的。”
“唔,这样啊!”殷夏凝目想了想,甚是有些抱歉地说道:“小妃啊,刚才实在对不起,没吓着你吧?”
成雨妃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就好,把这个拿着。”说着话,她便伸手将皮包的拉链打开,从里面摸出一沓100元的钞票来:“哎!高高兴兴来给表姐拜年,却白白受了这一场惊吓!来,把这个收好,给老师多买点贵重礼物送过去。”说着话,便招呼着她的司机去送成雨妃。
成雨妃也没加谦让,她知道殷夏的性格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路上,成雨妃忽然想起去年过春节前夕,杨云陪她去吉利大厦买新年礼物的情景——
她们俩在一楼的化妆柜里同时发现一个十分精致古朴的发卡,便让售货小姐拿出来看看。当俩人看清楚那发卡上面的标价是2998元时,杨云立即咋舌并低声道:“天哪,一个发卡要这么贵!又不是黄金做的!”
成雨妃正要说什么,售货小姐早已一脸傲慢地将那发卡收回,紧接着阴阳怪气地说道:“这要是黄金做的,就不会是这个价了!”
成雨妃见她竟是这种态度,心中十分不满,便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们说话,没你插嘴的份!你脾气这么大,怎么到这里来做售货员?干嘛不去美国做总统?”
售货小姐闻声,顿时将一张抹了厚厚一层粉底的、白里透青的脸涨得通红。
杨云见状,连忙将她拉去别的柜台,一边笑嘻嘻地劝慰:“小妃,别和那样的人一般计较。没听说过吗?就连主席夫人还曾因着装普通,被一个什么大饭店的门卫挡在门外不准入内呢!那个时候,那个小小的门卫怎么能想到人家就是第一夫人呢?这就像刚才那位售货小姐一样,她那双只认得钞票的眼睛,又怎么能看出相貌普通的我竟是将来一代文豪的闺中密友呢?嘻,小妃,把今天这事也写到你的文章里去吧,等将来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定会震颤她那脆弱的灵魂。”话音未落,两人便笑在了一处……
哎!那天,她买了好多的新年礼物,而杨云却始终两手空空,说那些东西没有一件适合自己。后来,她好像看上了一顶帽子,反复试戴了几次,连过往的顾客都忍不住夸奖她戴那帽子好看,可正当成雨妃决定要给她买下来时,她却在看到那贴在帽檐里边的订价不菲的标签之后,说什么都不肯让成雨妃到银台交款……
想到这里,成雨妃转过脸去吩咐司机将车直接开到了吉利大厦。
到了吉利大厦二楼,她按着记忆,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家帽子专柜,她一眼就看到,杨云去年试过的那种帽子依旧漂亮地挂在展台上。她不假思索地让售货小姐按那样式拿了一顶新的出来,付了款之后,便径直下楼回家了。
回到家中,她把那顶崭新的帽子放在自己的古筝前,然后沐手焚香,拜祭罢,挥泪两行,再次抚筝一曲《高山流水》。面前又映现出闺中好友的盈盈笑脸,这就使得她愈加的五内激荡,弹着弹着,竟猛然想起了那段令人怆然涕下之语: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
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第二天,她去恩师家拜年。天津的风俗,这一天是姑爷、姑娘回娘家的日子,成雨妃之所以年年选择在这一天去给恩师拜年,心中自然是将恩师、师母当成了自己的父母一般看待。
没想到这个新年,恩师竟是躺在床上度过的。二十九那晚,他一个人出去散步,不小心被井盖绊了一跤,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大好,加上近几年上了年纪,这一跤摔得他左半边脸全都肿了起来,左眼也眯成了一条缝。
成雨妃见状,甚是忧心忡忡地问长问短、关前照后,老先生却一脸轻松地连连摇着手说:“不碍事,不碍事!人老了,摔一两跤也是正常的事。”
成雨妃反倒无话可说,心头却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恰在这时,老先生又忽地想起了什么,接着说道:“小妃啊,该找个男朋友了!那样,等你结婚时,老师也好去做个证婚人。再不抓紧时间,老师可要走人喽。”
成雨妃听罢,再也忍不住,当下便哭了起来:“怎么说这样的话?你们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
那天,离开老师的家,她的心情真是沉重、压抑极了,一股无比的凄凉孤寂之感久久地盘踞在她的心头。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24岁了,是该找个男朋友的时候了!
她与纳兰熙的相识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