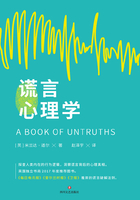鹂儿嘻嘻一笑,靠在云锦身边讨好道:“奴婢听说昨天晚上,皇后娘娘下旨罚陈雪玲抄《女则》十卷,面壁思过三月!虽然不知道陈雪玲如何惹恼了皇后娘娘,不过这件事城里都传开了!陈雪玲平日骄纵跋扈人尽皆知,如今皇后娘娘的旨意真是大快人心啊!”说罢,鹂儿崇敬地朝皇宫的方向拱了拱手。
云锦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尽管知道鹂儿还记着陈雪玲抢了她的包厢,不过皇后娘娘下这旨实在是轻轻放下,吃亏的还是她家姑娘她啊!云锦不由得失笑,看她一副言之未尽的模样,又问道:“你还打听到了什么?”
鹂儿这才神神秘秘地道:“奴婢听说,昨夜陈府都闹疯了!陈雪玲整夜在府里上蹿下跳,嚷嚷着自己撞见了鬼,闹得陈府一夜都不得安生,整个人就像疯魔了一样。今日一大早,陈家人就匆匆把她送到城郊宅子里去了!。”
“撞见了鬼?”难道是昨天落水迷了心智?云锦不由得想到。
但云锦不知道的是,昨日喝完酒走夜路的周家少爷,也被人蒙住脑袋打了个半死,此时正摊在床上哀嚎。而她英明神武的大哥,此时正拿着下属传来的消息发愁。他昨夜刚解决完陈雪玲,还没来得及对周家那小子下手,不知是谁先一步把他给打了!这让他怎好再对他下手?
而此时,某王府的某棵大树上,夜靠着树干,对身旁正在巡察的黑衣女人谄媚道:“止青,昨天我那一掌不错吧!有没有表现出一股地痞流氓的气质?”
那位叫做止青的身材高挑、身段火辣的黑衣女子白了夜一眼,伸手往他手臂上用力一按,讽刺道:“你身为王府一等暗卫,去教训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最后还带着伤回来,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真是丢脸!”
夜揉了揉手臂上一条血痕,张牙舞爪道:“谁知道那小子居然跟泼妇一样,伸手就挠人!”说罢,气势又矮了一截,委屈道:“再说,王爷也吩咐,给那小子留一口气,否则我也不会这样束手束脚。我可是不想再回望月阁思过了。”
止青嫌弃地瞟了夜一眼,利落的翻身跳下树,弹了弹身后的灰往外走去。
“止青,你去哪儿啊?”
“找管家给你拿药。”
听罢,夜咧嘴一笑,忙跳下树狗腿地追上去。
这日,云锦乘着马车悠悠地往建安侯府去。建安侯府坐落在内城西南方,大致行了一柱香的时间,马车缓缓停在了三间兽头大门前,正门一匾上书着“建安侯府”四个大字,门前两只威武的石狮子目光炯炯有神。
莺歌扶着云锦下了马车,换乘软轿从侧门进了建安侯府。软轿行至垂花门前,便有两个丫鬟迎上来,掀起轿帘扶云锦下轿。进了垂花门,穿过穿堂转过插屏,眼前便是侯夫人的正房了。
一见云锦来了,侯夫人便忙笑迎出来:“筠儿听说你要来,早就心心念念着了。听说你前几日染了风寒,可是在宫里受了凉?现在可好些?”
云锦行过礼,莞尔道:“劳夫人费心了,不过是受了凉有些头疼,家父不大放心,便不让我出门,其实不大碍事。”
“那就好!”侯夫人拉着云锦坐下,叹气道:“筠儿从小就和你亲,这些日子,筠儿整日闷闷不乐的,你来了就麻烦你好好劝劝她。”
“那日在宫中便见婉筠神情不太对劲,她可是有心事?”
“哎!这孩子,她是想不明白啊!”侯夫人皱眉叹道,“筠儿应该在房里呢,你们小姑娘说说贴心话,我就不扰你们了。”
云锦退出正房,跟着丫鬟往婉筠房里去,心中的疑惑却更甚。
身后的莺歌也发现了不对劲,拉了拉云锦的衣袖,耳语道:“姑娘,这好像不是去往苏二姑娘房里的路。”
云锦示意莺歌稍安勿躁,她多少也能猜到这其中的缘由。
穿过抄手游廊,绕过一个小花园,最后到了一个独立的院子前。院子里,婉筠倚着游廊出神,手中摆弄着一株洁白清新的茉莉花瓣。听见丫鬟的唤声,婉筠回过神,眼里露出一丝欣喜,上前拉住云锦道:“云锦你来了!”
一股凉意传过云锦的手心,云锦不禁一颤,忙捏住婉筠的手指:“你的手怎凉成这样!你在外面坐了多久了?”
婉筠讪讪一笑,身后的丫鬟冬儿忍不住插嘴道:“姑娘一大早起来就坐在外面发呆,奴婢劝都劝不住!”
云锦眉头皱的更深,拉着婉筠往屋里走:“先进屋再说。”
进了屋,云锦才发现这是一座两层高的绣楼,南面的纱窗下,放着一个绣花用的绷子,上午阳光斜斜照过木窗,照到棚子架着的绸缎上,在没有绣花的雪白缎子上印着雕花的窗。绣绷子的对面放着婉筠时常弹奏的古琴,而此时,古琴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尘。
丫鬟们端上热茶和点心便知趣的退下,婉筠抱着茶盏,手指渐渐恢复了温度。
迎上云锦担忧的目光,婉筠浅浅一笑:“娘为我说了门亲事,是……是淮阳宁家三少爷。”
云锦端着茶盏的手不禁一抖,茶水溅出来滴在手背上,云锦浑然未觉:“这……这么快?”虽然云锦有所预料,但从婉筠口中亲耳听见,她还是忍不住心头一紧,仿佛前世婉筠流泪伤怀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
“我本就比你大一岁,明年就该及笄了。”婉筠抿了一口茶,继续道:“娘和宁夫人闺中便熟识,我们两家也有来往,娘说……怕我日后嫁了人在夫家受欺负,不如找个知根知底的,过得舒心些。而且宁家家大业大,管家的事如何也轮不到孙辈三少奶奶身上来。”
“那亲事定了吗?”云锦试探道,若是已经定了亲,那就真的没办法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