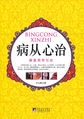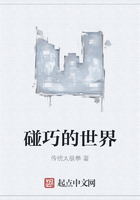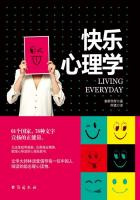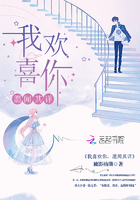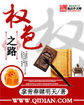肝脏在血红蛋白代谢中起重要作用,能把血液带来的间接胆红素改造成直接胆红素,由胆汁排入肠内。由肠道吸收的胆素原,大部分由肝脏重新排入肠内。当患肝病时,肝脏改造、排泄胆红素的能力下降,血中胆红素的浓度增加,便形成黄疸。
4.维生素代谢
肝脏与维生素代谢关系密切,不但能储存多种维生素,而且也直接参与维生素的代谢过程。
肝脏所分泌的胆盐,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胆道阻塞时,会引起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障碍。
肝脏可将胡萝卜素转变为维生素A并加以储存。可将维生素K转变为凝血酶原。
B族维生素在肝脏内可形成各种辅酶,参与各种物质代谢。例如维生素B1构成脱羧酶的辅酶,参与糖代谢。维生素C可以促进肝糖原的形成。
5.激素代谢
许多激素在肝脏经过处理后失去活性。例如类固醇激素和抗利尿激素等,在肝脏同葡萄糖醛酸或碳酸盐结合而灭活,再随胆汁和尿液排出体外。有些肝脏病人,因灭活障碍而使激素在体内蓄积,可引起性征的改变(如男性乳房发育)。雌激素有扩张小动脉的作用,肝病患者出现肝掌和蜘蛛痣,是雌激素刺激的结果。如果醛固酮和抗利尿激素出现灭活障碍,可引起水、钠在体内潴留,甚至引起水肿。
三、解毒作用
肝脏是人体主要的解毒器官。外来的或是体内代谢产生的有毒物质,都要经过肝脏处理,使毒物成为比较无毒的或溶解度较大的物质,再随胆汁或尿液排出体外。但也有例外,有的经肝脏处理后毒性增加。
肝脏解毒原理有下列几种:
1.化学作用:由氧化、还原、分解及结合作用,其中结合作用是肝脏解毒的最重要方式。毒物与葡萄糖醛酸或硫酸盐等结合后变成无害物质。
2.分泌作用:一些重金属如汞,以及来自肠道的细菌,可经胆汁分泌排除。
3.蓄积作用:某些生物碱如的士宁及吗啡,可蓄积于肝脏,然后逐渐小量释出,减轻中毒程度。
4.吞噬作用:细菌、染料及其他颗粒性物质,可被肝脏的网状内皮细胞吞噬。
四、造血作用
胚胎时期肝脏能制造红细胞,至后期则因肝内有铁、铜及抗恶性贫血因子,亦间接参与造血。
此外,肝脏本身储藏大量血液,在紧急出血时能输送出相当数量,以维持循环血量之平衡。
五、凝血作用
肝脏在凝血原理中起重要作用,肝脏损害严重或有阻塞性黄疸的患者,常有明显的出血倾向。
当血液流出血管后,在凝血酶和钙离子的作用下,凝血酶原转变成凝血酶。然后,纤维蛋白原在凝血酶的作用下变成纤维蛋白,随即形成血凝块。其中凝血酶原和纤维蛋白原均由肝脏合成。如果肝脏缺乏脂溶性维生素K时,便不能形成凝血酶原,而肠道中无胆盐存在时,维生素K就不能吸收入肝脏。即使有维生素K而肝脏受到严重损害时也不能合成凝血酶原,即使注射维生素K也不能提高血浆的凝血酶原值。相反,肝外胆道阻塞者,注射维生素K后,血浆的凝血酶原值将有显著提高。这对于鉴别肝内或肝外阻塞性黄疸有参考价值。
(滕光英)
中医学对肝脏及肝病的认识
一、中医对“肝”的认识
“肝”是五脏之一,《内经》谓“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把肝比作捍卫国土的将军,这说明古人对肝的免疫功能早有察觉。又说:“主怒”、“主藏魂”这里既包含有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又包含了植物神经系统的部分功用,另外《内经》中“其荣爪也”。“其合筋也”、“开窍于目”等论述,均说明了肝和营养代谢的关系,这与现代医学的认识是大同小异的。《内经》还说:“肝属木”、“性条达”、“主疏泄”,这既包含了肝具有类似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又说明肝对全身血管畅通、血流,淋巴等其它体液的分布都有一定的影响。《内经》认为“肝体阴而用阳”。它既是一个具体的器质性的脏器,又是一个功能超过自身局部形态,对全身各系统均有广泛影响的功能系统。由于足厥阴肝经起于大敦,过阴股,入毛中,沿阴器抵小腹,挟脐上行,络肝胆,上贯膈,循喉咙之后,过目系,上出额,与督脉汇于颠顶,凡肝经所过之地,在发病条件下,均会反应出肝的病变。《内经》中还有“风气通于肝”的论述。后人通过临床实践的总结,又形成了“肝风内动”、“风火相煽”、“血虚生风”等概念,从而使肝脏病理生理过程更加广泛,它不仅包含了代谢、免疫、植物神经系统的作用,同时还包含着一部分心血管系统的病理生理功能。
二、中医对肝病的认识
中医认为“肝以条达为顺”,如果一旦因外感或内伤等因素引起“肝气郁结”,则肝病由此产生,因此前人有“郁为肝病之本”说,“肝气郁结”则肝气横逆犯胃,临床上叫做“肝胃不和”或“肝木克土”,此为临床上最常见的症候。肝气郁结的临床表现主要有口苦、咽干,肝区疼痛、急躁易怒、脉弦等。一旦形成肝气横逆犯胃,即肝木克土后则在上述肝气郁结临床表现的基础上出现颜面萎黄、食欲不振、体乏无力,脘腹胀满等。肝为风木之脏,当肝病发作时通常与外风相互因果,临床上出现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欲呕、默默不欲饮食,此为中医少阳证群,亦称半表半里证,乃足少阳胆经循行于两胁之故。肝为木脏,木能生火,肝气郁结既久,则必然化火,形成肝火上炎,证见头眩目赤,舌黄,便结等证,肝病日久不愈,肝木克土日深,脾土虚衰,由气虚转为阳虚,则脾阳虚损导致肾阳虚损,形成脾肾阳虚,此时患者证见阳虚水泛,下肢及腹部肿胀,即现代医学所谓之肝性水肿和肝性腹水、肝气郁结还可由气滞发展到血瘀,中医称为气滞血瘀,此时患者之肝脾肿大,两胁疼痛显著。以右胁疼痛更趋明显。还有一部分患者,由于肝火过旺,引致肾水亏竭,临床出现肝肾阴虚的症候,此时患者可伴有骨蒸潮热、五心烦热,口干不欲饮,舌红少苔,脉沉细数等症候。也有一部分患者出现巩膜及全身黄染,这是因为肝木克土日重,脾阳亏损,中焦湿滞,与此同时肝郁生热,湿热蕴结于里则发为黄疸。当然在生成黄疸的二要素“热”与“湿”之间还存在着孰多孰少的问题。如果热重于湿则为阳黄,证见病来甚速,黄色鲜明,大便秘结,伴舌苔黄厚腻,脉滑数及发热等症状;湿重于热则为阴黄,症见病情缓慢,黄色晦暗,伴腹胀、便溏、舌胖淡,苔薄白、脉弦紧症状。肝病日久,正气耗竭,病人中之一小部分可由谵语、昏迷而导致死亡,此即西医所谓之肝昏迷或肝性脑病者。中医则认为正气亏耗,则外邪乘虚而入,风火相煽、热入心包可致斯症;肝肾阴虚,虚火过旺,火扰神明亦致斯症;气虚不能统血,火旺迫血妄行,热入血分亦致斯症。
三、对黄疸的认识
黄疸病名,最初称为“瘅”。如《内经》指出:“湿热相交,民当病瘅。”关于“瘅”字,其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伤寒明理论》解释为“瘅者,黄也”。瘅与疸同音,古代通用。中医对黄疸病症的论述,最早见于《内经》。《素问·平人气象论》说:“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灵枢·论疾诊尺》篇说:“身痛面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说明了黄疸的主要临床表现特点。对黄疸的病因病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说:“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腑肿。”最先提出了炎暑湿热之邪作为黄疸的病因。《灵枢·经脉》篇说:“脾所生病者……溏瘕泄,水闭,黄疸。”该篇又说:“肾所生病者……黄疸肠癖。”说明黄疸虽主要因湿热相搏所致,但与脾肾也相关联。
东汉张仲景对伤寒发黄及内伤发黄进行了研究,认为瘀热在里、寒湿在里不解和两阳相熏灼(火毒)是外感发黄的基本病机,而饮食失节致胃热脾湿,劳役纵欲致虚劳伤肾,是内伤发黄的基本病机。如《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说:“阳明病……但头汗出,身无汗,齐颈而还,小便不利者,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同篇中还说:“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他特别重视“湿”在黄疸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如《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中说:“诸病黄家,从湿得之。”以上认识,是对《内经》关于黄疸病因病机的发展。他还观察到,热病发黄,往往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有人在发热几天以后,才出现黄疸。故《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说:“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他还提到黄疸的消退时间和预后,虽未明示“急黄”之名,但指出确有一些黄疸属于难治。如《伤寒论》中说:“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为难治。”在《金匮要略》中,设有专篇论述黄疸,根据病因之不同将其分为谷疸、酒疸、女劳疸和黑疸四种。《伤寒论》中主要谈了伤寒发黄。张仲景提出了清热除湿、泄热通腑、清泄实热、解表清里、发汗涌吐、和解枢机、润燥消瘀、温补建中等治法,以及茵陈蒿汤、小柴胡汤、栀子大黄汤、栀子柏皮汤、大黄硝石汤、茵陈五苓散、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硝石矾石散、小建中汤等方剂。至此,黄疸病的理法方药渐臻完整,对当前临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黄疸诸候》中,把黄疸分为二十八候,并指出有“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的急黄,乃由“脾胃有热,谷气熏蒸……热毒所加”而致。巢氏还指出:“有得病即身体面目发黄者,有初不知是黄,死后乃身面黄者。”说明当时对重症黄疸的临床表现,已经观察得非常仔细。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认为,“时行热病,多必内瘀著黄”,在此指出了时行热病中的黄疸具有一定传染性。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黄疸的诊断方法:“令溺白纸,纸即如蘖黄者。”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了黄疸的针灸治疗配穴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黄疸的治疗手段。
宋代以后,对黄疸分类及其证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繁返约的过程。《太平圣惠方》记载了“三十六黄”的不同表现及治法;《圣济总录·黄疸门》分为九疸三十六黄;韩祗和《伤寒微旨论》中,除论述了黄疸的阳证外,还特设“阴黄证篇”,专门讨论阴黄的证治,使黄疸的分类更为合理,茵陈四逆诸方更是为后世所习用。金元时期,朱丹溪认为“疸不用分其五,同是湿热”;罗天益《卫生宝鉴》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湿从热化为阳黄,湿从寒化为阴黄,把阳黄和阴黄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至今仍为临床奉为分型准绳。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针对黄疸阳黄的病机尤重脾湿和郁热,提倡用清火利水之法治疗,并增加“胆黄”一名。他说:“阳黄证多以脾湿不流,郁热所致,必须清火邪,利小水,清则溺自清,溺清则黄自退。”黄疸的形成,还会因“胆伤胆气败,而胆液泄”所致。但也不宜执清利一法而治所有黄疸。故张景岳说:“不可以黄为意,专用清利。……但宜调补心、脾、肾之虚,以培气血。”因此,主张对虚证可用四君、理中、六味等方剂施治。清代沈金鳌对有些黄疸的传染性强、危害性大、死亡率高,在《沈氏尊生书·黄疸》中说:“又有天行疫疠,以致发黄者,俗谓之瘟黄,杀人最急。”可见,对巢氏所谓“热毒”所致的急黄,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三因方》论黄疸病因说:“各种黄疸都与水、食有关。”《医学必读》指出黄疸的病位和病机:“黄者中央戊己之色,故黄疸多属太阴脾经,脾不能胜湿,受挟火热则郁而成黄。”《医学心悟》论黄疸分型及特点:“谷疸、酒疸、黄汗为阳黄,女劳疸为阴黄。……黄如橘皮柏皮间火气而光彩此名阳黄;又有寒湿之黄,黄为熏蒸色暗不明,手足厥冷,脉沉细,此名阴黄。”这种分类法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现代一般认为,黄疸型病毒性肝炎属中医学“黄疸”的范畴,但黄疸不一定就是病毒性肝炎,在胆石症、胆囊炎、钩端螺旋体病等疾病中,都可出现黄疸。而无黄疸型病毒性肝炎,见于其他许多病症。因此,临床需辨病和辨证相结合。
四、对胁痛的认识
胁痛一证,在《内经》中就有记载。首先,胁痛与肝病有密切关系。《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忘。”指出了肝病的主要症状和病变部位。《灵枢·五邪》篇说:“邪在肝,则两胁中痛。”《素问·刺热论》也有“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胁满痛”等记载。说明当时对肝脏与胁痛之间的关系,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胁痛也与胆经病变有关,如《灵枢·经脉》篇说:“胆足少阳之脉……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了胸胁苦满、胁下痞硬、胁下硬满这三个症状,作为太阳转入少阳病的一个辨证依据。满、痞、硬虽然和“痛”有所不同,但同是胁肋部位的病变,是辨别肝脏和胆腑疾病的一个重要依据。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详细描述了胁痛的脉象、伴随症状及症候。他说:“左手关上脉阴实者,足厥阴经也,病苦心下坚满,常两胁痛,息忿忿如怒状,名曰肝实热也。”金元时期,朱丹溪从火、气、血、痰四个方面,来把握胁痛的病机。如《丹溪心法·胁痛》说:“胁痛,肝火盛,木气实,有死血,有痰流注。”
明代医家对胁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医学入门》中说:“胁痛本是肝家病,宜分左右审实虚。”指出了肝病的辨证要点在于分清虚实。《证治汇补》说:“湿热郁火,风令外侵,皆令胁痛。……凡胁痛日久不愈者,乃痰郁结成积块,肝积曰肥气,病在左。……发作有时,皆肝木有余。”说明这几种常见的病邪都可导致胁痛,且肝病日久,可形成积块。有的胁痛,也可出现传染性。如《脉因症治》说:“有疠气胁痛之症,病起仓卒,暴发寒热,胁肋刺痛,沿门相似,或在一边,或在两边,痛之不已,所谓疠气流行之疫症。”在此提出了“疠气胁痛”的病名。该书还详细论述了内伤胁痛的成因:“内伤胁痛之因,或痰饮、悬饮凝结两胁,或死血停滞胁肋,或恼怒郁结,肝火攻冲,或肾水不足……皆成胁肋之痛矣。”《景岳全书》说:“胁痛有内伤外感之辨……但内伤胁痛者十居八九,外感胁痛则间有之耳。……胁痛之病,本属肝胆二经,以二经之脉,皆循胁肋故也。……然而心肾脾胃肺与膀胱,亦皆有胁痛之病。”指出了胁痛的辨证要点在于区分内伤与外感,并说明胁痛的病位主要在肝胆,而与其他脏腑功能失调都有关系。他对将胁痛分为左右气血的见解,表示了极大不满,“古无是说,此实后世之谬误,不足凭也”。对于胁痛的治疗,《景岳全书》进一步指出:“病在本经者,直取本经;传自他经者,必拔其所病之本,辨得其真,自无不愈矣。”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对久病入络之胁痛,善用辛香通络、甘缓补虚、辛泄祛瘀等法,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林佩琴《类证治裁》把胁痛分为肝郁、肝瘀、痰饮、食积、肝虚诸类,对胁痛的分类与施治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代一般认为,胁痛病症与肝胆疾病有关,所以与肝胆病症有关的疾病多伴有胁痛的症状。乙型肝炎,特别是慢性患者,常见右胁不适或疼痛,与古代医家的认识是一致的。
(郭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