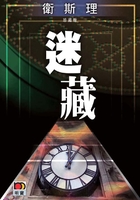树欲静而风不止。土改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土地和财产的再分配,而且还要启发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于是诉苦、批斗大会成了土改运动中一项核心的政治行动。
“把万恶不赦的地主押上来!”随着一声高喊,村里的几个地主及地主婆被押上了台。黄彩玉由于瘦小,站在台上显得格外可怜。第一次被批斗时,低着头的她真想在地上找一条缝钻下去。挨过饿,吃过苦,当童养媳时挨过打,但从没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过如此羞辱。
通常批斗会前要先诉苦。
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中,对“诉苦”一词的解释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
诉苦的贫下中农,往往是在地主家干过活的。而这需要做思想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主人家并不坏啊。曾在王松甫家当过保姆的洪黄女回忆道:“当时,乡村领导要我上台去揭发批斗地主婆,我是坚持不肯。他们说我在王家做了三年保姆一定吃了不少苦,我这人实事求是,没吃苦就是没吃苦。人家夫妻俩待我客客气气,给吃给穿,我怎么能平白无故去冤枉人。”
木瓜村的斗地主虽不像有的地方那样残酷,但阵势也够吓人的。公社、大队的干部都到场,方圆数里的村民都丢下农活赶来。偌大的庙堂里黑压压的全是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一阵接着一阵。
每一场批斗会,戏总是事先排好的。可临场也有唱得离谱的。
有一次,被做了思想工作的一个长工上台揭发,说地主王松甫家是如何如何富裕,以前这里看戏的祠堂、道路都是王家太公出钱修的。还说要饭的来到家门口,地主婆黄彩玉总不会让人家空手而归。因为有吃有穿,我们做长工的也就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干活,受他们剥削。现在他们被打倒了,自己连稀饭都没得喝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台下一阵哗然。主持者听得不是味,赶紧上来救场。可那长工蹲下来,双手捂着脸,竟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自己已经好长时间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肚子饿得咕咕叫……
后来,上去好几个工作人员才把他拉下台。
当然,立场鲜明、义愤填膺,对地主阶级造成了威慑效果的批斗者也大有人在。
每次开大会,有两个人斗起黄彩玉来总是显得特别的气势汹汹,喊起口号来也特别响亮有劲。他们先是诉说自己从前是怎么穷怎么苦,怎么受地主王松甫欺压,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对彩玉拳打脚踢起来……
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如此苦大仇深是事出有因的。
从前,国民党征兵搞摊派,每个乡村都必须落实任务指标。那回需要出两个人,王松甫很感头痛,这性命攸关的差事谁愿去呢?在家里,他也思量着,这天随口派起名字来。当说到某人,彩玉应了一句:“人家有老婆小孩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不是作孽吗?!”
是的,最好别拆散有家室的人。彩玉的话使王松甫想起了乡里的两个光棍汉来,而且他们又是最懒最穷的。
对,送他们去是最人性化,也是最佳的选择了。首先他们是光棍汉,本身无牵无挂;其次,他们很穷,如果当兵去,温饱问题就可解决了;而且,懒汉到军营还可好好得到锻炼,抽一下懒筋。
没想到解放了,两个光棍汉又回乡了。他们是穷人,是被迫让地主送去当兵的。于是,他们诉起苦来就显得特别苦大仇深,并且趁机动手打人以泄私愤。
两个光棍汉不仅在批斗会时出恶气,平时遇到彩玉不是骂骂咧咧吐口水,就是趁其不备暗中袭击。地主婆是要受惩罚的,如承担扫马路、拔草等义务劳动。有时,彩玉正蹲在路边拔草,光棍汉路过时会冷不防地在背后抬腿一脚。彩玉便扑倒在地。“哈哈,活该!”随着嘲笑声,她不用回头看,也知道是哪个光棍汉。
不管严寒酷暑,不管刮风下雨,多少年了,黄彩玉默默地忍辱负重。
大儿子可行的女儿王美君回忆说:“小时候,见奶奶在扫村里的路,心里奇怪,人家都扫自己家门前的,她怎么每天都要扫到大路上去?后来才知道奶奶是受罚才需要这样做的。但奶奶从不对我们说,也没提起过她遭人欺侮。这些事,我们都是后来从大人或者邻居口中得知的。”
也许是吃过童养媳的苦,又经历了丧夫之痛,黄彩玉面对人生磨难的抗压能力,明显比其他人强。
据说当地有三个地主婆,一个年老八十了,斗也斗不动,草也拔不了,拿她没办法。另一个与黄彩玉年龄相仿的,她承受不住无休无止的批斗与繁重屈辱的监督劳动,就改嫁到别村去了。于是,她就摆脱了地主婆的罪名。
为此,也有人劝彩玉,年纪轻轻的,日子还长着,若有合适的人也该考虑一下。但彩玉摇摇头:“我嫁出去,那孩子们怎么办?”她是绝不可能让孩子们受委屈的。
令人宽慰的是,三个儿子逐渐长大懂事,且在很小时就已尽己所能地帮助母亲了。那时,开批斗会还要地主人家自己挨家挨户去通知。而彩玉在田头忙得实在没工夫,童年时期的乐宾和阿光,常常替娘敲着铜锣去通知:“社员同志们,晚上庙里开大会!”这样,从上巷弄到下巷弄,边敲边喊,要二十多分钟。
在生活难以保障的岁月里,人们对那些政治上的迫害都已变得麻木。物质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让孩子们有饭吃是黄彩玉认准的硬道理。
儿子王泽光回忆起当年母亲的艰辛往事,历历在目。
象山出产番薯。作为一年四季的长粮,贮藏是很重要的事。而那活儿是需要赶时间的,每到九十月份,满地番薯收获来后,当地通常的做法是把它们刨成丝,风干。最好趁西北风起时一气呵成,这样如果老天爷突然变脸,提早下雪,也不担心发霉了。
但也常常有令人措手不及的事发生。好不容易在一张张竹垫上把番薯丝铺排好,突然一阵猛烈的西北风刮来。而番薯丝总是晾在风口的,于是整个垫子被掀翻,番薯丝被吹得一塌糊涂。
风口无遮无拦。寒冷中,黄彩玉面对意想不到的场景,慌忙捡拾,唯恐大风把那些食粮吹散。那时,跟在她屁股后的小儿子才四五岁,他见此赶紧帮母亲一起捡拾。
王泽光感慨:“娘真的很辛苦,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中,起五更落半夜,睡觉简直是马打盹。”
黄彩玉算得上是全村手脚最快的人。每年夏天的“双抢”,一个妇人默默地独自支撑下来,其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可见一斑。夏收夏种时,天没亮就起来出门割稻去了。中午,烈日当空,田头温度高达四十多度,身体感觉简直像被火在烤似的。古人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确是真实的写照。
打稻,晒谷,翻草,这些重体力活必须马不停蹄地做。若天公不作美,遇上雷阵雨,那晒在篾垫上的谷子可要遭殃了。所以,一旦发现乌云滚滚而来,得赶紧丢下手头的农活,先把谷子抢到仓库里去。有时,谷子藏好了,再去收晒着的草垛已经来不及,豆大的雨点已经砸下来,只得急匆匆把它们叠拢,大致遮盖一下。等紧急处理好这些,彩玉才暂到仓库避雨,身上的衣衫早已被淋湿。也只有这时候,她才得以喘息片刻。
黄彩玉付出着如此劳力,却不能满足自己的温饱。三个儿子随着个头的长高,饭量增大了。可家里的口粮不够。于是,她常常自己一日两餐,保证儿子们一日三餐。只有冬天下大雪时,才会让孩子们偶尔一日两餐。但这样会使她感到不踏实。因此,为把持好一日三餐,彩玉通常把早晚餐做得稀薄些,中饭则烧得厚实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
二儿子乐宾回忆道:“我上了一年学,9岁就帮人家放牛去了。娘是不会要我干这活的,我自己想去。因为那时饭吃不饱,我们一日三餐,而娘只吃两餐,苦活重活却要做,这使我看着心里不好受。于是,就提出给人放牛去。娘是要面子的人,常常对我们说要争气,不然家里要被人看倒的。所以,我替别人看牛去,她心里很难过。可娘犹豫之后,还是同意了。在她想来,至少可以让我吃饱饭了。这样,我不仅减轻了娘的负担,一年下来,还可给家里带来两三斗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