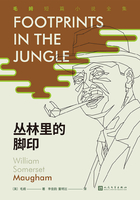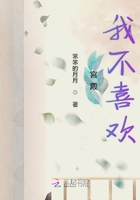我拨打子和的电话,也停机了!。她也失踪了?心里骤紧,巨大的悲伤铺天盖地狂袭而来,真想大哭一场,可我只能在黑暗中抽搐嘴角,干呕般难受。
如果不是腿脚发软背脊冒虚汗,真想不起自己还需要吃东西。
我在街角的快餐店吃了个梅菜扣肉饭,心里想扣肉始终不是红烧肉。吃过饭后,我在水果店买了些橙子,去看看李军花怎么样了。
给我开门时,李军花正在家里搞卫生。她让我随意,继续忙着拖地,家里已经焕然一新。
我陪着干看,听她在旁边念叨:"房子一天没有人打理,就脏的不成样了。"
我找话说:"我几天都不打理一次。"
她笑我:"猪窝能跟人窝一样吗?"
她已经恢复了过去的平常,因为休息不错的缘故,脸色光滑了许多。在她那坐了会,我就离开了,她也没挽留说回头电话联系。
我再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在街上晃荡。有个农村妇女神秘地问我,要毛片不。我反问她,你要找人演毛片不。她用方言说了句"毛病",然后继续去向其他的路人兜售。我猛的大喊一声城管来了,她吓得大跑。我在后面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心里像被人刚刚洗劫过空荡荡的。
气温骤降,异常阴冷。变天了!
连续两天,除了吃喝拉撒,我基本上都躺在床上,哪里都不想去。我想也许被窝和床给我莫名的温暖和隐约的安全感。期间我给李军花住的地方打了个电话但没人接,我想可能是出门了。然后,继续睡觉。这一睡又是一天过去,我再次又给李军花打了个电话,还是没人接,我担心出什么事。这样一想,赶快从床上爬起来。
李军花家的门铃任我怎么按,里面就是没有反应,我又打家里的座机电话,里面的铃声作响,就是没有人接。真的出事了?!我的心剧烈狂跳,拍门大喊,手掌瞬间红肿变得乌紫。
叫声惊动了对门的人,出来一个老太太,她问我:"你找对面的姑娘?"
我说:"对,阿姨您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老太太说:"她昨天搬走了"
"啊,搬走了!"我大吃一惊,"您知道她搬哪里了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顿时,我如坠冰窟。李军花也失踪了。
我回到自己住处。原本凌乱的房间里,开门间带起的风声扬起细细的灰尘,如我很久没有喝"鸡汤"的心。
躺在床上,我努力想让自己睡去,好忘记这所有的悲伤。可神经却如雪地里老笋把坚韧,让我继续浸泡在这悲伤中,血管里流淌的也好像是咸咸的泪水,流过之处,荒芜一片。眼前逐渐朦胧,我终于可以睡去。我太累了。
睁开眼,已经是早上10点。我起身冲了把冷水脸,在大堆乱七八糟就在通讯簿上的号码中找到子和公司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