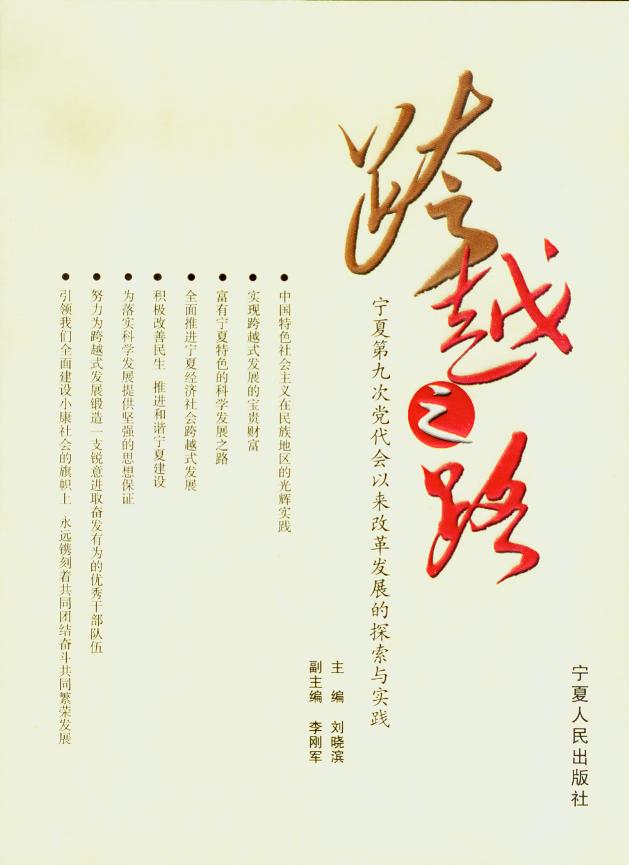笔舌之辩,义理之争。辩到最后,争到最后,最有权力的人,举起了刀。
本朝初皇帝在泗州屠杀僧人,已经表明了态度,俗家弟子的日子注定不好过,一个个当缩头乌龟,首尾皆收。初皇帝身边的贴身太监谁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手段鼓动初皇帝灭佛。道教跟儒家士族的联手,更是沉重打击了佛家的地位。与佛教交好的泛阳卢氏,泰元郭氏,河东柳氏,祝州宁氏,北方门阀大族更是牵连无数。
道教身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为了道门的复兴,自然做了诸多努力。
摩崖年间,初皇帝特命已入虚寂之门的陈升经于青牛肆栖梧观设醮,见红光射来,遁入殿西一株梅树下,令小道士掘之得青砖一块,上刻春秋古篆,陈升经面色铁青的将带着“****”二字的砖块一掌拍碎。陈升经对天道发誓,自己当初埋进去的时候绝不是眼前看到的这块砖,“初皇垂世,圣祖垂祥”这八个字,要比唱一万首颂歌来的效果好,起码能在自己归于湛然清净之海后,能有个银青光禄大夫加身,现在全他妈完了,整这么一出大场面,就等着拍皇帝的马屁,然后出来一句骂人的话,道门式微的征象吗,陈升经从来不信这种狗屁征兆,但一时又想不起是哪个阴毒之人起了坏心思,暗中搞破坏。眼下只好推到佛教那帮人身上。眼下自然做戏做全套,幸好来的皇帝的耳目是自己亲近的人,还有很多斡旋的余地。
场中自然有皇上身边来的小太监,在等待神迹的到来,所以睁大了双眼,生怕多眨一下就少看到一点,回到知闲校不能把所有不似人间景象的奇幻给皇上诉说完整。
小太监名叫陈淡闻,本是陈升经同族后生,不过这人天生喜欢男人,但内心的压制,往往大不过欲望。在一次醉酒后睡了一个不该睡的朋友后,被朋友的女人一刀剁下去,再也没有了那一嘟噜。后来活了下来,但再没脸进入以前的交际圈子。索性入宫,跟了一个老太监,老太监也姓陈,也不用换姓,不过不再用陈淡闻这个名字为家族蒙羞,只是叫陈骨碌,老太监就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整日骨碌骨碌的叫着,陈骨碌也挺喜欢这个带着土腥子气的名字,因为这能让他想起了很多遥远的朋友和与岁月一起沉默下来的故事。陈骨碌很少有出宫的机会,这次还是自己单独出宫做事。
“骨碌啊,叔不知道会出土这么个玩意,是叔的不对,这次你一定要帮叔一把。”
“叔啊,别说这样的话,我陈骨碌虽然现在叫陈骨碌,但我一直没忘我本名是陈淡闻。”
“那就好那就好。”
“叔啊,你把砖再埋起来一会,不然没有泥土味,反正我明天下午落城门之前赶回京城就行,晚上我再连夜赶路也不迟。”
“对对对。”陈升经已经被吓傻了,平时的精明道风浩荡全化成了漫天的渣土,赶紧挖坑把新砖填埋上。
山峦叠嶂,秋夜正凉。陈骨碌面色苍白的接过陈升经重刻的青砖,“初皇垂世,圣祖垂祥”八个字沿着青砖细细的脉络铺展开来。陈骨碌用明黄色的绸子细致的包裹祥瑞砖。陈骨碌已经知道怎么回复初皇了,为了那些朋友,为了那些逝去的时光,自己也要做些什么。道门,那就算了。
这几日在卡诗山游荡的僧侣无数,佛门衰败,谁也不敢发慈悲收留这些无家可归的和尚,生怕被游缉司的恶魔半夜踹门掳走扔进牢狱念经。
琅琊王氏出书法大家,钻研文字写法技巧的往往文章也漂亮,这些人极擅清谈,是那种一出口,话就嘟嘟往外冒,话密且杂,停下很难,基本上可以不用旁人插嘴就支撑整个谈话局面,还不会让人特别反感。这些人的说话时候的中心思想就是,不愿听就他妈滚。
今日逐堂私塾的老夫子讲的是一篇《长竿入城》的寓言小故事,旨在启发学生要拥有自己的思想,不要盲听盲信。赵渐暗一手托腮,甚是认真的望着窗外,透过伞盖大的芭蕉叶,一个用草绳随意束起的黑发小姑娘在篱笆外面已经转了好多圈了。
老夫子手捧古籍摇头晃脑,鲁有执长竿而入城门者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卡诗山逐堂私塾的老夫子属琅琊王氏一脉,自然信奉说话的中心思想,对学生从没好脸。老夫子手捧古卷为学生做最基本的启蒙,老夫子的学问并不高,只是认得许多字,对于书内的经义不甚了解,更没有自己的认识。没等老头诠释文章,赵渐暗就站了起来。
“老师不对啊,这老头太粗暴,既然横着竖着都进不去,他应该直直的捅进去,就是这个样子的。”赵渐暗不知道从哪寻来一根比自己长很多的竹竿端平往学堂内冲,老夫子看着那个竹竿头快递到脖子下面,这是要捅死谁啊,旋即被气的胡子都飘起来了。
赵渐暗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被赶出学堂了,瞥了一眼陈清昼,陈清昼把脸埋在怀里的兔子身上。赵渐暗跟兔子对视一眼,背着手无所事事的满山溜达。遇到好些和尚,也不上前搭话。行到叶记酒家看到那个清丽脱俗的女子,揉揉脸,摆出自认为很有杀伤力的笑容。
赵渐暗舔着脸,不知羞耻:“道旁榆叶似青钱,摘来沽酒,不知姑娘肯否?”
“不肯不肯,快滚快滚。”对这种口舌刁滑之辈,叶赛宁想起了爹爹教过自己怎么对付这类人,那就是不给好脸。但赵渐暗怎么会轻易退缩,拿出来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给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还要无耻的嘴脸,往跟前凑,帮她打酒。
叶赛宁的哥哥实在看不过去赵渐暗如此大胆调戏自己的妹妹:“东塘最大的劁猪匠人有个闺女,顶天的漂亮,我带你去祸害她。”
“当垆卖酒,白瞎了一双好手。”
“呸,还要不要脸皮。”
“宁宁,手是用来牵手的,你用来持青竹酒提那种烂糟物,啧啧,下辈子我立志要成为一个青竹酒提子。”对于这种人,叶赛宁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应了。
“对了,今夜有我的个人演奏会,要来啊,在卡诗山最高的悬崖边上。来晚了就抢不到好位置了。”
“神经病。”叶赛宁把赵渐暗的话抛之脑后,给过来打酒的酒鬼舀上半酒提。
风疾掠竹,先师闻此音,曾历数人间之音,“论声之韵者,曰溪声、涧声、竹声、松声、山禽声、幽壑声、芭蕉雨声、落花声,皆天地之清籁,诗坛之鼓吹也。然销魂之听,当以卖花声为第一。”有好事者暗自揣测,先师最初喜欢过的第一个姑娘,就是个走街串巷吆喝卖花的。红心词客的门人出言销魂有两听,乍然为官,万千鼻孔正对一人,倏然耳闻退堂鼓声奏起,此乃一听。得娇娘,入帷帐,轻挑金钩,铮然而响,怦然心动,此乃销魂第二听。赵渐暗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对,不是自己心中所幻想的销魂,销魂是有声音的,这很对,但销魂的声音应该是清昼开心时候的笑声。
曾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梦里梦到过这种乐器,奇怪的字符,NothingElseMatters,就是这个名字,虽然自己从没见过这样的文字,但赵渐暗会发出这些音节。赵渐暗无师自通的会了好几首曲子,其中就包括那首NothingElseMatters,赵渐暗选定天空中漂浮八颗顿首石,以那八个点延伸出宽广的音域,扯着神仙语绕匝几圈固定,抱着小吉他,清弹一根琴弦,天空中的神仙语回应出美妙的音,清昼是被赵渐暗硬拉着过来的。本来还要去打猎,不过看到赵渐暗从一个崖壁的缝隙中拿出来的小吉他,立马挪不开眼睛了。
“这是弦枕桥,用的浑沌的骨头,这个是我在西荒里捡的,据说这个凶兽两耳不闻两目不见,是个直肠子,不懂的打旋,有啥说啥,不整那些弯弯绕,是直肠子的都是热心肠,所以用了它的遗骨我想它也不会愤怒的来找我,要找也会先找为他凿出七窍的俩损友,南海之帝,北海之帝合伙干死了他这个中央之帝。音孔饰圈镶的的海介虫的贝壳,还有指板上与琴弦垂直的白铜丝,在这些地方按弦,得出的调调也会不同,我叫这个乐器为,吉他。”
“这倒是头回听说,教坊的乐工吹的悲篥,是南山截得青竹,婺州有麻奴者善吹且以技自傲。上截为父下截为母的两截叮,表面用獐子皮或鱼皮紧裹,有个池塘,容纳声音,等池塘声音漫出来,会更好听。火不思是长柄四弦,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大朝会和呼兰行围时要演奏。你手里制作的这把很像火不思,只不过你这个有六根弦,而且样式很新鲜。”
“池塘,你说的是共鸣箱吧。”
“什么是共鸣?”
“就是声音的叠加,就像你说的池塘,声音在池塘里堆积,把池塘堆满再流出来,会很悦耳清脆。”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到你在书院看书,旁边有颗挂满苹果的苹果树,你要爬上树给我摘苹果吃,但突然就到了观夜山的山脚下的河边,我朝你招手,然后拉着你一起跑,跑到另一片没有见过的海。”
“说了这么一大段其实你是想去观夜山的那边的海里划船。”
“讨厌,可能是我想游水了。”
“你可以在我将来撒骨灰的臭水沟里畅快一把。”
“你走,别碰我。”
“就碰你就碰你。”
“你走。”
“我戳,我戳。”
“你过来。”
“你就不怕我戳死你。”
“不怕,你戳我我就抱你,你还舍得戳吗?”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昼渣渣。”
“……”
“你应该说你渣爷在此。”
“渣爷……”
“然后我收,你就进了我神通广大的葫芦里,我摇摇葫芦,你就变成葫芦娃了。你不会吐火也不会吐水,你只会吐泡泡。在夕阳下,泡泡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