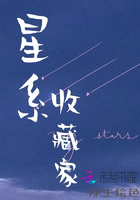“我一直都在这里啊。”他转过头对我笑,阳光照在他青春洋溢的脸上,我至今都能回忆起他脸颊上被镀成金色的浅浅的绒毛,还有那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其中有一颗特别地亮。
我很想和他接吻。他的嘴唇,他的气息,他的眼神,都让我情难自已。可是这是在八木家的长廊上,院子的石柱后面已经挤了两个好奇的脑袋在张望着这边,其中一个还在对我挤眼睛。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新八。
我忍住跟他打招呼的念头,担心会给他带来麻烦。宗次郎却毫不在意地拉着我,走到他们面前,摊开手掌,指着我介绍:“这是史密斯。”
那两人笑嘻嘻地跟我点头。
“永仓新八,很久不见啊,西洋来的小姐。”新八冲我摆手。
“原田左之助,”另外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挠着头,说,“我听麻纱说起你了。”
“你们好。”我学着日本人的样子规规矩矩地鞠躬。
原田左之助脸上全是惊奇的神色,新八用手肘碰了碰他的胸口,得意地说:“怎么样?跟你说了吧,她学了不少我们的东西。”
宗次郎和他们说笑了几句,准备带我离开,突然想到了什么,回过头问:“平助那家伙呢?没和你们在一起吗?”
“没有。他从昨天就一直待在新德寺伊东那里。”原田皱着眉头,还想说点什么,新八轻咳了一声,漫不经心地把手搭到原田的肩膀上,敲了两下,说:“都是北辰一刀流的嘛,走得近也不奇怪。”然后他像是有所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宗次郎静静地站了一会,说:“不用担心,土方先生那边已经说好了的。”
“总之,你要是看到一个脸比女人还白、长得很艳丽的男人,记得千万要躲开。”新八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像在暗示着什么。
等他们走后,宗次郎才告诉我:“他说的是伊东,大概除了近藤先生以外,没几个人会喜欢他吧。”
“你们不是同伴吗?怎么会不和呢?”我问。
“怎么说好呢?这家伙带了一帮人过来,还在我们的队士里面拉人。他是狂热的尊攘派,最好是不要让他看到你。”宗次郎专注地盯着枝繁叶茂的樱花树,说。
“那这里的主人呢?刚刚我看到八木夫人了,她看起来不太高兴我在这里。”
“不用担心,我和土方先生说了,会和你一起搬出去。八木先生也在的。我是局长助勤的职务,可以在外面住。”
“让你的同伴知道我的存在,真的没关系吗?”我还是很担心。
“土方先生说,尽量让更少人知道,不然……。”他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对不起。”
我握住他的手,小心翼翼地问:“我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他转身凝视我,重重地把我抱在怀里,附在我耳边温柔地低语:“不会。”然后他又笑了起来,说:“今年很暖和,樱花应该会提前开。到时我带你去平野神社看樱花祭,人山人海,漫天都是樱花在飘,很热闹的。”
“江户的樱花会比京都的好看吗?山南先生说他想回江户看樱花。”
宗次郎想了一下,说:“我也是很想念江户的樱花,有几年没看到了。以后有机会带你回去看。我记得小野路町那边有一大片的蒲公英地,每到春天,风一吹过,蒲公英和樱花糅合在一起,飞得到处都是。三年前,我和山南先生去教授剑术的时候曾经过那里。”
他闭着眼睛,像是在想象当时的画面,嘴角微微地翘起来,十分地孩子气。我趁着周围没有人,飞快地上前亲了亲他的脸颊,有点偷偷做坏事的紧张。他蓦然睁大了眼睛,捂着迅速泛红的脸颊,东张西望了一会,才低声对我说:“小心被人看到呀。”
我心中充满初恋少女的甜蜜,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冲田先生,快说,我是谁?”
他一下子就领悟了我的意思,羞怯地念了出来:“冲田夫人。”
“再说一遍。”
“冲田夫人。”
“大声一点。”
“冲——田——夫——人!”
我更加欣喜,心情欢畅得就像坐着骏马在春日的原野上驰骋。我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拥抱着他,喃喃自语:“我何其有幸,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了你。”美国姑娘直率豪迈的性情在那时完全迸发出来,我一点一点地褪去庄重矜持的面纱,变得跟一个天真的小女孩无异了。
我的嘴巴总想去亲吻他,我的手总是摸不够他的肌肤,好像没有紧紧地接触他,就无法驱散我心中狂野奔放的原始冲动。
“怎么办好呢?我像喝醉酒了一样。”我扯着他的衣袖,心里怦怦直跳。
也许是我目光过于火热,他的脸仿佛被烫伤了一般红彤彤的。他讷讷地说:“是啊,那要怎么办?”
“跑出去!我们一起从这里跑出去!”我大笑着,拽着他,撒开脚从这个僻静的小院子里飞奔出去。
没有人伸手阻挡,来不及看别人异样的眼光,我和他手拉手一起跋涉过春天的河流,顺流逆流,一路向前,从这个偏见与隔阂并生,杀戮和欲望共存的世界里远远地跑出去。
他一边欢快地带着我跑,一边指着地方对我喊:
“这是前川邸。”
“哎呀,别走那边,新德寺是我们的驻地,会碰上伊东那群人的。”
“不行,不行,那条路通岛原。”
“我们再去敷船屋看歌舞伎表演好不好?这边,这边啊!”
“……。”
那是我美丽的十九岁的春天。“噼啪”,抬起头,有个粉嫩的花蕾从树上掉了下来。对未来的幸福期待渗透了我的身心,无形中所有的花花草草都变得绚烂缤纷起来。我和我的男孩仿佛长出了翅膀,高高地越过黑压压的人群,直直地冲上云霄。在那里,没有别人,我们可以一起自由漫步,结婚生子,周围鄙夷的眼光和惊惧的尖叫都统统消散。
“宗次郎啊,如果我们能永远这样跑下去该多好啊。”我握紧了他的手,暗暗地想。
我们在敷船屋门口停了下来,守门的小厮却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他颤抖着手指向我,惶然地摇头,声音起伏不定:“这不可以,会吓走其他的客人的。”
经历过下关炮战,连长州藩都转而赞同开国通商,在日本这个岛国穿梭的外国人逐渐多了起来,贸易往来频繁。我零零散散地听闻了这些事,虽然不期望日本普通民众可以大方地接受一个外国人出现在他们的公开场合,但是没有想到依旧是排斥到这样的程度。这是他们的天皇所在的城市,对于信仰和血统纯正的坚持,一直是日本人骨子里不可抹灭的骄傲。
宗次郎神色黯然,不理会他人的指指点点,仿佛自己做了错事一样,只是不住地对我说抱歉。
我装作不在意地安慰他:“没事,我也不太喜欢看。那长长的音调听不懂,还让人想睡觉。”
“那我们去看看房子?附近有个挺好的宅子。嗯,我还是有一点闲钱的。不用担心,我们领的是会津藩的俸禄,够的。”
“好,先给我买个笠帽,那种有面纱的。”我想了下,又补充了一句,“因为太阳比较大。”
“嗯,再去趟大丸吴服店,该给你添几件衣服了。”他轻声笑着,好看的脸庞在温煦的阳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辉。
我觉得我不再像漂浮在深海上的木块那样孤独了。寂寞、眼泪、不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想要的那个人就站在我身边。拥抱着他,就像拥抱自己的心灵一样温暖。
衣服要过些天才能取,新到的布料里有一款我很喜欢的颜色,日本人管它叫“千草色”。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戴着市女笠,紧紧地跟在宗次郎身后。他一边按着刀,一边牵着我走一些比较偏僻的小巷。
宗次郎说的那个宅子坐落在一个名叫油小路的地方。他说他们可能不久就要搬到西本愿寺去了,那里离屯所近,以后会方便很多。
开门的是个老人家,头发苍白,拄着拐杖,发髻梳得一丝不苟。他和宗次郎是相识的,和善地招呼着我们进屋。他才刚从丹波的女儿家返回来不久,和八岁的小外孙住在一起。
我摘下笠帽,有些胆怯地望着他,生怕他的一句拒绝会让宗次郎更加尴尬。
可是,这位名叫忠野的老人家无碍地摆手说:“没有关系,去年也有个西洋来的姑娘租了我的房子住。”
我愣了愣神,又听见他对宗次郎鞠躬致谢:“真是感激您常来教胜太剑术。太麻烦您了,冲田师傅。”
仔细看,躲在他身后的那个小男孩正乖巧地对宗次郎招手。
“抱歉喔,胜太,今天不能教你了。”宗次郎露出他一贯开朗的笑容,说,“不过,以后我们会有很多时间可以练习的。”
忠野老伯带我们去看屋子。不是很大,但收拾得非常干净,铺着蒲草做的榻榻米。窗户是朝着南边开的,不久会有暖暖的风吹进来。我想着我还可以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上一些容易生养的花草,等到夏天,会陆陆续续地繁茂起来,就觉得非常地高兴。还有,门口挂着的芦苇隔断,据说冬天可以御寒,夏天可以散热。廊下有一方小小的水池,静下心来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击打竹片的声音,走近一点,会看到水池边上布满了碧绿又茂盛的青苔。我很喜欢这样的地方,一种跟英美居室风格截然不同的素淡静谧。
我还在屋子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副油画,画面上的景象是一个晚霞漫天的黄昏,狭窄的小道,归来的旅人,从一个矮矮的木板墙头伸出了一朵白色的小花。宗次郎说,这叫夕颜。
简简单单的画,色调却极其浓艳,只有那朵朴素的夕颜花暗自流露了画画的人别样的心情。乍看一眼,熟悉的感觉立马扑面而来。
无处不在的维维安。
宗次郎赞叹:“画得真好,看着就像站在画面里面。”
我笑了笑,把它递给蹲在门口张望的胜太,礼貌地说:“麻烦你放到别的地方去好吗?”
有些事,有些人,永远不能原谅。那个年纪的我就是如此地倔强。
忠野老伯留我们吃了顿便饭,我不喜欢萝卜的味道,偷偷趁主人家不注意赶紧倒到宗次郎的碟子里去。他无奈地对我笑,夹起一块就放在嘴里去了。饭后,我们坐在屋子里面,喝老伯亲手碾磨、冲泡的抹茶。听说这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宗次郎一本正经地说:“不要东张西望,专心一点,要怀着这是一生仅有的一次机缘的心情来品茶。”
我不太理解,忍不住又开始幻想和宗次郎一起喝英式下午茶的情形会是怎样的呢?这个国度的一切,我一直在努力着去适应,有一些新鲜,有一些惊喜。沉寂下来之后,我对伦敦对父母的思念也在悄悄地滋长。如果他们也能坐在这里喝喝茶,认认真真地审视我所爱的少年的话,该有多好。可是世事无法求全责备,就像萝卜的味道虽然不好,可是团子还是很好吃的。总的来说,我挺满意的。
我们一直待到了黄昏时分才告辞。霞光万丈,空气中弥漫着氤氲的绚烂,一轮蛋黄一样圆的落日静静地挂在我们身后。
“这位老人家人很好的,租他的宅子住,我外出值勤的时候也可以安心一些。没有人会欺负你的。”宗次郎微笑着说,“你觉得怎样呢?”
“我现在只想要飞起来。”我张开双臂,感受着风从指尖流淌而过。
“那我带你一起飞。”他目光炯炯地回应我。
然后,我们像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样,在京都安静又狭窄的小巷子里,如嬉闹的孩童般一前一后地追逐着。不经意甩头,看到一朵白色的小花倔强地孤立在墙头砖瓦的缝隙间,随风摇曳。那是只在黄昏盛开的夕颜。
“我宣布,从这里到那条路的拐角,都叫做‘冲田街’!”我边跑边回头,对我的男孩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