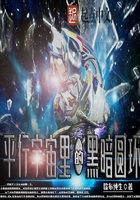“采玉,天色已晚,咱们先找家客栈投宿,明天再打听楼家吧。”
说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公子,年约十五、六岁,身材纤瘦,一身深蓝布衣,头扎壮士巾,风尘仆仆,一脸疲倦,想必是长时间赶路所致。
“小……哦,不,公子,好啊,咱们已经赶了这么些天的路,我都快累死了。”
搭话的人也有十四、五岁,同样一身粗布衣裳,书僮打扮,此刻正弯腰捶腿,看样子真是累坏了。
这主仆二人站在城门边商量了一会儿,似是商量妥当,二人背着包袱向离城门最近的“悦来客栈”走去,两人要了一间普通客房,安顿了下来。
“小姐,长安城这么大,你说,咱们明天能顺利找到姑爷家吗?”用过晚饭,回房梳洗过后,名唤“采玉”的小书童对坐在床边,公子打扮的人说。
不用诧异,没错,这位少年文士打扮的“男子”可是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姑娘。她正是连日赶路,千里迢迢从家乡前来长安投靠与她从小订了娃娃亲的夫家的江水凝,而采玉则是她的贴身丫环。
就在两个月前,水凝年迈的双亲双双病故,娘亲临终前拿出一枚翡翠玉镯,说是她夫家当年的订亲信物,让她带着前去京城投靠。江水凝原已听双亲提过,自己曾于三岁那年与一位名为楼煜的小男孩订了娃娃亲,但却从未见过楼煜,只知他家住京城,年长她五岁。可能因她家早年搬迁的缘故,两家已失信十三年了,因此对于投奔楼家,她曾忐忑了许久,毕竟她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何况两家十几年无来往了,谁知道他的未婚夫婿会不会早已忘记这段姻缘另娶娇妻了哪。只不过,父母过世后,只她一个女娃在家,那些附近的登徒子常来骚扰,让她十分不耐,再加上没了父母,没了牵挂,觉得出去游厉游厉也好,于是,她变卖家产,分散钱财,让家中老仆自去养老,自己只带了从小失去双亲一直服侍她情同姐妹的丫环采玉上路了。经过这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二人这才到达长安,投宿在悦来客栈。
“唉,我也不知道啊。”水凝叹息了一声,继续道:“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明天慢慢打听吧,找不到咱们再想办法。”她安慰采玉,也说给自己听。
“也不知道姑爷会不会不认咱们,那咱们可怎么办啊?”采玉还是有些担心,因为这么多年来,她从未听说姑爷家来过人啊,万一他们不认这门亲事,小姐一个年轻姑娘可如何是好啊。
“如果真是那样,那也没关系了,反正原来我也没打算嫁过去,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罢了。咱们不是还剩了点银两嘛,想必置办两间小屋还是可以的,然后咱们就自办更生,买些布料来,绣些帕子、鞋袜什么的去卖,应该也过得去。”江水凝不以为然。她虽出生并不贫贱,但双亲并未对她娇生惯养,平日里也常做些活计帮补家用,自信尚能自食其力,所以并不惧怕没有依靠。
“我是没什么了,本来就是穷人家出身,干这些个粗活也不打紧,只是担心小姐,你好歹也曾是大家小姐,虽然近几年咱家败落了些,但也不至于做这些粗活计来养活自己,如今真要让小姐做这些,采玉怎么对得起过世的老爷夫人啊。”采玉心有不忍,只希望姑爷能记得这门亲事,好让小姐有个安身之所。
“你说的什么话,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这么见外了吗?我什么时候当你是下人了,再说咱们这样家庭,怎与官宦之家相比,要那么多规矩做什么了,反正在我心里,你就如同我亲妹妹一样,既然这些活你能做,我自然也能做,何况此一时彼一时,咱们家已不比往日,爹娘在时,我已想过做些活计,为家里增点钱粮,减点开支,可是爹娘不允,现在就算楼家真的认了这门亲,我也没打算白吃白喝,自己也要做些事儿才好。”水凝说出自己的想法。
“只怕,到时姑爷看到小姐这双细嫩的玉手,不舍得让小姐做哪。”采玉打趣道。
“你这丫头,什么时候学这么不正经来了。”水凝假意打她。
“小姐饶命啊,采玉再不敢了。”采玉马上配合水凝,双手捂着脑袋,蹲在地上。
二人追打嬉戏了一会儿,又聊了一会儿天,因连天赶路,实在太困,就歇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