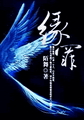弘历惊了,上一世,本就没有忠勇郡王其人,这一世,他不但手握重权,居然还有一个精通解毒之术的嫡妻,既懂解毒,那么下毒必是更形精通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弘历觉得自己连觉也有些睡不安稳了。于是弘历开始查探这个女人的一切,女人所在的伊拉哩家族,弘历打脑子最深处挖了出来,这个伊拉哩家,在他有些模糊的记忆里,做官做得最大的似乎只有阿山,可按说,他早该在二废太子前后就过世的,可现今却活得很滋润,而这个位列伯爵之位的阿尔济,现今已快一百岁了,如果,上一世,有这样长寿的老人,他岂会不知?
莫非,一切的根源,在这个阿尔济身上?
不找出一切的根由,弘历便一刻不得安枕,因此,特派了人去查阿尔济所有的事,其间,他自己则开始想办法要去见一见那位解了无解之毒的忠勇郡王福晋伊拉哩氏。
机会,很快来了,
康熙六十年七月,雍亲王四阿哥请皇父幸王园进宴,而这一次,弘历注意到,自家阿玛居然还找了忠勇郡王一家陪宴。
既然那一家都来了,弘历自然借机见着了这位深居简出的忠勇郡王福晋伊拉哩氏。
弘历是个见惯了美色的,可即使如此,在见着忠勇郡王福晋时,仍然失态了,而他目中的迷恋贪婪之意在一群孩子中,又显得那样醒目,便连年迈的皇帝都注意到了。好在,弘历很快垂下了眼皮,众人便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那一眼,弘历却引起了忠勇郡王一家子的反感。
按说,弘历做了一辈子皇帝,城府便不能说其深似海,也该如渊似壑的,又岂会这般不济,偏他倒霉便倒霉在遇到了沉睡过十年的玉儿。这十年间,玉儿为着打意识海驱逐出那只恶魔,天长日久地不停修炼,以至炼得对灵魂极其敏感。玉儿打一开始,便感觉到了弘历灵魂的异样,因此,那孩子过来见礼时,便短时间解开了自己脸上的迷障之术,于是,弘历很不幸又很幸运地中招了。
而也是弘历这不设防的一眼中,玉儿更清晰地察觉到了弘历灵魂中的问题,那种一张白纸中硬被镶上一块儿黑斑的违和感,怎么遮都遮不住。
这种见所未见的情况,引起了玉儿的好奇心,因此,当发现弘历着人引她到一处偏僻之地时,玉儿便顺水推舟去了。当然,临去前,她留了讯息给雅尔哈齐。
左右无人,玉儿便又把迷障术解了,唉呀,这不算****啦,她只是利用一下自己的容貌,这样会比较简单地得到答案啦。
“你是谁?”十一岁的弘历用一种上位者的目光与口气注视并询问这个美貌远胜常人的女子。
玉儿冲着弘历眨了眨眼,于是,那没有遮掩的凤目波光流转出一种荡人心魄的勾魂之力,她不曾有一言,偏那眼波把她所有的话都说了出来。
凤目之所以称凤,既因其具丹凤之眼的形状,更因其无法言说的那种让人心旌摇动的魅惑之力,那种有意无意间流溢出的似有情又似无情之意,让少年身老大爷心的弘历神为之夺,魄为之迷,心荡神驰间,弘历脱口道:“朕在前世,不曾听闻忠勇郡王此人,更不曾……”
弘历栗然噤声,可惜,为时已晚,那凤目中明明白白的表达出了明了之意。
弘历费尽自己最大的毅力终于闭上了眼,这个女人,是妖,不是人。唯有妖,才能这样迷乱他作为一个帝王的心智。
弘历忘了,他的心智从来便不如他想像中那般坚毅,而做了六十年皇帝,三年太上皇的他更已在后几十年的声色犬马中消磨了意志,更习惯于享受而不是自制。作为帝国的主人,他只需要下令,而后便能得到自己要的东西;可谓顺风顺水了一生的弘历,此时哪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毅力,他享受着天下财富带给他的奢侈生活,为此,甚至不惜放纵和珅贪脏妄法,为他聚敛钱财,世人都道和珅是巨贪,却唯有最上层的人才知道,身为内务府总管,管着皇室生活的和珅是为了提供皇室穷奢极侈的生活才那样大肆揽财至卖官鬻爵的地步。不过,弘历肯定是不会承认此点的。毕竟,何坤在为身为帝君的他服务的同时,自己也为此聚集了巨额的财富,皇帝也没强迫和珅替他自己搂钱不是,和珅的一切,俱是因为他本性便很贪婪。
弘历等到觉得自己再不会被那个女人影响时,方才睁开了眼,看着那个低垂了眼显得柔媚而又异常无辜惹人怜爱的女子,弘历的心颤了颤,脱口安慰道:“你别怕。”
玉儿抬起眸,眼中泛起一丝笑意,这个孩子,自称为朕,那么,是弘历的转世?带着记忆的转世?当了六十年皇帝的弘历,晖儿斗得过吗?
那丝笑意让弘历的心神又晃了晃,这个女子,为了他一言,便这样高兴?弘历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威临天下的那些日子,那时,天下的人都因为他一句赞许的话欢喜欲狂,也因为他一句责备的话而痛不欲生,他是帝国的主宰,所有人的主子……
“你长得真美,比朕见过的所有女子都美,真是可惜。”
那凤眸问道:为何可惜?
“朕登基时,你必是已经年老……”
凤眸闪了闪,带出丝疑惑。
“朕是曾经统治过这个帝国的至尊,朕于二十五岁登基,威临天下六十三载,既使退位为太上皇,也依然能让在位的皇帝伏首贴耳……”
弘历开始诉说自己曾经辉煌的帝王岁月,随着他的述说,那凤目或惋惜、或赞叹、或惊喜、或欣羡……这样的注视下,弘历谈兴深浓,评说着自己阿玛为帝十三载中御政的燥切以及种种不成熟,又得意于自己治国的功勋,说着自己六次南巡花费的巨额银钱以彰显帝国的繁荣强大,又说起自己自号十全老人的来由,对后嗣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还有相得大臣和珅的性情生平……
直说到自己驾崩,弘历才似如梦初醒:他为何对着这个深疑的女子说了这许多?
玉儿站起身,说了唯一的一句话:“你这孩子,倒是做了个好梦。”
孩子?
弘历呆住了,低头看一眼自己未长成的身体,复抬头,惊惧地看着那个女子袅袅而行,终于消失的身影……
这个女人,肯定是个妖精……
出了一身冷汗的弘历觉得口干舌燥,端起身旁的茶盏一口灌了下去,那个女人,迷惑了他的心志,说出了他藏在心底的秘密,说至咽喉疼痛而不自觉,不是妖,更是什么?
摔碎了手上的茶碗,弘历目中迸出狠戾的杀意,这个女人,留不得。
看着快步离去的弘历,一处假山后走出表情深沉的皇帝与满头大汗的四阿哥,同行的,还有面现焦虑之色的雅尔哈齐,弘历方才那不掩杀气的神情让他很是焦急,而妻子明显疲惫苍白的容颜更让他揪心:“皇上,玉儿……”
皇帝一摆手:“去吧。”
雅尔哈齐冲皇帝打了个千,起身后快步追着去了,他可不能让妻子出现什么危险。
皇帝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进了这处偏僻的所在,看了一眼先前弘历坐过的椅子,皇帝站住了脚:“在园子里坐一会儿吧。”
四阿哥闻弦歌而知雅意,赶紧搬了临门的椅子放在园子的台阶上。
等到皇帝坐好,四阿哥急步走到阶下,扑通一声跪在了泥地上:“儿子教子无方,请皇阿玛降罪。”
皇帝看着阶下的儿子,又抬头看了看万里无云碧蓝的青天,半天,方道:“一个孩子的黄梁梦罢了。”
四阿哥紧绷的神经在皇帝这句话后微微有了一丝放松,但是,却仍然跪在地上。
皇帝靠在椅上,六十一年十一月……吗?
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了?
“老四呀,玉儿说得对,你呀,就是个劳碌命,一夜睡两个时辰,朕何时教过你这般不爱惜身子的?”
四阿哥伏首泣道:“皇阿玛,儿子,儿子……”
皇帝的眼眶有些发红,“朕知道,大清现今有不少问题,只是,再急,你也不该这样糟蹋得之于父母的身子骨呀,乱服金丹,以至吐血而亡……老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八字,你以后要每日给朕临一遍。”
四阿哥趴在地上梆梆的磕头,直磕得额头上的皮都破了,看得皇帝只觉心酸,这个儿子,倔强严肃,刻苦勤谨,最是好强不过,又是个爱较真儿的性子,打小,他受了委屈就忍着,忍着……而自小便遭遇了无数变故的皇帝老眼并不昏花,这个儿子,是真正打心底爱着敬着他这个皇父的。
皇帝叹息一声:“起来吧。”
四阿哥又狠磕了一下,之后才站了起来,立在阶下。
“方才,那是你的庶子?”
“回皇阿玛,那是儿子的第五个儿子,因前面有一个三岁时夭了不曾序齿,故这个儿子行四,名唤弘历,是府里一个满族格格所出。”
皇帝点了点头:“弘晖聪慧有智,性情宽厚,谦和又不失决断之力,你教导得很好;弘昀虽体弱,却敏达有识;弘时略差,耳根子有些软,但他待兄弟们却极友爱;这个弘历虽亦有才却性喜奢华,好大喜功,有些浮躁,那个与他同岁的弘昼倒是个识时务的,性子豁达与十二有些像。”
四阿哥唯唯应声。
皇帝又坐了一会儿:“老四啊,你阿玛我身体自四月违和,五月初旬又复感寒遂,觉甚病,以致而今面色稍减,或稍行动,或多言语,便不胜倦乏,虽琏儿****随侍,承欢膝下,费尽心思哄着劝着朕,朕用的饭食也日益减量。这身子,眼看有些不好,你平日,就多替朕担着些朝政吧。”
四阿哥又撩袍跪了下去,虎目含泪:“皇阿玛春秋鼎胜,不过是短时有些不自在,再好好养养,自能复往日旧貌。”
皇帝摆摆手:“朕年已六十有八,古往今来,从未有如朕一般做了这般长久皇帝的,朕……”
皇帝住了口,之后,挥了挥手,“行了,朕该回宫了。”
四阿哥赶紧起身,趋身虚扶着站起身的皇帝,之后,伴着皇帝慢慢往园外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