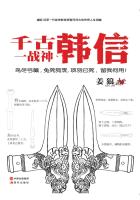译者序
我们都是在旧社会里开始学习航空工程的。在过去,像国内一般科学工作者一样,我们的技术参考资料都来自英美或西欧,始终没有跨出过资本主义阵营的学术圈子。感谢中国共产党解放了我们,除了教导我们将技术和政治相结合,领导我们去开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新生命以外,即使在技术本身范围内也把我们引入一个光明而广阔的世界。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得感谢伟大的苏联老大哥,迅速地给我们运来了许多技术出版物,使我们得知苏联在科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并向社会主义的先进技术学习。
1950年夏天,我们在国际书店买到了这本“飞机构造学”。那时候我们俄文程度还不够,工作又忙,但看图识字,我们知道它内容丰富而新颖。1950年11月,由于一种偶然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工作中得到一段比较空闲的时间来专门读它。读了以后,我们觉得它的内容不但丰富新颖,并且还完整紧凑而有系统;因为在英美的同类著作中,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书,所以便想到尝试翻译。
我们相信这样的翻译是有意义的。
第一、苏联的航空工程书籍,在我国还很少翻译过。这种译作的出版,在中国航空界是会有一定作用的,对热心向苏联学习的中国航空工程人员确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第二、过去国内航空工程书籍一直被英美的原文书统治着,用祖国文字写的书还很少,这是一件非常缺憾的事情。本书如能译成中文出版,将是国内各大学航空系学生很好的教科书,也将是人民空军技术人员和其他航空工程师很好的参考书。
第三、这本书可以纠正过去国内一些航空发展史方面的错误观念。由于从前英美和西欧的影响,国内航空界对苏联的成就所知极少,甚至于以为苏联的航空事业至少在早期是不行的。这本书,特别是绪论一章,告诉我们苏联在航空方面不但在革命成功以后(特别在近二十年来)有辉煌的成就,并且还是有优越的历史传统。伟大的俄罗斯科学家们不但远在1882年就创造了第一架飞机,并且在全世界航空方面一直是站在先进的领导地位。
有理想就得有行动。我们既然希望这本书能译成中文,便在11月底决定动手翻译,作为一件尝试工作。
当时我们最大的困难是俄文程度不够,书虽然可以看懂,但翻译似乎还谈不上。但是,我们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首先,我们之中有人已事先请了一位苏侨教师,专事解决本书中俄文文法和句法上的问题;其次,我们采用了互助的方法,在翻译过程中有困难时集体研究。最后,我们并采取了分工互校的方法。当1951年1月底初步译完了以后,便开始校对工作,方法是由两人根据俄文校核,另外两个人校对中文技术名词和文笔。这也等于说两个人以译者的态度来校对,而另两个人以读者的态度来批评。全书在3月底初校完毕。此后,科学技术出版社又对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前后又由我们做了两次全面修正,到7月初才脱稿。
我们的第二个困难是技术名词的问题,中文航空名词没有比较统一的标准,因此我们在译书时对名词的确定颇费考虑。我们的原则是以通俗即以过去习惯为主,但同时又将过去习用名词中比较不正确的加以修正;凡是可能发生疑问的地方都加以注释,以免误解。虽然这样,我们相信仍然会有一些名词是读者们不能满意的,还希望读者们加以指正。
此外,在翻译和校对的过程中,我们还遇到一个文笔(翻译方法)的问题。我们曾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即尽量对原文忠实。像大家知道的,俄文的文法和句法非常严正,因此有时和中文的语法相去很远;凡有这种情况时,我们觉得仍不应删节原文,而应尽可能把它的意思全部翻译出来。凡是原文有需要说明的地方,我们都另用译者注来解释,而不把它列入正文之内。我们所定的原则,虽并不代表出版者的意见,同时又因为我们能力很差,所以也不能做到完全符合,但为了使读者了解我们的翻译方法起见,我们觉得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在翻译、抄写和校对的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多方面的协助。首先我们应该感谢的是中央重工业部的刘谋佶、王士倬两位工程师,他们受出版者的委托,曾读完全书的译稿,又曾耐心地、详尽地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们的译作得以改善。关于抄写和制图工作,我们曾得到吴家粹、廖壁两位同志和南京大学的庄显章、裘澄涛、方克宁三位同学的帮助;还有中央重工业部的吴大观同志曾读完全部译稿,又协助我们接洽出版;这些都是我们所感激的,一并在此表示谢意。
此外,科学技术出版社在校阅本书的过程中,除了请中央重工业部的同志们负责以外,最后还由他们自己的编译同志亲自动手校阅又建议我们再作一次全面修改。这种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一直鼓励着我们,同时也使我们对人民出版事业的工作态度更为钦佩。
最后,我们愿意再声明一下,我们这件工作是一件尝试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俄文程度很差,因此相信可能有些译错的地方;因为我们写作经验很少,因此名词和文句都很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又加以我们时间有限,所以还可能有其他疏忽的地方;这几方面,都希望读者提出意见,给予批评和指正。我们对一切意见都表示欢迎,并将依照这些意见准备再版时修正。来信请寄北京盔甲厂科学技术出版社转译者。
译者195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