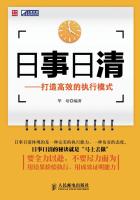自从那天水杉林中被董老师一句无意的话点破后,杨略虽觉害羞,心中却甜甜的极为受用。当天回家,脑海中浮现的竟全是葛怡的一笑一颦,又或者是这样的场景:她坐在草坪上看书,安安静静,看得入迷……杨略闭上眼睛,就看见那张姣美的脸庞,先是那道眉毛,接近眉心处竟呈辐射状,如曙光初透,真是神采奕奕;然后是黑亮的眼睛灵灵活活一转,就漾起一汪秋水,注入他的心田;然后呢,是秀气的鼻子;再然后呢,是一朵玫瑰般的嘴唇;再然后呢,呵呵……一种奇异的快乐渗透了他的灵魂,让他感觉到一种只有春天早晨才有的甜蜜和惬意。
这种感觉,让他仿佛置身一片林中圣地,他躺在春天的草丛中,呼吸着露珠和青草的香气、甲虫和泥土的香气,眼睛紧闭着,好像是在思考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想,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融化了,融化了,化作一股青烟,在草尖上盈盈地眠着,不再有一丝一毫的重量。听,周围的树林里正吹过微风,细细碎碎的仿佛波浪,在柔嫩的心头款款地淌过。此时高高的太阳一定栖息在树林的顶端,一缕阳光经过树枝的筛选,轻轻柔柔地敷在他的脸上,他的脸也温暖而有太阳的光泽了,他又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他在等待什么?等着一道圣洁的白光吗?那道白光里,是不是站着一位穿着洁白轻纱的女孩,脸庞那么白净,那么圣洁……
杨略就猛一睁眼,却只有空空的房间,挂在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得那么从容,自己的心里却满满的,似乎要膨胀开来,绽放开来,像林中的那丛兰花,要散发出淡淡的幽香;像五彩的蝴蝶要张开翅膀,在未知的空间款款而飞。
我这是怎么了?杨略问自己。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当幸福的神灵对你展开笑脸,你将成为一个快乐的傻子,善良的疯子。笑声从心底畅快地奔涌出来,他笑得浑身酥软。
杨略爱极了学校,早上一睁开眼睛,看到窗外微微的曙光,突然一种神奇的快乐浮上心头:我又能看见她了。于是世界顿时变得那么可爱,一切变得那么有意义。衣服的颜色那么鲜艳,质地那么柔滑舒适;牙刷轻轻滑过牙齿的感觉,多像演奏着的钢琴曲;还有早饭多么可口,滋养着快乐的生命……
在街道上,他骑车呼啸而过,一路播撒着微笑,这个城市也能明白他的心情吗?能被他的微笑感染吗?要是能的话,这是多么可爱的传染病啊。
上课时,他认真听着老师的讲课,偶尔也会溜号,目光落在那截细白柔和的脖子上,在黑亮整齐的辫子下面,是不染纤尘的蓝田美玉,还是希腊用来雕刻维纳斯的大理石呢?心里突然产生轻轻触摸的念头,却看到这截脖子的主人正用心地听讲,时不时点一点头,表明已经心领神会。杨略心里就自责,抚平内心的波动,将目光投向黑板。听不多时,忽然又想:我的目光和她的目光,这两条射线,一定在黑板上悄悄会合了。如果目光真的像古希腊学者说的那样,是些无形的小手,那么我的手能轻轻握住她的吗?能不能像拔河那样,将她的目光拉向自己?
脸上就微微露出笑容。
老师看到他的笑容,以为他听到妙处,就欣然提问:“杨略,你说说看,‘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中的‘空’字好在哪里?”
杨略没有听清题目,顿时手足无措,站起来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正尴尬时,低头正看到葛怡惊异的脸,脑海中就更为混乱,脸上一片绯红。
幸好老师没有多问,另外一个同学回答了这个问题,杨略坐下来,不敢再看黑板,也不敢看葛怡,低着头,目光定在课本上,等着脸上的热度渐渐退去。
他总担心老师或者葛怡下课会到他面前来,问他怎么了。于是下课铃一响就立刻闪开,在走廊的人群中逗留许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眼光却时时瞄回教室。等老师出去了,才一步一步蹭回座位。幸喜葛怡也没有过问。说是幸喜,内心却有一种类似失望的阴云轻轻蔓延,竟比上课时的尴尬还让他难受。
要是葛怡上课回答不出问题,自己会怎么做呢?肯定会问问她是否身体不适,甚至萌发出给她补习的念头。而她呢……
一会又想:也许真到了那个时候,很多话自己也未必能说出口,何况人家是个女孩子呢?心中便释然了,起身挨个收作业。他是小组长,这是他分内工作呢。
有几个懒惰分子就哭诉题目太多太难,难以如期完成,并哀求组长大人高抬贵手,给予缓期执行。杨略心情极好,就问:“哪些题目不会?本组长来教你。”音量很高,像是压抑之后,突然解了束缚,一跳却跳得太高,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那几个人就可怜巴巴地说:“还是给我一本做参考吧。”
所谓“参考”,自然就是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抄写”二字。正如夸某女孩子“气质好”时,隐含意思可能就是“相貌一般”。由此可见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岂是那帮憨憨的老外所能领悟?
杨略就说:“不行,人家都有知识产权的,我可不敢以身试法。”
几个人就无奈了,嘴咬着手中的笔,似乎那支笔五味俱全,品咂之间,回味无穷。而笔下的字却像久病的老人靠着墙壁走路,三步一歇,五步一坐。杨略一看这场人与题的战争旷日持久,等待不住,就回到座位,却把葛怡的作业本夹在最里面,而自己的则放在第二,恰好紧紧拥住。这样做时,手是轻轻柔柔的,心也是轻轻柔柔的,一道道波痕就微微漾起在心湖中,眼睛看着葛怡的背影,清清爽爽,一片空明。
以前他们时常讨论题目,各抒己见,意见不合时甚至近乎争吵。
他会说:“错了错了,应该这样这样。你那样不对。”
他会说:“你先闭嘴,让我再从头说一遍。”
他甚至会说:“烦死了,怎么说你都不明白,真笨,自己琢磨去吧。”
而现在杨略却觉事事都有些不同,事事都有无限的情趣了。
当葛怡转身过来,专心给他解一题代数,一边用笔写着解法,一边仔细地解说,不时抬头看杨略的眼睛,说:“对不对?对不对?”随着头的一低一抬,几绺头发就低垂到眼角。她伸出一根白嫩的手指,将头发轻轻编在耳后。杨略看到手指上浅浅的小窝,心里就觉得暖暖的,不免有些走神。冷不防葛怡用这根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对不对啊?”杨略一惊,说:“啊,对,对对对。”
“什么就对啊,”葛怡嘟了嘴,做出生气的样子,“我看你今天不大正常,心不在焉的,我不和你说了。”
“对不起,对不起,昨晚看球赛看得太晚了,今天有点困。”说完,杨略心里一想,坏了,看比赛是前天晚上呢。幸好葛怡不喜欢看球,应该不知道比赛的进程。
果然葛怡说:“球赛有什么好看的?一堆穷鬼花大价钱买票去看一帮百万富翁满场乱跑,有什么意思啊?”
她总是有自己的见地,并且说的还挺有道理。
杨略就笑了:“你说的也对,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花这个冤枉钱呢?”
葛怡说:“这就和斗蟋蟀差不多,大家看个热闹罢了。可惜那帮球星还自鸣得意呢,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大家养起来的蟋蟀而已。”
杨略说:“可这些明星个个腰缠万贯,享尽荣华富贵了呢。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前簇后拥,还有人疯了似的要他签名,多有面子啊。我们谁不想做这样的明星呢?”
葛怡说:“一个愚蠢的人,总会找到更愚蠢的人来为他捧场。”
这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杨略不知道语出自屠格涅夫的《前夜》,以为是葛怡自己的见解,心中就十分佩服,说:“大哲学家,我说不过你,你还是给我讲讲这道题目吧。”
葛怡一笑,刚才她说得激动,倒把正事忘记了。她也不嫌麻烦,把解法从头到脚又讲了一遍。杨略这次听得认真,不多时便心领神会,却不提醒葛怡,看她仔细讲完。葛怡换了个坐姿,脚尖碰到了杨略的腿,忙说:“对不起。”杨略却因为这种小小的接触而倍感甜蜜,就将脚放到容易被碰到的地方。果然,两个人的脚又轻轻触在一起。这次,葛怡却没有把脚收回。也许她是讲题认真,忘记了脚上的触觉吧,也许是她也愿意这样的吧……
似乎有电流从接触的地方传来,杨略心中一荡,脸上旋即就胀红了。
这样的一幕幕每天都重复着,每天又都有新的光彩。就像河流每天都是一个样子,但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日子就这样平缓地流淌过去,偶尔有风,偶尔遇石,都会掀起几层浪纹。转眼一个月又过去了,杨略几乎感觉不到中考的临近。生活对他展示出柔情似水的一面,但冰也是水的一种存在方式呢,他的头就常常碰到硬物,生疼。他的心也出奇的善感,随着葛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他的情绪都会出现起伏。焦灼、快乐、忧虑、温暖,都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像无数气流在他的脸上活动,忽而晴朗,忽而多云,忽而又阴雨缠绵。
我这是怎么了呢?他时常问着自己。没有答案,又不敢将心事说于别人听,故而显得有些淡淡的忧郁。
这一天是三月三十号。下午休息时间,他独自出去逛了书店,偶然取下一本书——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随意一翻,发现一段文字,心蓦地颤了一下。
啊,我的手指无意之间触着了她的指头的时候,我们的脚互相在桌下遇着的时候,我全身的血液要沸腾起来了哟!我缩转来,如同避火一样,一种潜力又把我引转去——我的感官简直一切都昏蒙了呀!——哦,这种细微的亲密使我如何地痛苦啊,而她的无猜,她的不羁的精神全不觉得咧!当她畅谈时把她的手放在我的上面,谈到高兴处更倚近我的身旁,她口中的天香可以达到我嘴唇上的时候——我会倒地,如象着了电的一样。
这分明是他内心的写照啊。他的手有些颤抖,似乎要握不住书了。莫非我真的爱着葛怡了?这种牵挂与甜蜜,真的就是爱情?心头一阵发瓷,呼吸急促。周围一片宁静,人流无声地运动。自己站在了时间的外面。
我该如何是好呢……这样到底对不对……她……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吗?
他的眼睛也有些飘忽,眼前的那些文字仿佛并非写在书上,而是像小树苗一样,一直蛰伏在他的心里,而今忽然被唤醒,立即舒展枝条,挺挺地向上生长,撑开圆圆的叶子来,吐出娇娇的花儿来。
那么,它会结出甜甜的果实来吗?
他将书买回了,薄薄的一册,捏在手中来到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水杉林中坐下细看。这个时节,水杉的叶子也像十六七岁的孩子,身量接近成人,也能静静思考些大问题了,却还是那样嫩嫩地淡绿着。水杉之间,艳艳的开了许多桃花,都是粉色的,像是刚从杨略心中采撷了来,每一朵都有无限的故事,都尽情地绽放着。
杨略全然被这本书吸引了,为维特的欢乐而雀跃,为维特的伤怀而悲戚。看到后来,维特便是他,他便是维特了。维特的所见就是他的所见,维特的所感就是他的所感。那么绿蒂呢?她会是葛怡吗?葛怡会像绿蒂那样以善良的方式拒绝他吗?眼中就不免留下泪来。
不知不觉,天色渐渐变暗,而晚读课的铃声也响起来了。他急忙站起来往回赶,却忘记擦去泪痕,教室门口与余振撞了个满怀。余振打了个趔趄稳住,正要开骂,看到杨略有些异样,就问:“杨驴,你小子这是怎么了?”
他说话向来大声,这么一嚷,立刻吸引来众多眼球。
杨略这才意识到,就解释说:“没事啊,沙子吹进眼睛里而已。”
余振说:“这种解释臭遍了街了,只有弱智的琼瑶电视剧里才会照用不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