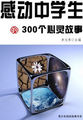泰山正在闭目等死,忽然听到四周又寂静下来,睁眼一看,见一个女郎来救了他,看看那女郎,却与自己素不相识,感到大惑不解。泰山转念一想,不免又替那女郎担心起来,因为那女郎身材纤细,绝不是这群粗壮矮人的对手,若她为了救自己得罪了这群怪人,可是要遭殃的。然而他看了看四周的矮人,脸上没有怒容,只是围着泰山又跳起舞来,那女郎口中也念念有词,像在诵经。泰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演戏一样的一套把戏,很可能是他们的一套宗教仪式。
没过几分钟,那女郎从腰间抽出一把刀来。泰山以为她要杀自己了,然而女郎却用刀割断了泰山腿上捆着的绳索。这时,跳舞的矮人也止住了舞步,围拢过来。那女郎扶起泰山,用很快的动作,把他腿上的绳索,绕在自己颈项间。她拉着泰山走出了庭院,其余的人也有次序地跟在后面。他们走了不少曲折回环的路,穿过了许多庭院,最后来到一座大殿上。殿的中央是一个祭台,四周有殷红的血迹,墙边堆着许多白骨。泰山至此才完全明白,这里就是专为奉祀祭神、举行仪式的地方。原来这些怪人是古代太阳教的后裔,所以等太阳照到泰山身上,就拿他做牺牲,算是太阳选中了他做祭物。至于那女郎急急走来拦住众人,并不是想救泰山,原来她是这教里的女祭司,是特地为了执行她的职责而来的。
女祭司领着泰山,走到祭台前面。这时,靠东南角落的一扇门开了,走出一群女郎来。她们的装束很像男人,腰间也围着兽皮,用皮带或金带缚着,长发披肩,用金圈束着,分为五绺,用小金环挽在头顶上,从金圈的两边,挂着连环金串,一直垂到腰部。她们的样子虽不十分美丽,却还有几分秀气。每一个女郎都拿着两只金环,走到祭坛前,和那些男人一字排开。那些男人走过去,从她们手里拿过一只金环,大家又一齐诵起经来。过了一会儿,从祭坛后面的黑暗处,又走出一个女祭司来。泰山猜想,才走出来的这个女郎,一定是女祭司的首领。看她的面貌,比第一个女祭司年龄大些,模样却十分秀丽。当她走到祭坛前,大家就停止了歌声。泰山抬眼看看她的装束,比其他的人都华丽,金首饰上嵌着宝石,腰间围着豹皮,用金链束着,挂着一把镶宝石的长刀,臂上和腿上套满了金钏,以至看不到她的皮肤了,手里还拿着一根小手杖。她款款走到祭坛前,嘴里也一样诵着经,四周的男女都朝她跪下。泰山听着她悦耳的声音,看着她娇美的风韵,几乎很难相信她是个杀人的女性。泰山心里暗暗惊叹,真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能看到这样美丽的女子。然而祭坛上明明放着一只金杯,准备由她的刀杀人之后盛血用的。周围这一切设置和气氛,和她的天生丽质,竟是如此的不谐调。
当她诵完咒语,转过脸来端详泰山的时候,脸上顿时显出一种惊奇的神情。她对泰山讲了几句话,似乎在等待泰山回答。泰山说:“我听不懂你的话,请你换一种语言说好吗?”
她似乎也听不懂泰山的话,于是泰山换用法语、英语、阿拉伯语、瓦齐里语,最后用非洲西海岸的土语对她说,竟没有一种语言能让她懂,她一直在摇头。泰山看她的神情,似乎非常失望。于是她只好抽出雪亮的利刃来,放好了金杯,准备履行她的职责。
泰山被他们扛到祭坛上,重重地摔了一下,一阵晕眩,昏了过去,过了好久才慢慢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那美女站在他面前,左手托着金杯,右手拿着宝刀,正要向泰山胸口刺过来。
宝刀尖刚要接触到泰山的胸口时,突然她又犹豫地停住了,引起了下面一阵骚乱。她回头去看,泰山也不禁斜过眼睛去观察,只见一个面目凶恶的大汉像一头狂怒的狮子,舞着手里的木锤,见人就打。有一个女郎被他当头一锤,脑浆都打出来了,倒地而死。那些男人虽然举锤招架,但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几个动作灵敏的矮人,早已躲到一边去。只见那恶汉一路冲过来,身边已经死伤了许多,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除了死伤者外,人们都逃光了,现在这间殿堂里,除了这疯狂的怪人之外,只有躺在祭坛上的泰山和站在他身边的美女。那美女吓得全身打颤,四顾没有躲藏的地方,她正要呼救,那凶汉已踉踉跄跄奔上来了。他凶神恶煞地走到她面前,开始对她说话,泰山一听,这怪人的话他却听得懂,原来他说的是猿语,就是泰山在喀却克一族中惯用的语言,那美女回答的也是猿语。泰山听那狂人所说,都是一派无理取闹的话,他威逼着她,她哀求着他,看来,美女的哀求没有效果,他越来越逼近她了,伸出他可怕的毛手,要抱那美女。
泰山趁着这时没有人注意他,就用力挣断了两臂上的绳索,那美女只顾逃避自己面临的危险,已经没有其他精力去注意泰山了,自然不知道他已挣脱了绳索。泰山滚下祭坛,爬了起来,站定了去看时,却不见那怪人和美女的踪影了。忽然他听得祭坛后面的石洞旁边,美女在大声呼救。本来,此时正是泰山逃跑的好机会,可是强男欺弱女,未免激怒了他。泰山忘了自身的危险,一个箭步跳到石洞处。
泰山细听呼救声在石洞里面,他就进了石洞。下面原来有石梯,里面很黑暗,他辨不清该往哪个方向走。他正在犹豫,听到对面地上有人扭打的声音。他定神一看,那狂人正掐住美女的喉咙,使她挣扎不得。泰山立即伸出他那铁钳一样的手臂,抓住那疯狂怪人的肩头,只轻轻一拖,那怪人已身不由己地被拖过来了。那怪人一看,竟是祭坛上的祭品,怒不可遏,跳了起来,张开血盆大口,圆睁怪眼,大吼一声,完全像只野兽一样,向泰山直扑过来。
那怪人手中的锤已掉在地上,他只有双手和锋利的黄牙和泰山搏斗,竟忘记了佩在身上的短刀。泰山自然不甘示弱,扑了上去,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拳脚交加,口咬手抓,打得不可开交。那位女祭司已经爬了起来,身体紧靠在墙壁上,睁着恐惧的双眼,看着这一对野兽似的人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像吓呆了一样,竟也忘记了逃走。
打斗了很久时间,怪人体力渐渐不支,泰山终于占了上风,把那怪人摔倒在地上,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用他那钢铁般的拳头,雨点般向怪人砸下,不到几分钟,那怪人滚在血泊里,一命呜呼了。泰山不自觉地又按照旧日习惯,一只脚踏在死者的背上,仰起头来,准备长啸一声,表示胜利。但是他忽然醒悟到,自己被当做祭品,还身在牢笼之中,不便于自鸣得意,于是便停住了。
那女祭司对于这场恶斗,一直紧张注视着。到此时,她非常感激泰山救了她,然而她现在看泰山,凶猛强悍,比被他打死的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不禁害怕起来。她刚想要逃走,泰山一个箭步跳过去拦住了她。
“慢着!”泰山用喀却克族猿语说。
她停住脚步,定定地看着泰山,大为吃惊,也用猿语问他:“你是谁?怎么也会讲原始人的话?”
泰山说:“我是人猿泰山。”
“你为什么要救我呢?”
“我不能看着一个弱女子被人无故杀死。”
那女祭司又问:“那么现在你打算做什么呢?”
泰山说:“我不要求别的,你能救我出去吗?”
泰山原以为她还会把他捉回去,做祭坛上的祭品,以尽她未完成的职责。但泰山现在已有了武器,从死去的狂人身上解下来了一把短刀,再想捉住他,恐怕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那女祭司对他凝视了许久,缓缓地对他说:“你真是一位英雄。我常幻想,我们的祖先一定也是和你一样的。你可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了这里的财宝,想尽了千方百计历经了千辛万苦,才到这蛮荒的地方,筑造了这座大城池。如果他们没有超常的武艺,怎么能成功呢?我从小就相信,凡是真正的英雄,一定像你这样,身体魁梧,面貌英俊,所以刚才在祭坛上,我开始看见你时,就吃了一惊,我们这里很少见到你这样仪表堂堂的人,及至看到了你的武功,更觉得,你不是我们这里野蛮族中所称英雄的人可比,但是,令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把我当做敌人,来报我们的人捉你、绑你、要杀你之仇呢?”
泰山回答说:“我知道你是信奉了一种宗教,日久成了习惯,自然会遵行宗教所规定的一切,而不是你有意要杀我的。所以我不怪你,只痛恨你们的宗教,让你们愚昧,让你们滥杀无辜。但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们到底是哪一种族的人?”
那美女答道:“我叫兰,我是这里奥泊城太阳庙里的高等女祭司。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以前,从海外一个国度到这里来开采金矿,我们就是殖民始祖的子孙。我们的祖先很有本领,也有雄厚的财力,所以创立了这样的基业。但他们每年都要回祖国去住几个月,他们不能忘掉自己生于斯、长于斯、亲族骨肉葬于斯的故国。他们走的时候,大多在雨季,这里只留下永久居住的教徒、商贩、兵士和管理黑奴的人们。据说他们最后一次回国,就再也没有回来。这里留守的人等了许久,仍旧音信杳然。我们这边的人也驾着船去找过,结果找了几个月,仍如石沉大海。我们曾经派人到祖国去找,据回来的人说,连故国原来的地方也没发现,可能遭了什么自然灾害,连地形地貌都改变了。从那时起,我们就和外界隔绝了,种族的势力也一天天衰败下来,人丁骤减,精神状态也萎靡不振,地盘渐渐缩小,现在只剩下这个小城了。种族之内由于近亲繁殖,人种也不断退化,一代不如一代,直到现在,几乎和人猿差不多了。我们和人猿共居在一个区域,已经有好多年代了,我们的人也变成了原始人,讲着半人半猿的语言,原先固有的语言只有在庙里通用。有时,我们甚至完全讲猿语,正如你刚才所听到的。再过若干年之后,也许我们就会退化得与野兽无异了。”
“但你怎能比其他人文明得多呢?”泰山问。
兰说:“女人和男人比起来,不容易受同化。当年回国去没有再回来的那批男子,都是很优秀的,留在这里的,却都是庸碌无能的人。只有留在这庙堂里的女人,倒是比较有知识的,因为我们祭司这个职务都是由母亲传给女儿的。我们的丈夫,也都是从优秀男人中挑选出来的,一般平庸无能的男人,是绝没有当祭司丈夫的资格的。”
泰山不无嘲讽地大笑着说:“哦!怪不得刚才我看见的那一排男人,从外貌看来,果真是非常优秀的。”
她听了泰山的话,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过了一会儿,终于回过滋味来了,说:“你不要取笑,在宗教里,他们可都是有道的人。”
“那么,这里除了他们,还有面目比较清秀的人吗?”泰山又问。
“其他的人你没见到,样子比他们可怕多了。”
泰山心里不免替她惋惜,这样面貌姣好而又聪慧的女子,一生的幸福竟断送在宗教上,太可惜了。但他此时无暇多想,他不能不担忧本身的处境。问那女子道:“你准备把我怎样处置?你能救我出险吗?”
兰神情严肃地说:“太阳神要谁做祭物,谁都性命难保。假如你再被他们看到,我也没法救你了。但我不愿他们再看见你,因为你救了我的命,我当然应该报答你。然而这很不容易办到,也许要费很多时日,等待机会。不过我相信,我一定能救你出险,快跟我来!别让他们再看见你,假如他们看到我和你谈话,连我的性命也难保呢!他们会说我有意违背神的意旨。”
“如果是这样,你就别救我吧!我估计,我自己设法也能逃出去,因为你救我担的风险太大了。即使你救了我,我心里也不安!”泰山立刻坚决阻止着她。
但她又坚决不愿意接受泰山的劝阻,无论如何要救他脱险,她诚恳地要求泰山跟她走,说:“你现在出去,反而使我担嫌疑,不如你先藏起来,让我独自回去,告诉他们说你打死了那个疯狂的人,我因受惊过度晕过去了。我醒来之后,不知你逃到哪里去了。这个说法入情入理,他们会相信的。反正当时他们都逃光了,没有一个人在场。”
她急忙拉了泰山的手,经过了许多黑暗的走廊,来到一间小小的石室门前,说:“这里是一间阴牢,平时不会有人来。他们绝不会想到你在这里,他们之中谁也不会有勇气到这里来冒险找你。你在这里放心藏着,天黑以后我再来。那时,我们再商量逃走的方法。”
她说完就走了,剩下这位格雷斯托克爵士独自闷坐在奥泊城的阴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