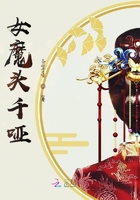男人拿着橡皮,把前天、大前天的“?”都擦了。不仅现在用的这本,上一本也没放过——嘎吱嘎吱地全擦了。一边擦,男人还一边想: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夜里,男人做了个梦。“?”们排成一队,边跟他挥手,边浩浩荡荡地向远处走去。
(平成十年八月十四日)
“每天写短篇故事的话,想点子就成了桩难事吧?”经常有人这么问我。
说实话,刚开始写这《每日新话》的时候,手边的点子有好几十个,新点子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令我不由地想:一百篇、两百篇算得了什么,多少我都能给你写出来哦,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相比之下,困难的倒不如说是怎么抽时间来写。或是外宿时,在旅馆里写了传真回家,或是妻子在医院里吊针时到附近的咖啡馆里笔耕,或是在往返东京的新干线上写完带回去,等等。
然而,渐渐地,随着逐步适应了如何挤时间,我不得不在找点子上费尽周折。平时总随身带着点子便条本,想到什么就立刻记下来。假如在两手都拿着行李,或洗澡时手边没放便条的时候,不记下来的话,就常常会忘了。
因此,坦白来说,我好多次都标上了“?”不过我很快就不这么干了。因为写了“?”又回忆不出什么,看了不是更来气吗?
所以,我从这个故事的中途就开始吹牛了。吹牛也无妨,这又不是随笔,必须把它写成小说才行。
啊,最后那个“?”排成队的梦,算是我免费附赠吹的另一个牛吧。
收录于《日课·每天三页以上》
D的来信
第一封信
别来无恙?小生,上月开始搬来此地。这屋子很久以来无人居住,几乎算是废屋,我得稍花些气力做番修缮。
不远处便是大海,拉开移门,低头一看就是。冬天恐怕会有点冷,风也会刮得猛些,我也不知会住到何时,不过眼下甚是惬意。
我正在源源不断地写诗。屋子距村子并不远,日常生活并未像想象中那般不便。你一定要来我这儿玩玩。
——D
第二封信
还好吗?小生,宛如生活在童话世界中。
今天,敞开门的房间里跳进来两条飞鱼。我烤来吃了,很快活哦。
诗,多得能出诗集了。
来一次吧。
——D
第三封信
近况如何?我简直过着有如天国、有如梦幻的生活。
前天,有只章鱼爬进家里。
今天,飞入一只海鸥。章鱼被我吃了,海鸥则放飞了。
诗想写多少就能写多少。
快来玩吧。
——D
最后一封信
最近精神头还好吗?我的劲头可是越来越足。
飞鱼也好,章鱼也好,总是自己往家跑。海鸥也是常客,来的东西真是千奇百怪。
昨晚,睡觉时没关门,有人从外面往屋里窥视。我起来想看看是谁,让它逃了。月光下我看到,那是人鱼。
我可没吹牛。不信的话,你自己来看看呗。
——D
我所造访的这户人家,房子距离悬崖很近,破烂到几乎谈不上“家”。并且D并不在那里。别说D本人,那里没有任何生活用品,丝毫看不到曾有人居住的痕迹。
问了问附近村里的人,说D大概的确在那房子里住过。然而,某个晚上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怕是悄悄地搬到别处了吧。
我百思不得其解地回到了家里。在那之后,再也没收到过D的来信,也再没听到过D的消息。我在想,他可能被大海掳走了吧。大海给D送去了飞鱼,送去了章鱼,送去了海鸥,甚至还送了人鱼。
于是,大海把D,连同D的所有物品一股脑儿都卷走了,难道不是吗?当然,这种说法是解释不通的。不过,我还是忍不住会这么想。
(平成十年十二月八日)
为什么用D这个名字——我必须从这里开始解释。事到如今才说,恐怕会招人诟病。这每天一则的故事里,我决定尽量不出现固有名词。固有名词会给人先入为主的印象,偶尔出现了相同的人名或地名,要是让人觉得对不上号可就麻烦了,这就是用D这个名字的理由。
因此,需要出现固有名词的时候,我就从字母A开始,按B、C、D的顺序排列下去。排到Z就再回到A开始。其实,这只不过是个非常手段,并非什么可以滥用的方法。全书读下来,应该就能理解了。
这个故事似乎会招人嘲笑,可感觉上也有种诡异的清爽感,当然自己说出这话多少有点王婆卖瓜的感觉。
有些看过它的人会边说“不错啊”边点头称赞。其中,还有人会觉得“你啊,每天写故事写得痛苦死了,想破罐破摔了是吧,文章里可都流露出这感觉了哦”,那可是您看错了。绝对没有这回事。
收录于《日课·每天三页以上》
常葆心情明亮
出门买面包时,初升不久的太阳钻入云中,只有云层下方那橙色的火焰在闪烁光芒。
今天,或许会碰上什么好事。倏地在心头浮起的,是几天前听到的一句台词:常葆心情明亮。
这样的话,据说对身体也有好处。没错,那就往这方向努力吧,常葆心情明亮。
那是个阴郁而寒冷的早晨,吐息都是白色的,我出门买面包。
天很冷,想到今天的工作,心情越发沉重。可是,我必须常葆心情明亮,常葆心情明亮。
开门时,呼呼的寒风扑面而来。加油,加油,常葆心情明亮。
忘记欠债的事,工作也总会有起色,顶着寒风往前迈。
“勉强让自己心情明亮开朗的话,面孔就像抽筋似的。”偶尔有人会对我这么说,自己照照镜子,也有这感觉。可,这是因为心情并非真的明亮,是情绪问题。为了不令面部抽筋,得想想办法保持心情明亮。
倾盆大雨之中,出门去买面包。手脚都淋湿了,好冷。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溅了我一身的水,我不能认输,要常葆心情明亮。
用柔和的表情,用并非抽筋而是发自内心的柔和表情,向前进,常葆心情明亮。
工作陷入了瓶颈,催债的步步紧逼,昨天开始腹部剧痛,睡眠不足,天虽然放晴可风依旧很冷,今早我也要出门买面包。我要常葆心情明亮。
然而,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到时累积起来的压力不会一股脑儿爆发吗?这念头掠过我的脑海。那样的话,我会不会抄起手边的东西到处乱扔,揪住身边的人对着他们狂吼呢?
或许会,但这是到那时候才会发生的事。能撑得住,就必须撑下去,常葆心情明亮,常葆心情明亮。
(平成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用自己的方式在加油,所以你也加油啊,也给我加油啊,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想折腾一篇东西出来(欠债什么的是虚构的),结果写成了这样。
说实话,这不就是自虐般的无病呻吟或是自我陶醉的小丑吗?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真是苦涩。
收录于《日课·每天三页以上》
占领椅子的怪物
早上九点多的时候,醒了一会,犹豫着是否要起床的当口又睡了过去。似乎没什么要紧事,也不必写稿子,精神便放松了下来,再次睁开眼睛,已是中午一点左右了。
睡过头啦,我边想边起身,打算穿衣服的时候,瞥了一眼桌边——那家伙出现了。我的书桌不带抽屉,而是连着木质靠背椅的那种。
椅子上,正坐着个长了圆盘形脑袋和细长手脚的绿色家伙。它身长应该有一米,手脚缠绕在椅背和椅腿上,占据了整把椅子。又出来啦,我心想。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只要我睡觉超过下午一点,这家伙就会偶尔出现并占领我的椅子。它到底是何方神圣,到底有何贵干,我是不知道。只是我很明白,它似乎总盯准了我偷懒或松懈的时机跑出来。
真糟糕,这家伙一旦粘上椅子就很难再离开,硬扯的话会相当费力,必须等它什么时候高兴了自己从椅子上下来。
不过,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必须用到书桌的急事。我穿好衣服,下楼洗了脸再回来。这家伙——在我看来就跟鬼怪一个样,姑且叫它怪物吧。怪物一如既往地粘着椅子,仿佛这上头有什么好玩的或是乐趣似的。圆盘形脑袋既没有眼睛鼻子也没有嘴巴耳朵,让人一点都猜不透它在想些什么。
放在桌边台子上的电话响了。我把手伸到怪物脑袋旁拎起话筒。是催稿电话。
一开始我还没搞清楚为什么要催稿,说着说着就记忆复苏了。确实,我和对方约好今天会把稿子传真过去,而预定表记错了一个月。
跟对方表示会在今天发过去之后,我挂了电话。得赶紧动笔才行,可是书桌被怪物占了。能把它一整团儿搬到别的椅子上去倒也好了,可我实在找不出一把合适的椅子。
至今为止,我做过许多次尝试,因此知道要挪动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我还是打算努力一下让它离开椅子。我靠近椅子,抓住它的肩膀部分,用力拉起来。
它的身体算不上冰凉,那种橡皮的触感好像橡皮做的玩具青蛙。可是,这块橡皮一拉就伸长了,并且可以伸得无限长。怪物加强了盘住椅背和椅腿的力道,以示抵抗。
肩膀部分不太容易使劲儿,这次我双手抓住它的脑袋用力往上提。它的脖子越拉越长了,可手一松,它又啪地弹回了原位。接着我把它缠在椅背上的手指一根根扒开,扯着手腕拉,可只是手被一个劲儿地拉长了。
再来试试它的腿,拉不下来。我两手抱住它的身体想把它从椅子上拉开。可它只是手脚不断伸长,身体却并不离开椅子。
果真行不通吗?我从书桌旁退到被窝上坐下。还有稿子要写,不得不写,把这个事情告诉催稿方请求推迟交稿——当然,我的念头里没有这个选项。
这种鬼怪故事,对方信了才见鬼了。虽然怪物就在我眼前,但说出去别人信还是不信,这种判断力我还是有的。
再试一次吧。我又一次靠近椅子,开始了与怪物的拉锯苦战。拉也拉了,抓也抓了,拧也拧了,还竭尽全力地拖得老长,可怪物就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长在了椅子上动也不动。苦战之际,这怪物身上的橡皮泥味儿越发浓重起来。
我听说过形状记忆合金,不过这家伙算是形状记忆吧?能记住怪物的原形并变回怪物的橡皮泥,但是,又是橡皮泥又能记忆形状,怎么想都太离奇了。说到底,真有这种东西存在吗?我脑海里万马奔腾,结果,我拿它束手无策。
你这混蛋怪物。这样下去只是浪费时间罢了,我只能等怪物自己从椅子上下来。
从书架上抽出来一本书,我戴上眼镜往楼梯走去。找了级台阶坐下,装作看书。
三分钟。
五分钟。
又过了一些时间,似乎是怪物从椅子上下来了,进入了我的余光。
可是,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对方正在试探我才故意搞出这种把戏来的,在我有意要坐上椅子时它又会跳回去,重新占据椅子。凭借至今的经验,我能肯定——还得等。
怪物从椅子上下来,在椅子旁边来回移动着,它正在窥探和预测我的行为。我继续装作看书,应该说,我的确被书的内容吸引进去了。忽地抬起头,只见怪物正往窗前走去。
这段距离的话,我应该会比它更快抢到椅子。我冲了过去,抓住椅子,一屁股坐下。怪物想跳回来,可我比它更早一步,已经没有怪物能坐的地方了。
它在原地愣了两三秒钟,最终,往房间的角落走了过去,那里堆了录音机、电视机、CD、录像带和衣服等杂物。随后它逐渐淡化,隐去了身姿。是消失了吗,还是化身为了什么,反正我是不知道了。
无论如何,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怪物只要消失了,这天就不会再出现。直到下回,我懒散地睡到下午一点以后,发现它又出现在我椅子上,其间什么事都不会再发生。
天已经黑了,我在桌上铺好稿纸,开始聚精会神地写起来。
怪物至今还不时会出现,因为频率不高,我差不多都快忘了,并且,只要我不睡过下午一点,它就不会出来。
假如,我是说假如。假如怪物更早一点,并且每天都出来的话,我就不得不把它当回事儿了吧。我就必须在怪物占据椅子之前起床开始工作了。
这么一来,我肯定能在工作上更加精益求精,写作量也会大大增长了。当然,那样恐怕会太勉强自己,以至于因过度疲劳而病倒吧……
保持目前这种状况,不是挺好的吗?
(平成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对于这个故事,肯定会有人解读说:这是作者潜在意识的实体化表现,或者是作者负罪感的戏剧性象征吧。不过,解读终归只是解读,很多情况下,作者们常常喜欢把非现实的素材当作现实来戏说一番,难道不是吗?
以前曾有那么两三个阶段,我工作到黎明时分而一觉睡到午后。仿佛是为了确认自己是个自由职业者而采取了这种毫无成效的做法吧。写《每日新话》的那段时期,早已没了这个习性,也可能是被严令禁止喝酒的缘故。
因此,这个故事便是以“假如有这么个怪物可就麻烦了”为出发点而产生的联想。实际上,真的很糟糕吧。不过,看到它的人(此处并没有规定它只会出现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好玩吗?若是变成影像就更是如此了。
收录于日本笔会文集《熟悉的风景变化之时》《日课·每天三页以上》
奔跑的植动物
快递送来一个纸板箱,是“生物保护育成同盟”寄来的。这个团体的名字前所未闻。总之先把箱子打开,只见里面还有只箱子,上面放着一封信。我念了起来。
这是新品种的植动物,每天花一小时照顾它,持续十五天后,它将为主人带去愉悦。您爱生物吗?如果您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请每天抽出一小时给它。无论何时开封都无妨,从开封之日起,成长就开始了。
就是这么一封信,对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我一点没有养它的兴趣。扔在一边,大约过了十天,有个朋友打来电话:“你家有没有收到过生物保护育成同盟送来的东西?”
朋友说:“看起来好像是跟环境保护团体有关的人送来的呢。我培育了几天,出怪事了,花居然跳舞了。”
“跳舞?”我疑惑地问道。
“没错,叶子甩来甩去,根部还打着拍子跳舞呢。这都连跳两天了。”
“到底为什么要送这么个东西来啊?不过,让它听听录音带,它就会和着音乐跳舞,要说好玩,也是挺好玩的啦。”朋友说道。
被吊起好奇心的我打开了箱子,里面只有一个插着茎状物的花盆,还有本育成说明书。每天花一小时浇水,施以附送的肥料,并亲切地予以注视——说明书上这么写。
水和肥料不必说,这注视是怎么回事?不管那么多,我决定先按指示做起来。茎里抽出了枝条,叶子也长了出来。只是这株来历不明的植物,就能跳舞吗?
每天不仅得浇水施肥,还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简直就在傻乎乎地浪费时间。尽管这么想,我还是认真地坚持了一周左右。茎长长了,枝叶也茂盛起来,渐渐地,根部也从土里窜了上来。
昨天,还有今天,我都没注视过它。我也是很忙的,只给它浇了水、施了肥。这植动物什么的,个头长到了一米多高,根部在茎的周围四散铺开。
最近,没浇水、没施肥,让它自生自灭去吧。因为我实在太忙了,而且也没法保证每天回家。它要枯死就只有枯死了,没办法。
今天一看,花盆里空空如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是谁给拔了?但家里人都说没干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花盆扔了。
来到街上,只见有个怪东西正在路上跑。叶子拍打着,根部不停地扑腾着——是植物在跑。还不是一两株,十几株凑成一群一起奔跑着。这么说来,我家那株莫非也逃出去跟它们跑在一起了吗?
镇上到处都跑着这种植动物。所谓植动物,似乎就是起初为植物,养着养着就变成动物的东西。它们会跑到有水的地方,吸饱之后继续奔跑。
之前,养了那株会跳舞的植动物的朋友,又打来电话问:“你家那株养得怎么样啦,会跳舞了吗?”
我如实说了。
“那可糟了。”朋友慌忙地说,“赶紧收拾好行李逃走吧,很危险的!”
“你指什么危险?”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