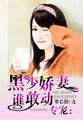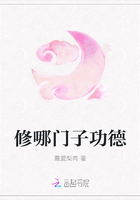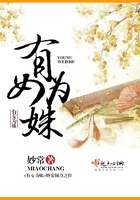1947年12月——1966年
1947年春节过后,胶东牟平县城南5公里的螞峡河村,回来了一个闯关东的人,他的归来,改变了从峭峡河参军到东北去的杨宗贵(杨子荣)母亲宋学芝一家的命运。由于儿子杨宗贵45年9月参军走后,二年多了一直没有来信,家里也不知他的情况究竟怎样了。这个回来的人散布说,看见杨宗贵在东北下城子穿着件黑棉袄,带着个貂皮帽子,匪里匪气的。这下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村支书把宋学芝叫到村公所,追问杨宗贵是不是当土匪去了,宋学芝当然不能承认。可是当村支书要杨宗贵最近的来信时,宋学芝却茫然了,儿子确实没有来信啊!
就这样,村里把给杨家的军属待遇停了,代耕也停了。村里不仅三天两头盘问宋学芝,还多次找杨宗贵媳妇许万亮,追问杨宗贵的下落。愁得许万亮整天眉头紧锁,眼泪不干。嫂嫂唐淑玉无法安慰弟媳,只能陪着默默地掉眼泪。邻里乡亲们,还有杨宗贵儿时的伙伴们,谁都不相信杨宗贵能当土匪。可是,谁也无法证明杨宗贵没当土匪。
1948年的春天来了。由于杨家被取消了代耕待遇。在杨宗贵名下的几亩地上,哥哥宗福在后面扶犁,母亲宋学芝、妻子唐淑玉、弟媳徐万亮在前面拉犁。一家人累得气喘吁吁。
宋学芝气不过,几次到村里去找,村里不管;她又到县里去找;县里也不管,叫她回村里解决。宋学芝一气之下,带着干粮,颠着小脚,步行百里之外的文登专署上访。可是专署的人也答复,你儿子是在县里当的兵,解决问题还得回县。
宋学芝并不气馁,紧咬牙关,在村里——县——专署的窄窄山路上,不知留下了这个坚强农村妇女裹过的小脚的多少脚印。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大军南下,宗贵没有信;开国大典,宗贵没有信。许万亮忧思成疾,病倒在炕上。
1952年的秋天,许万亮没有等到宗贵的来信,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因许万亮无后,没有人给“抓土”,按着当地规矩,不能入杨家的坟地。宋学芝只得商量宗福、淑玉把儿子克武过继给宗贵家的。宗贵、淑玉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哭着答应了。于是,五岁的杨克武在出殡时,一路披麻戴孝,喊着娘,给许万亮“抓土”送到了坟地。
时间仍在无情的逝去,宗贵始终没有来信。宋学芝心里反而平静下来。她不在哭闹,只是隔一段时间到政府去问一下:“我儿子被你们打发当兵了,是死是活,你们给我个准信。”
1957年1月1日,宋学芝终于得到了儿子杨宗贵的消息,一张盖着牟平县人民委员会大印的优军字924号“失踪军人通知书”送到了她的手中。通知书证明杨宗贵确系参加我军,由于没有音信,按照上级精神,被列为失踪军人,家属仍享受革命军人家属待遇。
捧着通知书,宋学芝落下了既激动、又心酸的眼泪。宋学芝在人前站起来,出来进去又挺直了腰杆。
1958年11月12日,一张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又发到了她的手中。上写:“查杨宗贵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伤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落款是“主席******”。
宋学芝因儿子杨宗贵是革命烈士而受到社会之尊崇。
1966年,宋学芝辞世,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