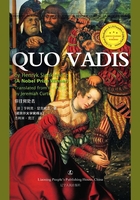开来了两辆警车和一辆推土机。警车还未进村就拉响了警笛。红蓝两色的警灯转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彩。羊角村水泥抹光的街道便于车辆行驶,警车不必减速就可以通行,车里的警察稳稳地坐着不受颠簸,他们把大盖帽子的黑带紧紧地绷在下巴上害怕掉了帽子实在是多虑了。推土机跟在警车后头,钢铁的履带在水泥街道上轧下白印,嘎啦啦轰隆隆的响声像开进村子的坦克要推倒老百姓住的房子。警车和推土机开出村子向南,没有去村委大院停留,直接跑上田边的土路,向着状元岭的方向开去了。
没有人知道警车为什么会跟推土机一起来。警车要是来抓人,也没有必要动用推土机,羊角村没有哪一座能藏人的房子需要推土机推倒。状元岭老矿井的矿工三龙和工友走出罐笼,看见警车闪着警灯开上来,三龙惊异地说:
“警车来干什么?”
工友笑着说:“来抓你。”
三龙说:“老子也不犯法,谁敢抓我?”他虽然这么说,听了警笛的鸣叫还是有些心惊肉跳的,可是看看警车后面的推土机,又把心放下了,他还没有见过警察抓人用推土机开路。
警笛鸣叫永远不会像敲锣打鼓一样给人带来欢乐,就是有会劳动的推土机相伴也不能叫人安心。警车和推土机刚刚跑上通往状元岭的土路,羊角村的村头就呼呼啦啦地涌出了人流,没有人号召,没有人指挥,大家全都朝着一个方向奔跑,就是警车和推土机前进的方向,边跑边互相探问:
“警车来干什么?”
“推土机来干什么?”
没有人提供答案,有一点却很明白,那就是不祥。吉普车在人流后头鸣叫喇叭,大家纷纷让路,看见家庆坐在车里一只手抓住铁制的把手是一种冲上去打仗的样子。大壮的手一直按着喇叭跟前头的警笛一起鸣叫,大壮无法超车,推土机庞大的机身挡在土路中间,大壮的喇叭按得再响也没有用。
警车和推土机开到元岭老矿井跟前停下,大壮同时驾车到达。警车的车门打开跳出了警察,一个个都是大盖帽子的黑带紧紧地绷着下巴一副模样,他们不说话在四周散开手持警棒,稽查队周队长赤手空拳朝着推土机招招手,推土机轰隆隆地开到废石堆跟前。家庆用盖过推土机轰鸣的声音大喊:
“干什么?”
周队长冷冷的声音只让家庆一个人听见:“封井,强制执行。”
三龙一直守在矿井跟前,他说:“凭什么封井?”
周队长不说明理由,只说:“谁妨碍执行,铐起来带走!”
此时跑上状元岭的村人已经黑压压站成了一片,他们的呼喊像林涛滚过山岭:
“凭什么封井?”
“凭什么封井?”
周队长不理村人的呼喊,朝着推土机摆摆手,推土机铲起一堆废石,轰隆隆推着驶向井口。人群呼啦啦地涌上来,警察挥舞着警棒阻挡,三龙躲过警察黑色的棒子跑到推土机前头,横着躺下来。周队长指着三龙大叫:
“铐起来!”
警察还没有动手铐三龙,又有几个青壮汉子跑到推土机前头,和三龙并排躺倒。周队长声嘶力竭地大喊:
“铐起来!全都铐起来!”
羊角村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一下子抓走这么多人,他们大喊着“拼了!拼了!”,向前涌来。警察的警棒挥舞着触到了人的身上,有人惨叫着倒下。三龙从地上一个高蹦起来喊:
“警察打人了!打呀,打!”
村人一齐呐喊着:“打!打!”跟警察扭打起来。警察的警棒不能一下子把一片人同时击倒,有两个大盖帽子绷住下巴的黑带子没管用,滚落到地上被混乱的大脚踩扁。家庆的喊声响在骚乱的人群上空:
“别打,打警察犯法!”
大家乱纷纷地停下来。三龙不肯罢休,叫着:“他们先动手打人!”
周队长的制服被撕掉了两个扣子,他把剩下的扣子自己撕掉敞开衣襟指着三龙说:“铐起他来,就是他带头闹事,铐起他来!”
两个警察把三龙扭起来,家庆不等他们拿出铐子,冲到跟前阻拦,说:“别抓他,我是矿长,是我不让封井!”
周队长盯着家庆说:“你真的不让?”
家庆说:“不让!”
周队长再一次朝着推土机摆摆手。推土机的轰鸣刚刚响起,李春林走进了人群中间。看见了李春林,家庆不再像矿长那样严肃地说话,连骂人的话都出来了,他说:
“春林,****的来封井!”
李春林问周队长:“为什么封井?”
周队长说:“越界开采,不执行停采通知,强制执行。”
李春林说:“说我们越界,谁作的结论?”
周队长说:“矿管所。”
三龙说:“是李俊打过来了,是他越界!”
周队长指着三龙再一次下令:“就是他带头闹事,铐起他来!”
李春林把两名警察挡住,说:“等等!”
周队长面冷如铁:“铐起来!”
李春林说:“周队长,你真的要抓人吗?”
周队长说:“谁妨碍执行公务,就抓起来!”
李春林说:“那好,你抓我吧,我就不让你封井!”
周队长说:“李春林你再说一遍。”
李春林提高声音说:“我是羊角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就不让你封井!”
周队长说:“李春林你不要后悔。”
李春林说:“我当了支部书记,为羊角村的老百姓办事,还没有后悔过。”
周队长说:“你别怪我不客气。”
李春林说:“到了法庭上,我不会跟你客气的,我要起诉矿管所,包括你稽查队!”
周队长说:“好,李春林,我等着你!”他向警察一扬大盖帽子的黑带绷住的下巴,还没有说话,警察的手上亮光一闪,李春林的双手已经被牢牢地铐住了。家庆和村人随即而来的叫喊喊不开李春林手上钢铁的械具,只把状元岭的松树震荡得索索发抖:
“不准抓春林!”
“不准抓俺书记!”
三龙抄起一柄铁锨冲向警察:“跟他们拼了!”
李春林不等三龙挥出第一锨,霹雳般大喝一声:“三龙,你发昏!”
羊角村的人从来没有听见李春林这样的声音,三龙被吓住了,握着铁锨呆呆地立在原来的地方。
李春林的声音仍然很大:“三龙,你不要命啦!”
三龙扔掉铁锨大叫:“抓我吧!抓我吧!”
李春林的声音略微放低一些:“三龙,你犯傻啊!”
三龙疯了一样扑到李春林跟前扭他手上的铐子:“让他们抓我吧!让他们抓我!”
李春林摇着头:“三龙,你个傻兄弟,你能扭断铐子啊?”
三龙声泪俱下:“大哥——”
周队长把手一挥:“带走!”
“不能走!”家庆张开双臂迎面拦住,村人密密层层站在家庆的身旁身后,警察要想带走李春林,需要从羊角村老百姓的血肉之躯上踏出一条道路才行。
李春林帮警察解决一点困难,他说:“家庆,你闪开。”
家庆站在原地不动。
李春林说:“家庆,别硬碰,找矿管局复核,请律师起诉。”
家庆说:“春林,叫他们抓我,我进去,你跟他们打官司。”
李春林说:“家庆,我年轻,身体好,比你抗折腾,你进去受不住……”
家庆热泪涌流:“春林……”
周队长重复一遍机械的命令:“带走!”
家庆身旁身后的人群一动不动,喊声如潮:“不能走!不能走!”
李春林说:“家庆,你领着大家闪开。大家闪开吧,都闪开吧。我回来当书记,没有做什么大事,就干了这个金矿,为这点金子,带来了这样的麻烦,老少爷们不顾身家性命来保我,我知情了。大家放心,我还会回来的,很快就会回来,回来以后我还领着大家挖金子,过好日子,拼上命,我李春林也要为父老兄弟做事,要不我就对不起大家这份情意。我知情了,闪开吧,大家都闪开吧,硬碰没有好处……”
李春林的话像一阵风吹过密密的树林,风过处闪开了一道缝隙,李春林从闪开的缝隙中走向警车。大壮在李春林举步走向警车的同时发动了吉普车,他驾车向前一直开到李春林跟前,打开车门。周队长问他:
“你干什么?”
大壮回答:“叫俺书记坐自己的车。”
周队长说:“你捣乱!”
大壮不理他,叫李春林:“春林哥,上车!”
李春林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壮你……”
大壮含泪催他:“上来呀!”
李春林语声哽塞:“大壮,你也犯傻啦?哪有带着铐子坐自己车的?”
大壮甩一把眼泪:“上啊!”
李春林一仰脸把眼泪压回去,嘱咐大壮:“好好给家庆开车,他还要出去跑呢。”他紧走几步,跨上警车。
“春林哥,我给你开路!”大壮喊着,驾车驶到警车前头,呜响了喇叭,他不开快车,在状元岭上的山路上像京都大街上的仪仗车队,他开到多么慢,警车也开到多么慢。两辆警车依然拉响警笛,可是他们的警笛被大壮的吉普车长鸣的喇叭冲淡了恐怖的气息,没有人再会害怕。
羊角村的村民呆呆地看着吉普车开路的车队驶下状元岭,像看一场梦中的情景,没有想到应该做什么。三龙忽然爆发的大喊把人唤醒,大家才想起眼前的事情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三龙喊道:
“是李俊害了春林哥,找李俊算帐!”
“找李俊算帐!”众人呼喊着呼呼隆隆地向李俊的矿井跑去。
家庆高声把大家喊住:“回来!”
家庆让大家看到事情的本质:“是孙天成捣鬼,是矿管所说我们越界!”
“找孙天成!找孙天成算帐!”
谁也不敢漠视众人的愤怒。跟着两辆警车开来的推土机没有跟着抓走李春林的警车下山,留在老矿井旁边,准备执行公务。可是在怒潮翻腾的人群面前,它根本不敢动,驾驶员楞楞地坐在驾驶室里像个泥塑的假人,他完全相信,他要是再敢铲起废石推向井口,狂怒的羊角村人不能把推土机推进井里,却一定会把他推下去。随着愤怒的人潮涌下状元岭,推土机也跟在后头下山了。
推土机从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没有人命令它留下推倒来孙天成的房子。要推倒孙天成的房子并不需要铁制的家伙,众人的愤怒就能把砖石摧成粉末。暮色中大家把孙天成的房子团团围住,怒吼如雷震动着紧闭的大门和窗户:
“孙天成,你滚出来!”
孙天成不在家里。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他也没有回来。他没有亲自带警察到状元岭老矿井“强制执行”,他叫周队长一个人带领执行公务,他的理由充满了乡情与无情的法律绝不相容,他说他毕竟是羊角村的人无法下手,他需要回避。周队长听了他的理由在电话里用鼻子冷笑,冷笑过后也就一个人带队来了。孙天成在矿管所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再回家,他乘坐了矿管所像一只拖鞋似的小汽车。他已经知道警察抓走了妨碍执行公务带头抗法的李春林,他想不出没有了李春林的羊角村会是什么样子。他不让拖鞋似的小汽车直接驶进村子水泥抹光的街道,他让司机在村口把车停下来。他用不着打开车门就听见了村子里像海潮一样的呐喊,打开车门他听见了他的名字像过街的老鼠一样被裹挟在呐喊的声浪中间,他关上车门吩咐司机:
“先回去。”
拖鞋一样的小汽车在村口掉头,脚趾头朝前脚后跟朝后,向着原来的地方跑回去。
孙天成的家里由他的老婆和儿子坚守。母子二人闭门不出,只要房子不被推倒,他们就不准备看见人,只用耳朵听人家的叫骂就行了。孙天成的老婆胆战心惊,不断地重复一句话:
“可吓死我了,可吓死我了……”
孙胜已经用一只手换来了关键时刻必要的胆量。他像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次次走到窗户跟前,眯了一只眼从窗缝往外看,可惜他已经没有枪了,他要是有枪,他就会把枪托抵到左面的肩胛上,用左手的食指勾动扳机。他走到电话跟前抓起电话,已经失去了打电话兴趣的孙天成老婆又跟儿子抢起电话来,孙天成老婆问:
“你干什么?”
孙胜说:“报警!”
“你还嫌没闹大呀?”孙天成老婆一把夺过电话,牢牢地抱在怀里,再也不肯松手了。
一块石头砸在窗上,窗玻璃哗啦碎了。孙胜就是想开炮,也能把炮筒子从窗户破洞伸出去。三龙在外面大叫:
“砸门!”
大个头的石头一块块砸在大门上,曾经在大年五更贴上了花粘纸的大门无比坚固,牢牢紧闭。
“别砸啦!别砸啦!”
李春林的母亲由二兰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进人群中间,阻住了又一批即将砸到孙天成大门上的石头。没有人想到母亲会出来说话保护孙天成的房子。家庆和三龙等人乱纷纷地叫她“大婶”“大妈”,想把她劝回家去好好歇着,不用管孙天成的房子被大家推倒,三龙说:
“大妈,他害了春林哥,不能轻饶了他。”
母亲说:“孩子,他不仁,咱不能不义,一疃一庄的,咱不跟他这么干。”
刘茂庆叫她“嫂子”,说:“嫂子,姓孙的做得出格了,好狗护村,他连条狗也不如啊!”
母亲说:“兄弟啊,他连狗都不如了,咱还跟他计较什么?人还能跟狗较长短?”
三龙振臂呼号:“拖出来,砸死他!”
已经举起过一次的石头再一次举起来,咚咚地砸到孙天成的大门上。
“别砸啦!别砸啦!”母亲拼命一般凄怆大叫,“砸出人命来,春林就回不来啦!”她禁不住放声痛哭,“别砸啦,别砸啦!我瞎老婆子求大伙儿啦!”她哭着喊着扑通跪下去,痛哭不止。
林芳乘最后一班面包车进县城,车里挂了一帧保平安的已故领袖的相片。相片已经陈旧,看不出领袖穿的衣服原本是蓝色还是灰色,随着车子行驶小相片荡动不止显得落寞而又不安。林芳刚刚结束了长途旅行又走上了新的旅途,这一段旅途虽短却让她心情紧张,不知道前途是吉是凶,已故的领袖不给她明确的指示,相片上领袖的微笑莫测高深。从省城回来坐了火车又坐汽车,她准备歇一会儿再去接芳芳回来。突然的变故像从天上掉下的惊雷一下子炸开,她刚刚出门就看见李春林坐在警车里,她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看不清李春林一晃而过的面容是严肃还是愤慨,李春林好像还对她说了句什么话她也没听清楚,她似乎完完全全地麻木了。她从麻木中醒过来很快便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她没有参加到围攻孙天成房子的队伍中,激愤的人群中不少她一个人的呐喊,她选择她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孤身一人出发了。她是一支孤军,却是一支奇兵。
猝不及防,她出现在副县长王志国家的门口,楼梯口黑乎乎的,王志国刚刚打开家门,她从黑暗中身影一闪,出现了。她像凌空而来的女侠,她却不穿黑色的衣服也不带刀剑,她温柔家常赤手空拳的出现依然吓了王志国一跳,王志国警觉地问:
“谁?”
林芳让门口投出来的灯光照到她的身上,说:“不认识啦?”
“是你,小林?”王志国认出了林芳,连忙把门关上了。他和林芳都回到了黑暗中,他说,“你有事?”
林芳说:“没有事我当然不会来了。”
王志国说:“走,咱到办公室说吧。”
林芳不动,说:“来到你家门口了,你都不让我进家?”
王志国说:“在家里不方便。”
林芳说:“在家里才方便呢。”她用命令的口气说,“开门。”
王志国踌躇着,不开门。
林芳不再等他开门,走上前去敲门。
王志国的妻子从里面把门打开:“谁?”她看见林芳,神情立刻狐疑紧张起来,她紧紧地盯着站在旁边的王志国,她不明白自己的丈夫带一个陌生的女人回家为什么还要敲门,陌生女人的年轻漂亮难道能让丈夫忘记了他不是去别人家里?
“我没带钥匙。”王志国从容地撒谎,优雅地往家里让林芳,说,“进来吧,小林。”
王志国让林芳到他的客厅里关上门说话,他让林芳坐单人的沙发,他自己坐两个人可以躺下的沙发,他背后的墙上挂着大幅的牡丹花,不知道来自哪里的画家用水墨丹青画下了国色天香挂到了王志国的墙上,王志国坐着躺着都能赏花,醉卧花丛,异香满怀。曾经如花似玉的林芳没有看画的心情,她急切地述说此行的目的,她尽量简洁节省时间,她很清楚她用的时间越少,李春林在牢狱里呆的时间越短,反过来也正好是反面。她结束了自己的述说作一个结论,说:
“不用再说了,反正李春林是冤枉的,你把他放出来。”
王志国不说不放,只说困难,他说:“放个人哪能那么容易。”
林芳说:“那么抓个人容易吗?欺负个人污辱个人容易吗?”
王志国说:“小林你别这样说话。”
林芳说:“我这样说话难听吗?好听的我早就说过了,你愿听我等会儿还说给你听,你叫他们放人吧,放了人我就说好听的给你听。”
王志国说:“我总得了解一下情况,各方面做做工作。”
林芳说:“那好,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什么时候把人放出来,我就走。”
王志国说:“行,我给你联系一下,你到招待所去住下。”
林芳冷笑:“哼,招待所,你还想让我上招待所吗?我已经不是那个小服务员了,那个小服务员死了,早死了。她得了心病,没人治,死了,死得好惨……”一阵剧烈的腹痛忽然从她的身体底部生起,迅猛袭击,她痛苦地捂住了腹部。
王志国有些慌乱了:“你怎么啦?”
林芳不说话,揉着肚子在沙发上扭动身躯,她强忍着不叫出声来。
客厅的门忽然打开,王志国的妻子出现在门口,她目光如鹰隼,看看林芳,又看看王志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王志国说:“她肚子痛,你找点止痛片。”
王志国的妻子转身走去,一会儿手里拿着药片回来了,她把药片送给林芳,冷冷地问:“什么病?”
林芳说:“妇女病。”
王志国的妻子阴沉沉地看看王志国,好像要从王志国的脸上看出林芳的妇女病在哪里种下了病根。王志国不动声色,摆摆手让她出去。王志国的妻子把嘴闭严走出去,留下大开的门不关,王志国走过去把门关好,对林芳说:
“你先吃药。”
林芳把止痛的药片放到茶几上,按着肚子说:“我的病没药可治。你叫他们放人吧,我在这儿等着。”
王志国说:“这事儿总得商量商量。”
林芳说:“商量吧,商量不好,把你老婆也叫过来,咱们三个人一起商量。”
王志国说:“小林你逼我。”
林芳说:“你说对了。”她挣扎着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准备随时把王志国的妻子叫过来商量。
李春林在监狱里关押的时间正好与林芳在王志国的客厅里等待的时间相等。监狱里没有挂在墙上的牡丹花。一看见监狱高高的大墙,李春林就想起了小山被剃成了秃头,他不知道监狱里的剃刀什么时候会剃光他的头发。监狱在县城的东南角,向东不远是县里的人民医院,医院向东不远是火葬场。夜深人静时医院里病人的惨叫有时会传进监狱,火葬场焚化的烟尘也会落进监狱的院子里。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布局最初出于什么人的头脑设计,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巧合,生命与死亡希望与恐惧是这样触目惊心地组合在一个三角区域里。夜暮四合的时候李春林隐隐地听见了人的惨叫,以为是监狱里正在审犯人,监狱里水泥筑起的坚固墙壁使人的惨叫听上去变远了。隐隐的惨叫没有让李春林自己感到害怕,他只是又一次想到了小山。小山早已经不在这座监狱里关押了,他去了一个叫做微山湖的地方。那里水草葳蕤莲花接天却不是供小山他们观赏的,小山他们要在荒凉的地方改造出又一片胜境,包括他们自己的面貌,让不像样子的秃头生出漂亮的头发不再剃光。李春林擢发绞首,悲愤交集,弄不明白他们弟兄为什么会来到同一个要被强制地剃成秃头的地方,事情的起因似乎都是金子,可是无辜的金子宝贵的金子分明不应该与人的苦难相联。
李春林失去了时间的观念,一进监狱高高的大墙他就失去了在状元岭上的那份清醒。其实,在状元岭上他也许就已经不清醒了,他也许不应该阻拦周队长他们“强制执行”,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推土机铲起废石把老矿井填平封掉吗?填平的废石当然可以辨明是非以后再挖出来,可是那样做,就好比一个共产党员先写了自首书交到敌人手里,获释后再去参加革命,你也许会把手持了你的自首书的敌人亲手干掉,可是敌人在倒地的时候就从心里把你嘲蔑透了,你在敌人的嘲蔑冷笑里看到的永远是你断了脊梁骨的****样子。你可以被敌人毁灭,但绝不可被他嘲蔑。李春林没有太多的时间梳理他的思想,他只是凭着男人的血性道义的力量做他的事情。他还不能估计他什么时候会被剃成秃头,可是他很清楚他剃成秃头的样子跟小山是不一样的,他饱满的秃头将更加有力地显示壮士的风骨男儿的豪壮,击一掌噌噌地冒出火星。
夜风萧萧,李春林走出监狱的大门打了一个寒噤,大门立刻在他的身后关上了。他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抓起来,抓进来的当夜就把他放了他却不知道为什么了。抓他的不讲道理可以理解,因为正义已经在一些地方被扭曲,放他同样不给他讲个理由,他不知道这个理由被什么人藏在哪里。他一时无法适应大墙外面明亮的灯光,他眯了一会眼睛,拣一条灯光微弱的路往前走。这条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他形单影只,能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在路面上踏出夜里的声音。他走着走着忽然站住了,他定睛看看前头。
林芳站在那里,孤寂落寞,像一根秋天的柳树枝独零零地立在那里。
“林芳……”像是梦中的呓语,李春林喃喃地叫了一声。
林芳没有反应,也像梦中的人。
李春林再叫一声,声音低得好像怕把对方吓着:“林芳……”
好像是一个幻影,林芳的身子慢慢地动了,她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脚底下好像拖着千斤重负,向着李春林艰难地移动,移动。李春林不敢动,他好像在梦中等待着结果到来,他害怕他一动就会把梦境打破。他等待着,屏住呼吸等待着,等到林芳的身体伸手可及,他相信他只要牢牢地抓住就再也不会消失,他便张开双臂把林芳地紧紧抱住了,他在抱住林芳的同时似乎是叫了一声,但是那完全像是一声重重的叹息长长的呼吸,随后,他就再也没有从容的长长的呼吸时间了,长长的呼吸被长长的热吻取代,积久的思念悠远的困惑束缚的渴望全部在长长的热吻里聚集和消解,已经有过的婚姻经历没有给他留下可用的经验,他没有条理分明的体味只有混沌一团的吸纳融汇,感觉中只有林芳的身子在他的怀抱里瘫软,他需要用力扶持林芳才没有倒在地上。林芳瘫软的身忽然扭动起来的时候,先是给了李春林一个错觉,他以为林芳是积极地作出了反应,等到他发现林芳把一只手从他的腰部拿下去揉自己的肚子,他才猛然醒悟了,他惊叫着:
“林芳,林芳,林芳你怎么啦?”
林芳闭着眼睛抗拒腹痛,李春林抱起林芳就跑。他在这一刻十分痛恨监狱没有筑得离医院更近。
天亮后李春林等候在县医院妇产科门口,女大夫走出来叫他:
“林芳家的。”
李春林说:“在这儿。”
女大夫说:“你来。”
李春林随女大夫走进门诊部。他看见林芳躺在小床上正要爬起来,他朝着林芳点一下头跟女大夫走进内室。女大夫在椅子上坐下问他:
“你妻子的病以前看过吗?”
李春林说:“没有。”
女大夫说:“都发展到这样了,一直没看?”
李春林还说“没有”。
女大夫指责说:“你这个做丈夫的,真是失职。”
李春林说:“我不是……”
女大夫打断李春林的话:“你不是失职?你不是失职也是不负责任。你妻子需要马上手术。”
李春林问:“她得的是什么病?”
“子宫癌。”
女大夫的话音刚落,黄色油漆的门重重地响了一下,林芳的身子贴着门往下滑,李春林抢不到时间跑过去扶她。
作过手术的桂莲身体恢复得很快,她原本不是身体里长病要把病割掉,她难产手术把孩子割出来也就舒畅了。她怀胎十月却没有听见孩子哇哇的啼哭,她倒不是那么为没见面的孩子难过——作手术的大夫不等她从麻酸剂中醒过来就把死婴处理掉了——她为自己那么多沉重的日子流泪。手术之后她一身轻松开始思念床上的事情,就是她必须把灯闭掉才能忍受李俊倒栽的小辣椒一样的鼻子她也想,好像女人的快乐饥渴不是从新婚开始的,而是从怀过一次孕消除了负担之后。有了一个兰彩云,李俊舍弃了怀孕在身的桂莲,桂莲的身体复原之后,李俊又拾起来发现了异样的风韵,可是他很快地又拉着兰彩云到处跑了,桂莲不能从李俊那里得到最基本的满足。桂莲曾经想用“哄”的办法把李俊从兰彩云那里拉回来,她身上有孕的时候就是想哄也力不从心,她轻装上阵了也不能奏效,她使尽了所有招数不亮灯跟李俊学螃蟹学鳖的样子,仍然没能让李俊死心塌地守着她一个人,她不怨自己的本事不够,只恨兰彩云的办法更多。
桂莲一个人实在住不满一座小楼,她到楼上有一铺大床的房间里去躺着,楼下睡觉的房间里的大床就空了,反过来也一样。她夜里睡下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搭在楼下床边的椅子上,早晨醒来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衣服了,她打开门光着身子走下楼梯找衣服,才明白她大半夜过后起来尿尿,完了以后又到楼上去睡去了。白天的阳光比夜里的光阴好打发,她从天一亮就把电视打开,不到睡觉的时候绝不关上,她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大,一直到她自己的耳朵也受不了才罢休。电视里的人声音极大地说话,就好像这座小楼里的人多得盛不下叫人不耐烦了。可惜电视里的人往往正说着话就会忽然停住了不说,好像一下子被炮弹击中似的,人影子也忽达一下子没有了。桂莲不知道是停电还是她家的线路出了毛病,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她都急急忙忙地去找刘东。刘东只要跟她进了小楼就认真地检查线路,有时候还没有查出毛病忽然有陌生人大声地说话,两个人同进吓一跳,看看电视里的人戴着礼帽说话一点吓人的模样也没有,两个人又扑哧笑了。刘东看一会儿电视再走,他就是把一部片子全部看完了再走桂莲也这样说他:
“说走就走啊?”
刘东说:“走,走吧。”
桂莲说:“你怕我吃了你呀?”
刘东说:“我才不怕呢。”
桂莲说:“不怕你别走,再坐会儿。”
“坐会儿就坐会儿”,刘东说,刚刚说完了又说,“不行,不走不行,得干活呢。”
桂莲说:“哼,说得好听。”
刘东说:“真的,走啦。”
于是桂莲倚到门上,好像没有力量支撑自己的身体似的,幽怨地看着刘东走出去,走远了。
刘东甩开膀子走路被杨菊香叫住,杨菊香买了个电冰箱叫刘东给她安一个插座接通电源。刘东很快地给杨菊香安好插座插进插头,电源一通冰箱发出呻吟一样的叫声,刘东想起了在电工行业里流行的关于插座与插头的一种比喻,忍不住哧地笑了。杨菊香问他笑什么他不说,那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比喻,他不好说给杨菊香听,他自己一想脸都红了。他红着脸走出杨菊香的家门,杨菊香又把他叫回来,杨菊香说:
“我又想起个事来。”
刘东问:“什么事?”
杨菊香犹豫了,说:“这事不大好说,算了,不说了吧。”
刘东说:“什么事啊?你不说我倒难受了。”
杨菊香又一顿,说:“你看桂莲那个人怎么样?”
刘东说:“你说谁?”
杨菊香说:“桂莲,李俊媳妇。”
刘东说:“人不错,心眼挺好的。”
杨菊香说:“长得呢?”
刘东说:“也不错,跟李俊真是可惜了。”
杨菊香说:“要是给你找这么个媳妇行不行?”
刘东脱口而出:“行。”又说,“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杨菊香说:“不干什么,我就想问问。”
刘东说:“你是不是听人说什么啦?”
杨菊香说:“没有,我看你对她挺好的。”
刘东说:“你是说她生孩子?那样的事谁碰上能不管哪?”
杨菊香说:“管当然管,我是说,你要是心里真的对她有意思……”
刘东急忙打断杨菊香的话:“不,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她没事,我真的跟她没事儿。”
杨菊香哧地笑了,说:“看把你吓的。我不是说你跟她有什么事,我是说……你知道,李俊早在外边有人了……”
刘东说:“我知道,李俊对她不好。”
杨菊香说:“你看着她跟着李俊遭罪,你心里不难受?”
刘东说:“难受也没有办法。”
杨菊香说:“她要是不跟李俊了,跟你,你要不要?”
刘东说:“她怎么能不跟李俊?”
杨菊香说:“她要是跟李俊离婚了呢?要是李俊不要她了呢?你要不要?”
刘东说:“我没有想过。”
杨菊香说:“你这就想,好好想。”
刘东想一想,为难地说:“这话不好说。”
杨菊香说:“说实话,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嫂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刘东说:“说实话吧,我看着她挺好的,她要是没跟李俊结婚,一开始跟了我,我会一辈子待她好的,可她已经跟了李俊了,还有了李俊的孩子……”
杨菊香说:“你就嫌她了。”
刘东说:“不是嫌她。”
杨菊香说:“是什么?”
刘东说:“就是觉得心里别别扭扭的,我也不瘸也不瞎……”
杨菊香说:“小伙子长得还挺帅。”
刘东说:“帅倒不帅,可总比李俊强吧,凭什么李俊不要了我要?”
杨菊香说:“刘东啊刘东,看起来你对她还不是真好,要是真好,你就不会嫌她。”
刘东说:“就是我不嫌她,我愿意要她,我爹和我妈也不能愿意。”
杨菊香说:“他们不愿意不怕,要紧的是你,要看你心里是不是真的对她好,你要是真的对她好,就不用在乎她跟了别人……当然了,这还要看她,看她对你是不是真心,看她对你是不是真好,她对你不是真好,她就是没有跟过别人,你也不能要她,她跟了你,也不会对你好,不会真心跟你过一辈子……”
杨菊香好过来好过去地说了半天,刘东忍不住笑了,说:“嫂子,我看你就对我挺好的。”
杨菊香也笑了,说:“刘东你个兔羔子,嫂子跟你说好话,你跟我耍花花嘴皮子,叫你这辈子说不上媳妇。”
刘东笑着说:“说不上拉倒,咱不要,光棍好过,不要老婆……走啦。”
杨菊香看着刘东的背影大声说:“刘东你别后悔!”
像杨菊香一样关心着桂莲和刘东还大有人在。李俊倒不在其中,新婚之夜刘东给他修好保险丝接通电源,没有照亮大面积的记忆,因为桂莲很快就把灯拉灭了。往后的日子他在家的时候不大看电视,桂莲看电视需要检查线路的时候,他已经和兰彩云在车上摇晃了,他并不知道桂莲和刘东会被电视里陌生人的说话吓一跳。他不知道就放心地拉着兰彩云在外边跑,把矿上的事情交给刁六监管。刁六庆幸自己由司机升为老板助理,就想为老板多操一点心,他问李俊:
“大哥这么成天往外跑,把嫂子一个人撂在家里,放心哪?”
李俊说:“别人我倒放心,我就是不大放心你。”
刁六说:“大哥真能说笑话,我刁六再不是人,也不能上大哥的炕啊。”
李俊说:“那我就放心了,你不动你嫂子,没人动她。”
刁六说:“大哥真错了。”
李俊紧叮着刁六说:“你说有人?”
刁六说:“这话不好说。”
李俊说:“刁六你******别跟我含着半句露半句的!”
刁六说:“我要是说了,不是骂大哥吗?”
李俊说:“你说,我不怪你。”
刁六说:“我说啦?”
李俊说:“说!”
刁六说:“好,我说,我要是不说,老憋在心里,能把我憋出病来,也对不住大哥。”
李俊催他:“别罗嗦,快说!”
刁六说:“那天傍晚,嫂子坐着个小车,人家就那么和她脸对着脸,一直从山上推下来。”
李俊说:“谁?”
刁六说:“刘东。”
李俊说:“你亲眼看见啦?”
刁六说:“这还能假啦?”
李俊说:“他们两个脸对脸?”
刁六点头。
李俊说:“隔得近?”
刁六点头。
李俊说:“多近?”
刁六说:“你想想吧,小推车,傍晚了,看不大清楚了……”
李俊说:“就那么一回?”
刁六说:“就那么一回还不行啊?还有,你不在家的时候,刘东常去你家。”
李俊说:“那个我知道,他是去查线路。”
刁六冷笑:“对呀,查线路,查线路为了干什么?”
李俊气冲冲地说:“你说干什么?”
刁六浮出一脸淫笑:“通电呗!”
李俊猛地朝刁六的胸膛打一拳,骂道:“刁六你他妈放屁!”
刁六躲避李俊可能还要打出的拳头,说:“大哥,大哥你这是干什么?我好心好意给你告诉,你不信拉倒啊!”
李俊像狗一样咆哮:“我不信!我他妈不信!我花钱买回来,不是给别人预备的!”李俊在地上跺脚,像饿急了的狗一样转圈,他找不到什么东西好咬,拔腿就往家里跑。
家里的东西搁在沙发上,穿着衣服李俊也知道这东西无遮无盖时什么样子,那种样子比电视里有时候映出来的更像好东西,因为不让人看的时候多更加保密。李俊踢开小楼的大门就扑向他的东西,狠狠地打一拳,东西发出叫痛的声音大声说:
“你干什么?你为什么打人?”
“干什么?我叫你知道干什么!”李俊一把抓住对方的头发,把她从沙发上拖下,按到地上。
桂莲在地上挣扎:“你干什么?你为什么打人?”
“为什么打人?我的东西我爱打就打,我爱摔就摔,我先打够了摔够了,我再给你告诉干什么!”李俊又在桂莲的身上狠狠地打一拳,抓着桂莲的头发把她的身体拉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说:“你好好坐着,我给你告诉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要问你哪,我问你,我不在家,你都干什么啦?”
“我干什么啦?看电视,给你看着这个房子!”
“你给我看着房子?你给我看着房子,把狗放进来吃我的东西?”
“吃什么东西啦?谁吃你什么东西啦?”
“吃你!吃我花钱买的东西!我花了钱别人来吃……我不吃,行,别人吃,不行!我的东西,烂了臭了,也是我的!”
“你胡说,我不是你的东西!”
“不是我的东西是谁的东西?是刘东的?他花钱啦?他一分钱都没花,他凭什么来吃?”
“谁来吃啦?你别冤枉好人!”
“好人?谁是好人?你看着刘东长得好,他就是好人?他是好人,他可没花钱,他可不能买东西!他一个钱不花,来白吃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你他妈不老实,看着我丑,想跟别人啦?”
“谁跟别人啦?我没跟别人,你可找别人了!”
“我找别人?那是老干给我的,我有钱,我能养起她!你有什么?刘东有什么?没有钱还想玩女人,他凭什么?****他妈……操他妈我去找这个王八蛋!”李俊转身就走。
桂莲喊住他:“你站住!你别去找他!”
李俊回头看看桂莲:“你他妈心疼他啦?你什么时候心疼过我?你不叫去,我偏去!”
“你别去!”桂莲扑上去拖住李俊。
“你他妈到底心疼他啦,好,你心疼,我叫你大疼疼!”他用力把桂莲摔倒地上,狠狠地踢一脚,又踢一脚,发疯一样冲出去。
“你回来!李俊你回来!”桂莲不顾身上被李俊踢疼挣扎着爬起来,身子摇晃两下又倒下了。她放声大哭。桂莲看电视总把声音开大,小楼外面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电视里的女人在哭没有人来看,电视里的女人穿着衣服大哭,衣服还没有脱光就笑了,不值得正经人陪她们难过。
李俊在他的选厂里找到刁六,他说:“你跟我去找刘东,去揍他!”
刁六说:“这样不行,咱不去。”
李俊说:“你害怕啦?”
刁六说:“不是害怕,你这样去揍他没有理由。”
李俊说:“怎么没有理由,你不是亲眼看见啦?”
刁六说:“我光看见他推着嫂子,又没看见他干别的。”
李俊说:“你没看见他干别的,你给我说什么?”
刁六说:“我是怀疑。”
李俊说:“怀疑就行,就去揍他。”
刁六说:“光凭怀疑就去打人哪?你去吧。”
李俊说:“我自己不行,我一个人打不过他。”
刁六说:“你就是能打过他,也不能去,你得抓住证据。”
李俊说:“什么证据?老干打人,从来不用什么证据,想打就打。”
刁六说:“你又不是老干。老干的女人,搁那儿摆着,也没人敢动。”
李俊说:“对,他要是叫你动,他就给你了。”
刁六说:“这就对了。老干是老干,你是你。”
李俊说:“对,我是我,我是李俊,不是老干。我这辈子成不了老干啦。老干的东西,不要了,就给别人,我的东西,不要了,我也不给别人。”
刁六说:“谁要也不给。”
李俊说:“对,谁要也不给,皇帝老子要也不给。”
刁六看见了老干给李俊的东西,说:“兰彩云来了。”
兰彩云风摆杨柳一样摆过来,浑身的好多地方扭出不同寻常的景致,朝着李俊扬起一只手,学电视里的女人吐一个腔调回环上扬的字:“嗨——”
李俊用同样的姿势也扬一下手,吐一个同样的字:“嗨——”像一只公鹦鹉一样肚子里的气还没有出完。
李俊像一只气筒子一直把气攒到夜里,他再用起来的时候就不把气撒到桂莲身上了,他把兰彩云当成一个会叫唤的车胎。兰彩云可真不含糊,李俊的气筒子就是刚刚使了油膏,她也不会有被打得爆裂的时候,她只不过把声音叫得更大节奏感更强让楼下的桂莲听起来更清楚罢了。兰彩云叫出来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桂莲点点滴滴全部听到了,像房顶上漏水滴到水盆里一样,桂莲就是想着不听也不行。她拉起大被把头蒙住,兰彩云叫唤的声音穿透棉被的纤维和棉絮,一直灌进她的耳朵里,凭兰彩云叫唤的声音桂莲就知道李俊站着打气了。桂莲五内俱焚肠子打结披散着被李俊抓乱的头发。等到楼上的声音停下来,兰彩云同样披散着头发出现在桂莲的眼前,桂莲不用看就知道兰彩云的乱发也是被李俊抓乱的,李俊抓乱兰彩云的头发却不是为了打她而是玩她,桂莲气哼哼地不理她。兰彩云却不生气,她主动地跟桂莲说话,好像很奇怪桂莲居然没有听着楼上的声音入睡,她说:
“哟,还没睡呀?”
桂莲擦一下自己的眼睛,不让对方看见她的眼泪。
兰彩云说:“哟,哭啦?”
桂莲扭过脸去,依然不理她。
兰彩云不生气,她发现了桂莲身上令她惊叹的东西便叫起来:
“哟,你这条项链真好!”兰彩云为自己的发现再一次惊叹,“哟,你这个戒指真大!”她伸出自己的手指跟桂莲比量,说,“比我这个大,李俊还是待你好。”
桂莲突然爆发了:“出去!你滚出去!”
兰彩云不动身,说:“生什么气呀?我说李俊待你好,你也生气呀?”
桂莲赶她:“你给我出去,贱货!”
兰彩云不服气了,说:“我贱?你以为你贵呀?李俊告诉我了,她在我身上花的钱比你多,他买你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多钱呢。”
桂莲用两只手往外推兰彩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兰彩云说:“你别动手啊,要是动手,你可打不过李俊。李俊饿了,想吃东西,你给他找点东西。”
桂莲叫着:“滚!滚!”把兰彩云推出门外,把门关上。
兰彩云在门外骂桂莲“泼妇”,桂莲没有开门跟她计较。兰彩云四处搜觅,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香肠火腿和啤酒,她朝着楼上喊:“李俊,李俊你下来帮我拿!”
李俊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你自己拿吧,我得省点劲儿。”
兰彩云咕哝着说:“熊蛋。”自己把吃喝的东西拿上楼去。
李俊成心让桂莲知道他在兰彩云身上到底会有多少力气,他吃过了喝过了肚子里饱撑撑的又开始了。开始的时候他把门关上出于一种习惯好像桂莲习惯闭灯一样,刚过了一会,他就伸出一条腿用大拇脚趾头勾着门把手把门打开,他不终止正常的运动伸出腿去开门,兰彩云以为他发明出了新的招数,很显然此招并没有十分过人之处,兰彩云不以为值得太兴奋,可是她依然叫出极其夸奖的声音,让楼下的桂莲听了发疯。
桂莲真的像疯了一样了。她自己的男人和另外的女人在她的头顶上惊天动地地叫唤,所有的声音全部化成一种不要命的样子在她的眼前展开,楼上的男女不要命的同时还能活命,她却真的活不下去了。她把枕头摔到门上堵不住流泻而来的声音,她把镜子抓起来摔到地上,玻璃破碎的声音掩不住头顶上压下来的声音,她抓起床单乱撕,撕成一缕一缕,裂帛之声听上去像皮肉之音一样刺耳,直透心肺。她无论如何也受不住了,她打开门,冲出小楼,冲出大门,跑上大街。
像勒住脖子的羊乱蹬蹄子敲着一面大鼓,桂莲用两只手敲门。门从里边打开走出了刘东。
“谁?”刘东刚刚问过就认出来了,“是你?”
“是我,我来给你,我来送给你!”桂莲一头扑进刘东的怀里,身上往刘东身上乱贴乱揉,用的力气又大又狠,好像她的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毫不顾惜。
桂莲疯狂的样子把刘东吓坏了,他不知道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应该推开这个女人还是抱住这个女人,他像一棵幼嫩的小树被桂莲摇晃着,他慌乱地说:“别,别这样,叫人看见。”
桂莲说:“不怕,谁看也不怕,走,你跟我走。”
刘东问她:“上哪儿?”
“上我家,上李俊的小楼。”
“李俊不在家?”
“在,他在楼上,咱在楼下。”
“不,明天,等明天我再去。”
“不,就今天,就今天晚上,我给你,走,你跟我走。”
“不,我不去。”
“你怕他?你打不过他?”
“不,这样不好。”
“好!为什么不好?他做他的,咱做咱的。”
“不,我不能。”
“你为什么不能?你不是个男人?”
“不,我是说……”
“我不听你说!”
“你听我说……”
“好,我听你说,我就听你一句话,你说,你喜欢不喜欢我?”
“我……”
“你说,喜欢不喜欢?”
刘东不再犹豫:“喜欢。”
桂莲拉刘东:“那好,你跟我走。”
“不,我不能去。”
“好,不去也好,上你家,你不是自己睡厢屋吗?就上你的厢屋里……”桂莲往里走,要从刘东身旁挤过去。
刘东挡住门,着急地说:“不,别这样,嫂子!”
桂莲定定地看刘东:“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嫂子,嫂子,你别这样!”
桂莲点着头,点着头认定一种东西:“嫂子,好,嫂子,嫂子送上门了,人家也不要,我就贱到这样了……”她开始摇头,连连摇头,“没有意思,真没有意思,我,真没有意思,我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她转身跑去,不管身后刘东如何喊她,她没有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