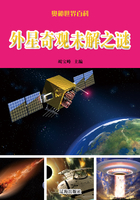在众多的秦淮佳丽中,敢于公开骂皇帝的,唯有郑妥娘一人而已,她口无遮挡,直言不讳:“这大明的天子怎么这么下作?天下的女人尽他挑,管他拣,他还不满足呀!怎么非要找一个多少人吃过的残汤剩羹不可?”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董小宛插嘴道,“宋徽宗不是也照样嫖过李师师吗?”
“那是‘嫖’!他这是什么?又想当****,又要树牌坊。既然喜欢咱们这些老娘们裤裆里的‘香饽饽几’,还当什么‘中兴明主’?”
“哎呀我的妈呀!你也太出格了!”顾横波忍不住地插嘴了:“皇上是我们这些贱人可以随便乱说的吗?甭说如此信口雌黄,就是有此等‘腹诽’也是‘大不敬’的!”
“你可别吓坏了我!”郑妥娘鄙夷不屑地说,“我岂止是‘腹非’?我是堂而皇之的大逆不道。皇帝佬儿又能把我怎么样!”
“那是要活灭九族的!”
这是一句颇带威胁的话,让顾横波一个不乏温柔之气的女子说来,就未免有点滑稽。不料,却被郑妥娘一下子抓住了话柄,她要反击了。
“活灭九族?”郑妥娘冷峻地问,“那你还有‘九族’吗?只怕你连一族都找不到!亲爹热娘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还怕他活灭九族吗?”
“你就不怕——”
“本娼妓无门可灭!”郑妥娘非常自豪地宣布。
顾横波被噎得一句话也答不上来。陈圆圆却不肯轻轻放过她,话语就越发尖刻了;“我不象有的人,期望值那么高。嫁了个‘七品芝麻官’,就做着当‘诰命夫人’的美梦。一心一意地夫唱妇随,一起当奴才!”
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驴,谁都明白她的矛头所指。顾横波让她说得不上不下,一时语塞。
郑妥娘却开始了长篇大论:“咱们跟皇帝本来是互不相干的两类人,完全可以‘河水不犯井水’,他在金銮殿上该作威作福,就作威作福;该卖官鬻爵,就卖官鬻爵。我等在秦淮河上,该搔首弄姿,就搔首弄姿;该上床卖**,就上床卖**。老死不相往来,谁又认识谁?
“可今天,皇帝佬儿偏偏要找我们来了,这就把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埂放在了一起,不比也得比。这一比,咱们可就用不着妄自菲薄了。娼妓与皇帝一样,皇帝也与娼妓一样。不光都是人,而且同样的下贱!皇常与娼妓比较,仅仅多了点手里的权;娼妓与皇帝比较,也仅仅多了个他朝思暮想的**。他那权,就像手里的花生豆儿,得一点点地分给他用得着的人;我们的辰,也像身上的‘香饽饽儿’,得一点点地卖给花了钱的人。他们那权,就是我们那**。
“我们比皇帝更了不起。这是因为他手中的权,我们根本不要;可我们身上的**。他们却非要不可。所以,所有的皇帝都赶不上娼妓!”
郑妥娘说完了,得意洋洋地望着众人。然后,又对着顾横波,挑衅地问:“老娘说的对吧?我的顾大姐。”
顾横波连声地叫;“罪过!罪过!”
趁着郑妥娘高谈阔论,顾横波洗耳恭听的空儿,陈圆圆把董小宛约到了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这是“眉楼”回廊尽头的一个小亭子,掩映在假山背后的翠竹之中。如果不是常客,很难走到这里。董小宛明白:圆圆一定有重大而机密的事情相告了。
岂料见了面,陈圆圆只说了一句“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就大哭着抱成了一团。
已经有很长日子了,两个人只是在暗暗较劲,她俩是“情敌”又不似“情敌”。就一个冒辟疆,和陈圆圆过从甚密,已经到了论婚嫁的地步。但是,陈圆圆也非常明白,冒辟疆心里有董小宛。曾经说过“秦淮河上唯有董小宛有后妃气质”的话。这话传到了董小宛的耳朵里,董小宛就对冒辟疆越发难以忘怀了。
哭了一气,还得说话。话题就是冒辟疆——如果不是这场变故,两个女人决不可能坦诚布公地如此谈论共同的“心上人”,现在,谁都顾不上羞涩了。
还是陈圆圆先开口:“有什么法子呢?‘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也只能认命,男人是虚名累人,女人却是艳名毁人。真的,女人一有了艳名,十个有十个遭殃!男人为了你去争夺,你就得背‘狐狸精’的骂声;不敢为你争夺了,像褒姒、杨贵妃,就都是‘祸水’,要承担亡国灭种的责任。你说,长俊了有什么好处?”
这问题也许问得太深刻了,也许问得董小宛还未来得及思考,董小宛竟一时失语。
陈圆圆继续娓娓说来;“我不是那种想当‘人尖’的人,压根儿就不想立后当妃。到那种地方去跟女人争宠,有什么意思?”
“那你不好不去吗?”董小宛终于有了一个插嘴的机会,“反正有一个死对着他!实在怕死,还可以到庙里当尼姑去。”
“我是为了他,才要到那不是人去的地方的。我当然可以撒手人寰,可他呢?他还有一个家,一个很大的家。他们把底细早就摸去了呀!”
说着,陈圆圆又啜泣起来。
董小宛也接上了这个思路,十分担心地说;“冒辟疆还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伤心呢!”
“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了。他何罪之有?不就是喜欢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吗?可这与那抢了我,却要治他的罪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陈圆圆又悲又愤地说道。
“这天下是讲不得理的!”董小宛也激越地加上了一句。
“我这一走,就只怕再也见不到冒郎了。”陈圆圆幽幽地说,“这是我的一块最大的心病。”
董小宛无法安慰她,但是心里明白,冒辟疆这个潇洒倜傥的年轻公子在陈圆圆心中的位置;也隐隐约约觉察到她找自己的目的。
果然,陈圆圆开口了:“我把他托付给你了,不!是把你托付给他了。不,不!看我都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董小宛却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一阵慌乱裹胁着强烈的羞涩袭击过来。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也该考虑自己的归宿了。冒公子虽然也有不少阔公子的毛病,比喻说用情不专,但那是他们的通病。我看此人是八九不离十的,他对你也极有好感。”
董小宛却越发慌乱了。他眼前浮现出冒辟疆温柔多情的面孔、还有那脉脉含情的眼睛,就有点手足失措了。
自从郑妥娘把他带了来冒充“孤老”之后,她就有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愫,又想见他,又怕见他。见了面,真想说说话儿,却又一句也说不出来。那冒辟疆倒是落落大方,对她嘘寒问暖。她十分喜欢他那极富磁性的声音,耳边似乎老是回响着他的声音。这令她常常遐想:“如果能常常听到这个声音该有多好!”尽管这么一想她就脸红,但是却禁木住常常去想。每每一想,她就严厉地自责:“真不要脸!怎么能跟自己的姐妹争汉子?让他同时嫖自己?那他成了什么人?又会让姐姐处于何种境地?”所以,尽管她对“冒郎”满怀情思,却只能把这种情思深深地埋在心底。
不意今天突然被陈圆圆一下子揭破了。她本能的想抗拒这种裸露,可是一想彼此的处境,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只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这时,只见陈圆圆解开了上衣,在绛红的抹胸下面,雪白的两乳之间,摘下了一块碧绿的玉石。一道绿光映人了董小宛的眼帘,她也免不了目瞪口呆。
不消说,这是那“欢喜佛”。
董小宛当然知道关于这块“翡翠之王”的种种神秘的传说,老实说,她对这块已经脍炙人口的人间至宝,早就十分神往了,渴望能有一天目睹它的神采;只是由于那些传说过分离奇了。她都有点将信将疑。现在,完全在无意之间。突兀出现在面前,那震动真是不可名状的。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十分想问:“它怎么竞到了你的手中?”但是又一想:这是“行中大忌”就蓦的钳口,只把好奇的一双大眼盯住了那玉看。
善解人意的陈圆圆马上说:“这是冒公子送给我的。至于它如何成为冒家的传家之宝的,我想内中一定也会有让人魂飞魄动的故事,只是冒郎还没来得及讲给我听——”
“还有一只,也在冒府吗?”
“不知道。应该是不在吧。据说,冒家几代人都在偷偷摸摸地寻找呢!”
“你还没过门他就把如此珍贵的东西交给了你,可见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董小宛不无醋意地说。
“这是他送给我的定情物,只可惜我无福消受它了!”
说到这里,陈圆圆黯然心伤。
董小宛也只能陪着叹气。
陈圆圆郑重地把“欢喜佛”交到了董小宛的手中,说道:“我希望有一天是冒辟疆能亲手把它挂在你的胸前,让你的体温来滋润它,结一个‘爱情正果’。”
三
红粉劫难升级,国舅对秦淮名妓情有独钟,法外施恩,要一网打尽,全部拉去京都,让她们充分享受“老夫少妻”的风流,于是,秦淮河就沉寂了。
董小宛“避难”到了孝陵侧畔的一所小庙里。那里除了有青灯古佛之外,还有一个与她心心相印的和尚——慧清。
慧清兑现了承诺,在秦淮河上一片混乱,名妓们纷纷作鸟兽散的时刻,来搭救义妹了。
董小宛是悄然消失的,谁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慧清甘冒风险,把她藏在了一座佛像的后面。
“阿弥陀佛!”慧清面色苍白地祈祷,“在劫难逃。”他深知自己要受到“色魔”的诱惑了。一个天姿国色的娼妓,一个青梅竹马的另一半,此刻陷入了绝境,又跟自己孤男寡女地昼夜待在了一起,通常在青年男女之间要发生的事,在他们之中果真会避免吗?慧清实在丧失了自信。他把董小宛放在了佛像后面,实在有着自警、自戒的意图。
果然两人都未能免俗。一天夜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追忆往事的温欣就浓得难以化开,气氛就涂抹上了一层可触可摸的甜蜜。
往事在当初也许只是一瞬问的异样感受;但追忆起来却是刻骨铭心的——
桃花盛开的时节,他——一个在庙里长大的小沙弥,刚刚知道应当力戒“色魔”就受到了“色魔”的诱惑。他跟着师傅“五戒禅师”到一个“在家居士”的家里去布经讲道。师傅与那居士津津乐道“禅机玄理”,他却被悠扬的琵琶声所吸引,寻声走去,就见到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情景:
桃林深处,桃花树下,一个姑娘正在弹琵琶。那姑娘穿着一身粉红的衣裙,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倒影映在清澈的溪水里,与红色的世界浑然一体,让你分不清人是桃花,还是桃花是人。只有一头青丝随着微风飘逸,才传递出动人魂魄的美来。再看那姑娘的面庞,端的是粉面桃腮,此刻正全神贯注,沉浸在乐声的意境中,就凝固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恬静的美。仿佛是晶莹剔透的玉雕,一动不动,却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也许因为小沙弥刚刚成熟,也许因为他第一次端详女人,他只觉得自己有一种飘飘然欲仙的感觉。他弄不清是被女人的绝美锁定在那里,还是被那美妙的琴声捆定在那里。反正他也成了雕塑。
这个时刻并不太长,曲终人立,姑娘就察觉了有人偷听。她一扭头,却见到是常来家里的小和尚。此刻见他痴痴地呆望着自己,就未免一阵慌乱,红晕立即飞满了双腮,同时也就抛出了一个娇羞的眼波:“你怎么却在这里?”
慧清很不好意思了,他要掩饰,就只好说琴声;“你的琵琶弹得实在太好了,真可谓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他说这话,确实是由衷的。眼前的这个女子慧中秀外,博得了他深深的好感,如果不是因为过分矜持,他早就喊出叫好的声音了。
按照常规,一个女孩子得到一个陌生的男人由衷的赞美,该是十分激动的。然而——
女郎听了夸奖,却反而比他还矜持。她不仅没有喜形于色,反而异常冷静地问;“你还听出点什么来了吗?”
“这是一首名曲,叫《十面埋伏》。我不仅听出了千军万马奋力拼杀的声音,那里有战马嘶鸣,刀枪碰撞;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心的叹息。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同类残杀,这又何必!琴声犹心声呀!”
一句“琴声犹心声”可把姑娘的矜持一扫而光,打下了她的一串热泪。她想不到眼前的这个小沙弥竟然是她的知音。
从此,这个孤女就对这个飞来的“知音”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依赖感。她自幼就丧失了母爱,又缺乏了父爱,还没有兄弟姊妹。真可以说:只要有一滴感情的水,就能够令她的情感世界膨胀起来,仿佛一块干涸的海绵,太需要感情的滋润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发育得很早,少小年纪身上来红,就令父亲措手不及,但是情窦却远没有开放。她努力封闭了自己,从不肯给任何一个男人一个温柔的眼神。也许这种封闭如今反弹了,她对小沙弥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她见了这个“非常有学问”的大哥哥会莫名其妙的害羞,想立即躲开,却又绝对挪不开脚步;她渴望见到那双睿智的眼睛,一想到那双眼睛就会在无限甜蜜中心跳不止,但是又十分害怕那双眼睛瞥见了自己。这种时刻她就只想哭。这种哭,往往很快就演化成真正悲伤的哭:养父对自己再好也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她的情愫只能埋在自己的心里发酵。发酵的结果是:她沉浸在甜蜜的悲伤中不能自拔了。
突然降临的灾难令她永诀了这种悲伤,但是,哥哥却又突然出现了,而且是在江南,是在她已经陷于绝境,举目没有一个亲人的江南。她多么想立即扑过去紧紧地拥抱这个失而复得的人间至宝啊!可是哥哥的一身袈裟却在她俩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
“避难”的日子里,她决心突破这道鸿沟。这天,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她俩追忆着清菡居士的往事,说到动情处,这个董小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一下子扑过去,用那粉嫩的小拳头狠狠地捶着哥哥的胸脯,含着满脸热泪,几乎是绝望地喊;“你为什么偏偏要当和尚?”
这喊声令小沙弥呆若木鸡。
“你为什么要当和尚?为什么要当和尚?”那喊声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