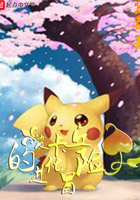夜里,树娥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明天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啦,离开这个她经营了几十年的家,离开这个令她饱尝了辛酸苫辣甜的家,她真有点舍不得。她在考虑着,去丁能住长久吗了与女婿、亲家公的关系能处理好吗7过午吕大婶的话也在心里回味着,这能成吗7孩子们能乐意吗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不成,不成,不能给后人目下笑柄。原始的、传统的、封建的意识链锁又把她紧紧地束缚在旧有的思想篱桩上。第二天早晨,柳树娥早起先来到丈夫李冬至的坟上,烧了些香纸,祷告说:“冬至,明天我要到女儿家长住了,你也不要寂寞,我会常回来看你的。”最后又落了几滴汨,走回家去。一进门就听到老黄牛的呻吟声,她走进牛棚,见老黄牛肚子鼓得象个充满气的大皮囊,圆晔着眼睛,四蹄难受地瘙孪着,嘴里淌出一些腥臭的黄液。树娥吃惊地上前解开缰绳,把牛头轻轻地放在地上,老黄牛费力地呼吸着。柳树娥哭着敲开了快嘴吕大婶的门。吕大婶开口就问:“啥事这么急?是孩子掉到井里了,还是大火上了屋笆?”树娥说:“你快来看看头老黄牛得了什么急病?”吕大婶过来一看说:“先莫急,我给兽医站挂个电话,请个兽医来看看。”树娥又捎信叫女婿大宝来。不一会儿兽医赶到了,拿出听诊器,听了听心脏,又扒了扒眼、唇看了看,说:“你这牛得的是急性胃膨胀,已经很危险了,抢救抢救试试吧。”兽医拿出一根放气针,扎进牛胃里,嗤嗤地放了一会儿气,又打了针,牛的呼吸仍然很微弱,树娥说:“刘医生,再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了?”刘医生看看牛说:“心音已经很弱了,没有什么好办法。”树娥难受地直掉泪。这时大宝赶来了,劝娘说:“娘,别难受了,牲畜象人一样,都有个寿限,大概是它的寿限到了。”中午时分,牛停止了呼吸。大宝向兽医算了医疗费,问娘这牛怎么处理。娘说:“这牛是病死的,为咱家出了力的,你到你爹坟右侧的松树底下挖个深坑埋了它,你想着我死后也埋在你爹的身右侧。”大宝就找了个年轻的熟人,把牛抬上地排车,拉着去埋了。柳树娥收拾好东西,把临时需要的让大宝带着,然后环视了一下屋子,锁上门,难受地离开了家。离开时快嘴吕大婶招呼了几个婆娘来送了送。一连几天,树娥每想起死去的老黄牛,心里就隐隐做痛。她又对雪萍说:“这牛是有灵性的,通人性,可能它不愿到这里来,生了气,就病的。”雪萍说:“娘,那有这么通灵的牲畜,听说这种病主要是吃了霉草和饮食不当的缘故引起的。甭说是牛,就是人得了急病,有的想留都留不住。娘你就别难受了,看看咱的栓栓,你该高兴才是,省的公公看了你这样,还认为什么事不愿意呢。”娘擦了擦眼泪说:“好啦,不难过啦。来,把栓栓给我,明天你和你公公、大宝他们去种花生。”娘接过了栓栓,拍着,打着,哼着,亲着,小栓给姥姥一个笑脸,欧啊地说了些听不懂得话。
树娥住在闺女家,象过去那样短时间住几天倒觉不出怎么别扭来,可一搬来常住,就觉得不习惯。守着亲家公说话做事,总觉得有些胆怯,不象一个人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尤其在晚上睡觉,尽管东间西间,和一个老头子在一个屋里也睡不踏实,有时黑夜里胡思乱想,还做些不着边际的梦。最令她难堪的就是现在的电视剧。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一些男欢女爱、拥抱亲吻的镜头,使她脸红心跳。当和亲家公坐在一起,电视出现这些镜头时,她就借故抱着孩子离开。她想搬进厢屋里去住,和女儿女婿换过来,可已经住上了,也不好意思再开口,时间一长,慢慢地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两个不完整的家庭组合,给这个家带来了幸福和喜气。家庭成员的分工合理而有序,每个人都在用汗水和真情辛勤地描绘着美满的生活。柳树娥除了看孩子刷锅洗碗,瞅空还给他爷们儿缝补浆洗。尽管比自己一个人过时累点,但她觉得不孤独,有生气。看看,女儿女婿和睦相处歹日子也有奔头,心里整天美滋滋的。
有全爷儿仨个一早就下地干活,为了增加收入,春天在土地叫行承包时又多叫了五亩地,加上原来的一共十二亩。六亩花生,忙了四五天才种上。傍晌时,雪萍说:“爹,你先回家去歇歇吧。“这点地头我和大宝种种就算了。”爹说:“你先走吧,回去给小栓喂奶。”雪萍说:“没事,娘给他喂奶粉,吃得甜呢。”有全看看也插不上手干,就回家了。爷爷亲孙子,这是古来有之的,虽然孙子身上没有有全的基因,可他和对待大宝上样,心里没有一点不是亲生的感觉。每次从地里回家,他都从亲家母怀里接过孙子抱抱,然后再送回亲家的怀里口“栓栓,来爷爷抱抱。”有全伸出两手。,“大哥,回来了。栓栓快跟爷爷抱抱。”有全两手伸进树娥的怀里,树娥觉得有种异样的感觉,脸红得象霜后的枫叶,有全嘴里不住念叨着:“来,抱抱,来抱抱。”手在树娥怀里停了一段时间,才把小栓抱过去。每次有全从树娥怀里接小栓眈树娥也感觉到有全成信用手触着自己的胖****,但很快就离开了。这次接触的时间那么长,以至似乎觉得手还在动;心里慌极了。她回到自己那间里,坐了一会儿,稳定了一下情绪,又下来收拾锅准备做饭。这时,大宝和雪萍回来了忑娘问:“种完了?”大宝说:“种完了。”雪萍从公公手里接过栓栓,扯了个板凳在地下坐着给小栓吃奶。她望着娘那慌乱的动作说:“娘,你脸怎么那么红?”娘说:“热的。”雪萍说:“娘,你歇着吧,给小栓吃完奶我做饭。”话刚落下,就听到街门一响,吕大婶哈哈着从门外走进来,“雪萍,来客了,还不快出来接。”
树娥把手往饭襟子一擦,跑出来笑吟吟地迎上去,吕大婶把抱住了树娥:“老伙计,真想死我了。”树娥象见了娘家亲人样,眼里噙着泪水。雪萍也抱着小栓跑出来,亲切地叫了声:“大婶。”吕大婶松开树娥,过来接过小栓抱了抱,一边亲着孩子的嘴一边说:“真好孩子,真好孩子,看这大脑袋,看这大耳朵,官相福相都全了。”小栓象听懂了她的话,笑着依依呀呀地直叫。雪萍逗着小栓说:“栓栓,快叫姥姥。”吕大婶笑着对雪萍说:“闺女,怎样,大婶给你算得对吧。你一家子跟小栓享清福吧。”雪萍一听,又不自然起来。树娥过去接过小栓说:“雪萍,快去炒菜,叫你大婶在这里吃。”雪萍接坡下崖去做饭。大宝在栏里喂上牛,也出来叫了声:“大婶,屋里坐吧。”吕大婶进了屋,问树娥:“大哥呢?”树娥说:“在里间。”吕大婶说:“我去给大哥说个话。”吕大婶进了西间,躺在炕上的王有全忙坐起来说:大婶,你来了,快坐。”急性的吕大婶“嗯”了一声坐在凳子上,没等喘过气来就说::‘大哥,我今天是来给你和雪萍她娘说媒的。你和雪萍她娘搭伙你愿意不愿意?”一点思想准备没有的王有全,一时怔住了。他望望吕大婶;六十岁的老人脸上顿时起了红晕。稍一稳定情绪,又叹了口气说:“你对孩子们说去吧。”吕大婶说:“只要你俩愿意,孩子们的工作我去做。”有全说:“我这么个年纪了,好说。你先和她们商议去吧。”吕大婶又上了东间,把雪萍和大宝叫过去,说:“雪萍,大宝,我今天来是想把你们两家合为真正的一家,你娘和你爹这辈子都不容易,亲家俩一块儿住也不方便,我想给他俩介绍介绍,去登记结了婚,光明正大
地一块儿住,成为一家真正的人家。你俩商量一下,看行不?”
雪萍一听就火冒三丈,说:“吕大婶,俺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别给俺乱孱合了。你要来玩,就在俺家玩玩,说点正经的,要是为这些事,趁早!”大宝也说:“吕大婶,俩老人都这么个年纪了,快叫他们过个安顿日子吧。说什么不好,偏说这个。”吕大婶一片好心却讨了个没趣,任凭树娥忽么挽昭,也不在这吃这顿饭。边往外走边说:“南头亲戚已说好请我吃饭,过几天我再来。”
中午饭,一家人都强作欢颜,心事重重地吃不下去。
人怕闲,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胶东的五月天,长而乏人。树娥拍着睡在腿上的小栓,脑子里又在迷迷糊糊地想着旧事。她先想起她童年时的苦难,又想起年青时的青春冲动和爱情
的苦恼,继而想起结婚后的不幸。想着想着又想到女儿女婿,也想到了有全。上次与有全交接孩子时的慌乱样,是自作多情呢,还是郡老头子有个意思?吕大婶一直撮合着和邵老头子搭伙,老头子乐意吗?女儿女婿的思想能通吗7如果女儿女婿和老头子都愿意的话,街面上不能笑话吗她自己问着自己,一连串的问号,一她回答不上来。她晃着怀中的外孙,似梦似幻地想着,好快嘴吕大婶又来给她说媒了,她认了,有全也同意了,有全那黄胡子茬扎在她的腮上,手捏痛了她的奶,她无意识地打了他一巴掌。怀里的小栓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醒过来,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小栓子的手正在她的****上抓来抓去,她知道孩子饿了,就拿起奶瓶把****添进小栓的嘴里,小栓栓急不可耐地吸吮起来。
天气渐渐地热了,人们都开始换上薄衣薄衫。树娥给他们把洗好的衣服释压的板板正正,拿出来放在炕上,预备着过午上坡时穿。中午;歇大晌的时候,栓栓跟雪萍搂着睡,树娥就下来。她提了两壶开水,关了门,脱去外衣,在屋里洗起头和脖子来。对面大镜子里映出她的身影,她在凝神地端详着,仿佛在欣赏一个女模特。白晰的脸已消失了往日的皱纹,部分白发发根已变黑,衰老慢慢地在脸上减退,年轻时的美,又挂上她那漂亮的眼角眉梢。她发觉,自己胖了,结实了,她摸着她那对挺起的乳房,一股青春样的骚动撂拨的她难受。她没有老,她还不到五十周岁,她每月月经还经常着呢。如果生活在富贵家庭,如果生活在大中城市,她可能还是个令年轻人心动的美人呢。她痴望了一会儿,把头梳好,换上一件茄花色的薄褂子,两只竖起的****令她害羞,她找出女儿过时的白布乳罩,把那对显眼的东西罩住。
穿好衣服后,开门出去倒水,见西间的门敞着,有全正在捣弄牛锁头。就问:“大哥也不歇歇晌。”有全说:“牛锁头绳断了,我换上条皮的。”树娥把亲家公的单衣拿过去,说:“大哥,天热了,好换衣裳了。”有全放下手里的活,激动地两手接过几件叠得整齐的衣服,望着树娥那美丽的身段和漂亮的脸,沉默了多年的心忽地翻腾起来,他想起那天双手触到树娥乳房的感觉,一种饥渴从心底下翻上来。树娥转身欲走,有全扯住了她的手,她转回身,敬慕地望着他,他一把把她搂在怀里,浑身躁热地抖动着。树娥没有反抗,她让他黄胡渣在脸上扎了一下,便轻轻地剥开他的手,转身回到自己房间。这一切都静悄悄地,没有声音,也没有“眼睛”,一股感情的潜流滋润着两颗干涸的心田。夜里,疲劳了一天的人们都熟睡了,整个村子里显得空旷和寂静。大宝家里的两位老人却睡不着,各人都在想着各人的心事。白天的镜头不断地在树蛾的脑子里闪显着,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甜蜜、羞怯、害怕,如果再往下发展呢?如果变成真事嚟她不敢想了,她觉得如果做出丢人的事对不起大宝,对不起雪萍,也对不起死去的冬至。她克制着,她死下心来。西同的王有全更睡不着,自从大宝他娘突然去世,他再没有机会碰过女人的手。他觉得他尽管六十岁了,体格好,心不老,月儿半载的那家伙夜里还起硬,心里有时也想那事。今天他闻到女人身上那味,看到女人那模样,实在控制不住了,他恨不得立刻过去和那女人干一会儿。他起来躺下,躺下又起来,觉得下身发热,老起尿尿,他披衣出去尿一回,回来躺下还是睡不着。躺一回又出去尿,一宿折腾了四五回,但他终于没有勇气到东间去。
早晨起来,大宝问:“爹,你今夜怎么起来那么多次?”爹说:“有点上热,尿频。”雪萍说:“叫东头许医生来看看。”爹说:“不用,喝点浓茶就好了。”“那今天就别下地了。”爹说:“没事。”第二天晚上,有全又这样折腾了一夜,真的病了。他有点发烧,嘴唇爆起了皮。树娥做了好吃的送过去,他也不吃,大宝叫来了老中医许文仙,许医生先试了试脉,又看了看舌说:“没什么大病,下焦有火,与睡眠不足有关。”就开了药吃上。睡到头午十点多钟,有全醒了。树娥一手抱着栓栓,一手端着水杯走过去。“大哥,醒了,喝点水吧。”有全瞪着发红的眼说:“亲家,那天中午我对不起你。”树娥说:“那有什么。”有全说:”你不恨我。”树娥说:“不恨。”有全说:“你是真心话?”树娥说:“都是过来人,真心假心还看不出来?不过我有点怕。”“怕什么,又没别人看见。”“我怕让孩子们知道了,丢人呢!”两人正密密地谈着,听到街门吱的响了一下,树娥抱着孩子走出去,到门外撒眸了一下也没见有人,就又回到屋里与有全拉起呱来。
有全吃了药,睡足了觉,精神就好起来。大宝买了鱼,割了肉,树娥变着样儿做给有全吃。有全也打心里感激这位亲家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