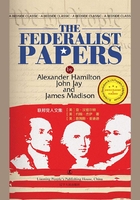老家院里的那棵梧桐树是我亲手所栽。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个春天,我从生产队的苗圃里拣了一棵小梧桐树苗栽在我家院里的西窗下。这棵小树苗只有烧火棍那么粗,不足1米高。栽上后我天天浇水、培土,经常往树根下倒尿。有时家中无人,也偷偷地挖开窝往里大小便。希望小树吸收了这些营养后,快快长大。可是这棵小树苗虽经我殷勤侍候,却长得不快,一年长了还没有我高。恨不能让它立即长成大树的我,心急如焚。我问奶奶,为什么邻舍家栽的梧桐树长那么高,而我栽的这棵不长呢?奶奶说:你今冬把它伐掉,明年就会长高的。我对我亲手栽的这棵树再亲手把它割掉,感情上很是过不去,试了几次都舍不得。后来我了解到其它人家栽的梧桐树真是都到年底伐掉,就狠狠心把它从根锯断,再学着别人的办法在新伐的伤口上滴上几滴豆油,用牛皮纸把它包起来,培上土。果然,第二年就长成二米高的树干,叶子又壮又黑。一年又一年,树杆开始变粗,叶子长得象芭蕉叶。放学回家,先拿竹竿去量一量梧桐树的身高,看它长高了多少,再用线绳量一量粗细,看它长粗了多少。
春天,正是“芳景如屏”时节,芽胚上冒出雄壮有力的芽子,绿中带红,白蒙蒙的绒毛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几天后,筋脉清晰的叶子缓缓展开,象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浑身透着勃勃生气。
夏天,是梧桐树最潇洒的阶段。底下的叶子有蒲扇那么大,白天可以遮荫,夜晚可用来报告风雨。我睡在靠近梧桐树的那间屋里。每当夜半听到梧桐叶上啪嗒啪嗒的响声,就知道天下雨了,立即告诉父母起来收拾天井。父母披衣下炕,看草垛苫好了没有,咸菜缸盖严了没有,衣服是否还在铁条上晾着,檐下的阳沟是否透开了。待一切收拾好后,便回到炕上躺下,闭着眼慢慢欣赏着那雨打桐叶之声,时大时小,时急时缓,如泣如诉,如琴如弦。很快,我便进入了梦乡。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享受,从小生长在城里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自然美境的。夏天,也是梧桐树上内容最丰富的季节,不绝如耳的蝉鸣,高一声,低一声叫得烦人,叫到高潮时连人说话都得大声。树杈上有一个喜鹊窝,那是一双老喜鹊在开春时就一口草一口泥地衔来垒成的。窝垒成不久,便生出三只小喜鹊。老喜鹊整天忙得脚不站枝,来回地采食喂它们,我经常立在梧桐树下看这动人的场面:每当老鹊衔食到窝门,三只小喜鹊便张开小黄口唧唧地叫。老鹊就把嘴里的食吐给它们,再去衔,这样轮流着喂。
梧桐树的一个侧枝下面还有一窝蜂子,蜂子是蜇人的,若干只蜂子围着蜂窝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很吓人。有时我想爬到树上去看小喜鹊,见到蜂窝就打怵,始终没敢爬上去。有一次,我用苇杆粘蝉,没注意触了一下马蜂窝,一群马蜂子向我追来,提防不及,脖子被蜇了一下,肿痛了好长时间。马蜂象卫士一样保护着梧桐树和梧桐树上的一切。
深秋,喜鹊飞走了,蝉儿不鸣了,蜂儿们也躲进了蜂房里,一切都静下来。倏地,“一夜北风紧”,树上的叶儿开始哗哗啦啦地往下落。林黛玉看落花伤感,我看梧桐落叶也伤感,为什么冬天要落叶呢?奶奶说树冬天也睡觉,冬天睡觉也长,真的吗?我心痛地把叶儿一个一个地捡起来,舍不得喂猪,把它们埋在树下。几多岁月,树长我也长,到七十年代初,梧桐树已长到六七米高,一搂粗,枝繁叶茂。
又一个春天,梧桐树竞意外地开出了几朵紫色的花,闻着那香喷喷甜滋滋的桐花味,更使我心花怒放,我知道梧桐树和我一样,成熟了,该结籽繁衍了。到冬天,又加了一道风景,结满籽的梧桐葫芦象风铃一样挂在树梢上,咯啦咯啦地响个不停,引来满树的麻雀吱吱喳喳地叫。
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我这棵梧桐树差点遭了恶运。有人看到梧桐树长得这样粗壮,说我家把粪堆都喂了树,要杀掉归公。我大爷叔叔地哀求了半天,他们才答应,暂不杀。但必须刨一刨树底下有没有粪尿,如果有,树必须杀掉归公,如果没有可暂放一放,以后再处理。他们拿着大镢就在树底下刨,他们没发觉那盘放在西墙根的石磨。结果刨着刨着,两扇石磨扑通一声倒下来,正砸在一个人的脚上,脚脖子被砸断,于是他们只顾得救人,不再杀树了。梧桐树这才亭亭玉立地长着,我心里暗暗地称它为神树。
古人大多都是把梧桐树与秋联想在一起,给人一种凄凉、寂寞感。如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韩准的一潇潇梧桐几度秋,凤凰飞去旧山幽”;白居易的名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等。但白居易寄好友元九的桐花诗则别开一面:“月下花所有,一树紫桐花,桐花半落时,复道正相思,殷勤书背后,兼寄桐花诗。”
以桐悲秋,以桐寄思,这都是文人的事。早些年,奶奶也常说,梧桐长得快,木质好,男人栽树除了盖房结婚做家具外,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用处,就是百年之后,做棺人殓。原想奶奶去世的时候,把梧桐杀了做棺木,只是时代一过,殡葬改革已经推行火化,也用不着这棵梧桐树了。我的梧桐树一直活着、长着,见证着我和我们家不断旺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