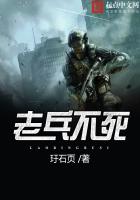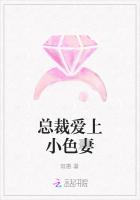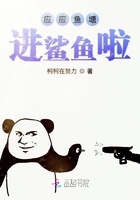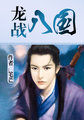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海军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之间会由于相距太远无法及时提供救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要具备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这就意味着每个分舰队都要在其所处的地方占据力量上的优势,因为敌人有可能得到额外的援助,但在己方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看起来总有些不切实际。尽管英国在每一处都有着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但是英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海外战场都不占优势,这就说明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是行不通的,而且非常危险。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提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却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英国船员的危险不断增加,舰船受到的损害日益严重,那些不适合出航的舰船得以保留,而并没有将它们运送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穿越大西洋的时候,英国殖民地造船厂严重匮乏,使得这些舰船得不到及时的修缮。上述关于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不是哪一种在同一时间支出最多,而是哪一种能够在最大限度内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的军事政策相比较英国就更加值得诟病了,因为同盟国作为进攻方,它的条件要比防守方有利得多。当同盟国终于克服了难以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阻碍时,我们发现,英国从来没有阻止或危及它们的相互联合,同盟国完全可以选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作战方式,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发动对英国的进攻。同盟国是怎样利用自己这一巨大优势的呢?它们一边对英国的边缘地带不断蚕食,一边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直布罗陀这块坚硬的石头,法国做出的最认真的军事决策就是向美国派遣了一支分舰队和一支部队,想让目的地的兵力在数量上增加一倍,其结果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殖民者发现同殖民地的对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从而结束了对自己分散力量的控制,其实这种控制对它的敌人是最有帮助的。而在西印度群岛,大多数是趁英国舰队不在场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小岛被攻占,这种轻易地占领说明,只要能够绕过英国的舰队取得胜利,那么其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尽管法国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通过攻击英国的海上力量来解决这个难题,可它从未付诸过行动。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虽然用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换取了一场胜利,但这种胜利却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欧洲,英国政府采取的计划使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军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然而,同盟国却从来没有消灭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在最关键的时候,德比舰队的30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49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战争委员会对此的决定却是围而不打,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同盟国海军作战行动的特点。为了进一步阻拦英国海军在欧洲的行动,西班牙固执地将自己的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在直布罗陀海峡还是公海,只有对英国海军的粉碎性打击才是攻克直布罗陀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途径,而在当初就不止一次地让直布罗陀的守军陷入了饥荒中。
在实施攻击性行为的过程中,同盟国跟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在军事行动的意见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吵得不可开交。从这点看来,西班牙尤为显得自私自利和不讲信用,而法国则比较忠实可靠。为了对付一个共同选择的军事目标,进行两国真正战略上的合作,应该是双方共同期盼的目标,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同盟国在管理和准备上存在着不足,尤其是西班牙在管理和战备方面的效率非常差,根本没办法和英国抗衡。不过,虽然管理和战备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和同盟国选择攻击目标,从而达到战争目的所采用的战略计划和方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于管理和战备问题的调查,不但会毫无意义地拉长这种争论,而且其中纠缠的一些同本书主题无关的细节也会模糊我们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关于战略问题,我们可以简略地认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这一军事政策的主要错误。这种猜想让同盟国的希望彻底落空,因为它们都一心向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标,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把自己最狭隘的目标当成主要目的——或者是致力于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而具备的某种优势上,以至于对眼前能够把握住的唯一机会视而不见。因此就战争的结果来看,它们都一无所得。在我们做出结论之前,有必要再次重申前面的概述,同盟国的目标是为它们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并结束英国称霸海洋的时代。做出的这种报复对于它们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人认为,同盟国不但解放了美国,更加打垮了英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们没有将直市罗陀与牙买加收回,这就意味着英国海军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失,而北方的各个强国都武装中立,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就返回了。随后不久,英国的海军再次崛起,更加飞扬跋扈和专制了。
同英国海军相比,同盟国的准备、管理和作战素质都远远比不上对方,他们所能依靠的唯一优势就是数量上的差距。在同盟国处于攻击地位而英国处于防御地位时,面对英国的海军,同盟国的舰队却采取了防御性的措施,并没有主动进攻。谨慎严肃地运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逐个击溃对方的小股力量,将两方的数量差距拉得更大,接着摧毁对方的海军组织,并推翻这个海上帝国。而这些都没有在同盟国的战略活动中表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的光辉事迹以外,同盟国不是逃避就是仓皇应战,从来没有主动地发起过进攻。只要英国海军能在没有任何打击的前提下在海上耀武扬威,不但法国人的最终目标不会实现,如果因为某一次幸运的机会而让英国人获得一场胜利,那么两方就会恢复到原有力量上的平衡,不这样做是英国政府的错误。但是,如果英国由于某种指挥错误导致它的舰队仍旧不如同盟国的话,那么同盟国没能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便更加值得批评了。进攻的一方不能由于防御方拥有许多基地就分散自己的兵力,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我们上次已经批评过法国国民的民族偏见,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再次得到了展现,看起来这种民族偏见是法国政府和海军军官同时具备的,它是法国海军作战的毒瘤。依照作者的观点,它也是法国海军没有在此次战争中获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所在。这种传统的观点对于它的民众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的,法国一大批极具才干的海军军官满怀着崇高的事业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如此不重要的任务,这就说明传统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有多么根深蒂固。如果这种意见正确的话,它也算是一种警示,就是目前盛行的观点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总是需要检验的;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就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
商业袭击战作为海上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对于像英国这样依靠商业立国的国家具有特别的效果。当时的法国海军官兵就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现在在美国广为流传。一位著名的海军军官拉蒙特·皮奎特写到:“在我看来,打败英国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袭击它的贸易。”所有人都承认,对一个国家商业贸易的袭击,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无疑是海战中最重要的一项辅助性作战行动,并且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都不会过时。但如果把它看做一项根本性的、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战争措施,恐怕也是不对的。当这种幻想披着廉价而迷人的外衣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它就非常具有危险性。尤其错误的是,把袭击商业贸易对准像英国那样的海洋大国,要知道海上强国必备的两个条件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和足够强大的海军。
如果把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集中在几艘运宝船上,就像西班牙那样,它的财政来源就随时有可能被切断。但当财富被分散在成百上千的商船上,这种制度慢慢扩散开来,就像一棵大树,当它的根系深深扎进地里的时候,就不怕种种剧烈的打击了,即使丧失掉某一个比较大的枝干,也不会危及生命。只有通过海上力量控制海洋,进而长期控制商业中心,这种攻击才是致命的,只有通过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战斗并赢得胜利,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200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商业国家,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都把财富寄希望于海洋商业上,而在众多的国家中,它是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权力的国家。英国不将这种贸易豁免资格当做一个权力上的事情,而是一种基本政策,历史也证明,这种拒绝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英国还能够维持自己庞大的海军的话,那么未来将是历史的重复。
英国和同盟国的预备性合约就是为了结束这场延时已久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个协议是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两个月之前就制定好了的,这是这次战争最辉煌的胜利。除此之外,英国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了除多巴哥以外在西印度群岛丢失的全部领土,但是却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国在印度的军事据点也得到了恢复,由于亭可马里被敌人所占有,英国无法反对把它还给荷兰,但它却拒绝割让内格帕顿(Negapatan)。英国还把佛罗里达与梅诺卡还给了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的海军有足够的实力占据梅诺卡的话,这对英国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事实上,在下一场战争中,梅诺卡再次落入了英国人手中。此外,条约还对非洲西海岸的贸易据点进行了某种不太重要的重新分配。
虽说这些安排不重要,但是我们仍要对这些安排进行论述,那就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这些安排的持久性都完全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些没有归属权的海域上的海洋大国。
1783年9月3日,和平条约最终在凡尔赛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