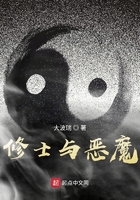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位法国诗人与当时流行的诗歌观念完全脱节。在有生之年,他仅为一小群诗友所知晓。在一九三九年逝世之后的数十年间,他的名声扩散到较大的圈子,他的着作被译成几种语言。不过,他依然是一位仅为相对有限的读者所认识的作家。这位诗人,叫作奥斯卡·米沃什,署名时他一般使用O.V.德·L.米沃什。他来自立陶宛大公国,是我一位远亲。我在这里乞灵于他,是因为我想介绍他的诗观,我认为他的诗观是颇为切题的。
由于他在讲英语的国家里实际上没人知晓,因此我必须简略介绍他。美国对他而言,是他一生的朋友、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蒂安·高斯的国度。他只有一本薄薄的诗集于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出版,译者是肯尼思·雷克斯罗斯,这本诗集如今已成为藏书家的珍本。奥斯卡·米沃什生于一八七七年,虽然他像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科斯特罗维茨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科斯特罗维茨基(1880-1918),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一般称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其母亲为波兰人。那样,有一个异国情调的出身,但他是法国诗人,当他一八九九年初登文坛时,他被视为象征主义第二浪潮的一部分。因而,他所作的某个选择,就显得更加奇怪了:他自愿在精神上栖居于一个较早的欧洲历史时期,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并且对后来欧洲文明发生的事情持不信任态度。他的世界主义教育背景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他精通多种语言,青年时代着迷于德国诗歌,着迷于海涅,尤其是着迷于歌德,后来又着迷于荷尔德林,后者是他在一九一四年发现的。
即便如此,他对于他自己时代的评价却是悲观的。他称他的世纪是“一个闹哄哄的丑陋时代”,他诗中现在的形象并不比艾略特或庞德诗中的现在更欢欣。然而,有某种东西使他与现代诗那些代表人物截然不同:他坚持太平盛世主义,相信新纪元将会到来--不管我们用什么来称呼它--布莱克心目中的“新耶路撒冷”或欧洲大陆浪漫派心目中的“精神时代”。根据奥斯卡·米沃什的哲学着作,这个新时代将在一场末日式的大灾难之后出现,这场大灾难发生的时间,他定为一九四四年左右。他所称的“世界大火”也许是指原子武器的爆炸,这种事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至于那个新纪元,我们仍在等待它出现。据他说,这样一场复兴将伴随一种新科学而来,这新科学将摆脱牛顿式物理学,并从爱因斯坦的发现中得出激进的哲学结论。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些预言的真实或错误。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由于他倾向于未来,他属于一个包括威廉·布莱克和波兰浪漫主义诗人在内的家庭。他相信他将被遥远的后代所阅读和理解,那些后代将比他自己那代人更幸福,因为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恢复了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时代。他与当代诗歌保持距离,他在当代诗歌中看到的是一个全然混乱的形象。我从不掩饰我青年时代对他的作品的熟悉,以及我们的个人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自己做诗人的方式,使我倾向于抵制文学时尚。这里,我将分析奥斯卡·米沃什的一个作品《关于诗歌的一些话》,写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某个时间,并在许多年后,在作者逝世后才在法国出版。它以简洁的形式,提出了在他别的着作中也可以找到的观点。
在开场白中,诗歌被定义为自人类开始以来,自穴居者那些神奇的仪式以来,就是人类的友伴。它永远是“原型的组织者”,以及--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对我特别有用--“对真实的热情追求”:
那神圣的文字艺术,仅仅因为它从宇宙生命的神圣深处涌出,在我们看来便比任何其他表达形式都要紧密地与那精神和物质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是那运动的催生者和指导者。恰恰是基于这个理由,它使自己与音乐分离,后者是一种自泛希腊主义的黎明以来就基本上有效的语言。分离之后,它便参与了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持续不断的变化,并主宰它们。在原始时代以司铎的形式,在希腊殖民扩张时刻以史诗形式,在酒神节衰落时以心理和悲剧形式,在中世纪以基督教、神学和感伤形式,自第一场精神和政治改革--也即文艺复兴--开始以来以新古典主义形式,最后以浪漫主义也即一七八九年之前和之后既是神秘的又是社会的浪漫主义形式,诗歌始终紧跟着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神秘运动,充分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责任。
诗歌是节奏的艺术,却基本上不是一种像音乐那样有效的沟通手段。诗歌的语言使它可以参与并主宰“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持续不断的变化”。奥斯卡·米沃什的时间原型是动态的(如同威廉·布莱克的)和历史的运动,它以三联组的面目出现:天真的时期、堕落的时期和恢复天真的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位法国诗人却继续忠于浪漫主义时代,他选择它作为自己的时代: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可能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寻找奥斯卡·米沃什疏离其当代法国氛围的原因。他高度刁钻,贵族气,其生活方式十足像一个后期象征主义者,他不寻求那类可使他赢得盟友的社会方案。与此同时,他不相信诗歌可以不受惩罚地背对公众:
继歌德和拉马丁--那位写“苏格拉底之死”的伟大、非常伟大的拉马丁--之后,诗歌在迷人的德国浪漫主义小诗人的影响下,以及在埃德加·坡、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的影响下,遭受了某种贫乏和狭窄,这贫乏和狭窄在潜意识领域把诗歌引向一种无疑是有趣的,有时候甚至是瞩目的寻找,然而这种寻找被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带来的成见所玷污。此外,这种小小的孤独练习,在一千个诗人中的九百九十九个诗人身上带来的结果,不超过某些纯粹的词语发现,这些发现不外乎由词语意料不到的联系构成,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精神的或灵性的活动。这种不幸的偏移,导致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出现分裂和误解,这分裂和误解持续到现在,并且还会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一位伟大的、受神灵启示的诗人,一位现代荷马、莎士比亚或但丁,他将通过放弃他那微不足道的自我、他那常常是空洞和永远是狭小的自我,加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富生机和更痛苦的劳动大众那最深刻的秘密。
二十世纪诗歌遭受了“贫乏和狭窄”是因为其兴趣局限于“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换句话说,它退出所有人共有的领域,而进入主观主义的封闭圈。我意识到这里的术语陷阱,因为作者显然是反对从个人观念的角度看待客观存在的世界。然而我们大致可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不同意仅仅把诗歌视为“小小的孤独练习”,并要求一首诗应是他所称的内在活动的表达。这里他很可能是指把个人经验普遍化的行为。米沃什因而抨击了现代诗学的一个基本宗旨:它被法国象征主义者们编成法典,并且此后一直在以多种形式重新出现。它是这么一个信条,认为真正的艺术不能为普通人所理解。但那些普通人是谁呢?一整个社会结构都被反映在这样的信条里。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被视为艺术消费者。剩下的就只有中产阶级及其坏品味,这种坏品味也许在东墓园那些墓碑上达到高峰。对波希米亚来说,那个阶级已成为憎恨的对象,他们还将写作视为一种直接针对这个阶级的活动。如果奥斯卡·米沃什提到马拉美是唯美主义的推广者,他也大可提到福楼拜,因为对福楼拜来说,写作的核心正是那个誓要驳斥中产阶级的意志。但福楼拜是在驳斥中产阶级还是在驳斥生活,这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对福楼拜来说,普通人代表了一般的生活,它沉闷如潮虫的生存。自此,艺术与公众分离便成为一个既成事实。在二十世纪,各种流派和宣言可分成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赚钱花钱者,连同他们对工作的崇拜、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波希米亚,他们的宗教是艺术,他们的道德是否定另一阵营承认的所有价值。某些运动,例如美国的“花孩儿”,代表着波希米亚态度的奇迹般繁殖。在欧洲,自十九世纪中叶起,诗人就一直是外人,是反社会的个人,至多也不过是某个亚文化的成员。
这便造成“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和误解”的永久化。《关于诗歌的一些话》的作者,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不应被视为呼吁有社会承担的诗歌。不过,他却认为未来属于工人,并认为上层阶级的文化是颓废的。未来那位真正受神灵启示的诗人将超越他那微不足道的自我(用威廉·布莱克的话说,是他那“幽灵自我”),并且与那些精英诗人相反,他将表达那些现正获解放的被践踏的人民无意识的热望。他将穿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更富生机和更痛苦的劳动大众那最深刻的秘密”。让我进一步引用奥斯卡·米沃什:
因此,在约一百年间,文人在诗中或在韵文中表达自己的活动,一直是--实际上全部是在追求“纯诗”这一标志下进行的。这两个字流露出那些把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的人的某种有点儿幼稚的先入之见,需要更精确的定义。很不幸,这两个字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淘汰过程,才多多少少变得可辨。如果它们有任何意义,那就是指这样一种诗歌:它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从其领域内清除出去,甚至消灭所有其他艺术分支的方法和倾向可能对诗人产生的影响。因此“纯诗”将是一种自发性的诗歌,并且将是最深刻和最直接的诗歌。
在这段话里,矛头直指精英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他们为自己保留了欣赏“纯诗”的能力,同时把主题性的、多愁善感的和夸张的艺术让予市侩者。差不多同时,奥尔特加加塞特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和随笔家。写了他那篇着名的《艺术的非人性化》,修道院院长亨利·布雷蒙亨利·布雷蒙(1865-1933),又译白瑞蒙,法国文学批评家和天主教哲学家。则于一九二五年在法兰西学院的穹顶下,发表了他关于纯诗的演说,从而把纯诗正典化。
他宣称,纯诗包含各种声音的妙不可言的混合,如同神奇的咒文,而不管它们有什么意义。他引用拉辛的一行诗作为纯诗的例子:“弥诺斯和帕西法厄的女儿。”语出拉辛《费德尔》,乃是《费德尔》人物表中对费德尔的介绍。弥诺斯和帕西法厄是夫妻。帕西法厄与一头白公牛生下人首牛身怪物弥诺陶洛斯。纯诗与试图把绘画从“内容”和从模仿自然中解放出来的做法相似。各种艺术分支在这迈向纯粹性的奋斗中竞争,有时取得令人吃惊的效果。如果说音乐可较轻易地走这条路,而绘画则倾向于抽象的话,那么想象戏剧中的“纯动作”就较困难了。然而,纯动作在理论上也被介绍到戏剧里来了,而且也有某种程度的实践,实践者是两个同时创作却不知道彼此存在的怪人:一个是波兰人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1885-1939),波兰戏剧家、小说家和艺术家。,一个是法国人安托南·阿尔托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法国诗人和戏剧家。。
我的法国堂兄不是那种“把宗教、哲学、科学、政治从其领域内清除出去”的诗歌的支持者。毫无疑问,这种诗歌就是纯诗展开的方式,因为即使它使用来自人类心灵中非诗歌活动的概念和意象,它也是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过去的诗人是不“纯”的。就是说,他们没有给诗歌指定一片狭窄的领土,没有把宗教、哲学、科学和政治留给被假设不能分享精英入会仪式的普通人。再次,让我回到奥斯卡·米沃什的论文:在他看来,纯诗无法定义,其意思是某种纯抒情。因此,任何定义它的企图也许都应该放弃:
我们也许听说纯诗虽然表面上难以捉摸但实际上是存在的,因此只要拥有必要的能力就可发现它。我们接着应谦卑地问,那些有贵族精神的人在哪里找到它,以及在哪些作品中找到它;以他们精英的灵魂,他们显然不会像瑙克拉提斯或米利都的脚夫那样陶醉于荷马,像佛罗伦萨工人和威尼斯船夫那样陶醉于但丁,或像伦敦街头的阿拉伯人那样陶醉于莎士比亚。纯诗:它是不是尤利西斯与求婚者们的战斗,埃涅阿斯下冥府,《神曲》、《歌谣和祈祷》法国诗人维庸诗。
《仲夏夜之梦》、《贝伦尼斯》第五幕和《浮士德》结尾的天堂?它是不是《尤娜路姆》爱伦·坡诗。、《蓓蕾尼丝》拉辛剧名。、《牧神的午后》马拉美诗。?或,更直接些,它是不是我们时代的诗歌,那种找不到读者的诗歌,那种“未被承认”的诗歌,那种诸如我们,甚至不读彼此作品的我们无一例外都是的平庸者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