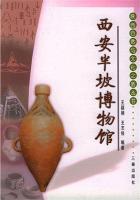可见在一定的条件下,“缺陷”会发生转化,变成了“美”。
这就不难看出,“美”和“丑”是相互依存、相生相化的。
其次,以丑衬美。丁玲深深懂得“丑就在美的身旁,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
(雨果:《<克伦威尔>序言》,《西方文论选》下卷1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l979年版。)如此看来,如果删掉了丑,也就删掉了美。但是描写丑,目的不是展览丑,作家应该作出审美判断与审美评价,应该用艺术手段塑造审美化的形象来加以表现。
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美丽地描绘一副面孔’和‘描绘一副美丽的面孔’是两件全然不同的事。”(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就是说,作家对于生活中存在的“丑类”自然不能把它们描绘成“一副美丽的面孔”,却可以“美丽地描绘一副面孔”,即以自己崇高的审美理想先否定它,再调动一切艺术手法,“美丽地描绘”它丑恶的本质,使之转化为具有自我否定价值的美学形象。
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杂货店老板,是个“丑”的形象,作者只是淡淡地通过他的一、二句话,就“美丽地描绘”了他丑恶的本质——浓厚的封建意识,缺乏正义感与同情心,低级趣味等等。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当“我”(小说中叙述者)到杂货铺买东西时,听说“我”住在刘二妈家里,他“便挤着那双小眼睛,有趣地低声地问我道:‘她那侄女你看见了么?只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他又转过脸去朝站在里边门口的他的老婆说:‘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
从杂货店的老板那双挤着的小眼睛里和“有趣地”低笑的问话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丑恶的形象,他对于自己的同胞贞贞遭受日本鬼子的糟蹋,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且又以淫邪的口吻,添油加醋地四处宣传,唯恐全村人不知道。他还将贞贞遭受的蹂躏视为“可耻”。其冷酷之心,实在令人发指!尤其是在他的意识里,贞贞不贞了,就应该死——自杀殉节,而不应该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就是“不要脸”……。杂货店老板是憎恨无辜的贞贞还是憎恨侵略者,不是明摆着的吗?显然,作者对他是批判的、否定的。杂货铺的老板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具有自我否定价值的审美形象,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反面人物的躯壳。
这样丁玲小说中的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丑的形象,便往往起到反衬美的作用,在美、丑对照中否定丑,肯定美。
如前所述,杂货店老板的形象正是用来反衬美的。霞村中不少的人同情贞贞,认为贞贞肉体虽然受日本鬼子践踏,却能够忍辱负重,给游击队送情报,她的心灵是美的。她们能够真正理解贞贞。比如贞贞从前的恋人夏大宝即使已知道贞贞“不干净”,仍然向她求婚,夏大宝是善良的,他的心灵也是美的。这些人对待贞贞的态度和杂货店老板形成了反差。没有杂货铺老板这个丑的形象的反衬,也就显现不了夏大宝以及村子里那些同情帮助贞贞的美的形象。这可以说是以丑衬美。
杂货店老板的形象也正是因为作为美的一种陪衬才具有美学价值。
这种美丑相映成趣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巴黎圣母院》中外丑内美的卡西摩多和道貌岸然而灵魂肮脏的副主教克洛德是个鲜明的对照;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的心地善良和她的情人弓箭队长法比斯的生性残忍轻浮也形成鲜明的映衬。
这种美丑的反差和对立在中国的古典文论中,论述也颇多,庄子、李渔、刘熙载等都有论述。
其四,追求“怪异”之美。
丁玲笔下的形象,被称为“怪人”。莎菲、阿毛、陆萍、贞贞,无一例外。
一方面,她们处于同社会流俗强烈的对抗中,不入时从俗,不入主调,我行我素。由于反抗的激烈和行为的乖戾,一直被周围的人视为“反常”、“怪诞”、“怪异”。而这种“怪诞”,也正是莎菲们美的特质之一。因为她们正是用“反常”来对抗世俗中的“常”规陋俗。
在阿Q看来,“不同就是异己,异己就是可笑,可疑,可恶”。陆萍所在的医院有些人也有这种奇怪的逻辑,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点阿Q相。陆萍建议改革医院,却“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他们认为“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认为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成为习惯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于是人们对这位“不平凡”的“怪人”嘁嘁喳喳,说她“爱出风头”。在她害病的时候,“医院里的流言却四处飞……有的说她和郑鹏在恋爱……害相思病,有的说组织不准她们恋爱,因为郑鹏是非党员,历史不明……。”这些猜测和诽谤与阿Q的心理定势多么相似。
另一方面,莎菲们之所以被认为“怪异”,还与她们“总是爱飞,总是不满于现状”这一特点有关。正是她们“爱飞”,不满于现状,想改变现状:所以她们的思想不但是“反常”的,而且是“超常”的。其实这正是莎菲们不同凡响之处,足以体现她们开放的姿态。
一个小小的阿毛(《阿毛姑娘》),居然也那么“怪”。她因一次进城,思想发生了变化。她羡慕城里的繁华、富
丽,倾慕城里女人的打扮穿着,她也想有漂亮的衣衫,舒适的生活。于是阿毛开始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拼命地养蚕,耐苦地劳作,并且还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幻想将来也会富起来。但是,小二却只是一个“安分的粗心的种田人”,他不理解阿毛隐秘着的心思,更不能满足阿毛摆脱贫困的欲望,于是阿毛失望了,变懒了,病倒了。在断定“幸福只在别人看去或羡慕或嫉妒,而自身始终也不能尝着这甘味的时候”,阿毛自杀了。这个小女子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确太新奇了。阿毛的家人,无法和她沟通。阿毛的想法超越了世俗的“安贫乐道”观念,超越了常规,超越了现实,甚至超越了时代。试想想,那个时代只要求阿毛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然而阿毛却要反这个常规,要依靠自己,帮助丈夫走致富的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的确令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说莎菲、阿毛、陆萍、贞贞等人的“怪异”也是一种美呢?我们可以先看看西方的“怪诞艺术”为什么倍受人们的欣赏吧。就拿绘画来说,盛行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怪诞绘画“巴洛克”风格,其本义就是不整齐、扭曲、怪诞。古典绘画的构图呈现三角形,体现单纯、均衡、稳定,可它却打破这种构图而采用“s”状。这种构图,运动感强,明暗对比强烈,使人眼花缭乱。再说“怪诞”雕塑家贝尼尼,他喜欢把建筑跟雕塑结合在一起,甚至打破它们中间的界限;又常常在雕刻中运用绘画的手法,从而创造出建筑、雕刻和绘画混合的“非驴非马”艺术,正是“怪诞”才大大地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力。
丁玲笔下的莎菲们的“怪诞”、“怪异”之所以也是一种美,就因为她们打破了世俗的“均衡”,打破了世俗的“中规中矩”搅动了现实生活这一潭死水,暴露了墨守传统的弊端。因此,莎菲们这些“不合常规”的思想、行为,才会美。
丁玲也像怪诞艺术家那样,塑造了这些“怪异”的人,作家通过她们,将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总体考察、审美评价,艺术化地、含蓄地表现出来。特别运用她那独特的慧眼将尚未被人们发现的、尚看不见的东西,超越前人的东西寓含于她的人物形象中,使人物形象超乎寻常地表现出一种美的特质来。
5—4“女性而非女子气”——丁玲的文体风格及其演变
作家的文体风格诚然要受到文化的制约。众所周知,“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他的文化属性,亦即他创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可通约性,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合理地解释语言现象;反过来,适用于语言学的东西,也适用文化分析。”(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第1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由此可见:“人是文化的动物”,人能创造和使用语言,这是人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而语言现象本身就是文化现象。因此作家创造的作品,其文体本身就必须充满着文化的意味。
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是能够“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指它符合事物的规律性;“自觉”,是指它能符合人类的目的性。.正因为如此,作家的文体风格及其演变,也必须与现实相联系,受作家的思想观念、个性气质、审美情趣制约。“篷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的丁玲,“蛮”、“倔”、“辣”的丁玲,喜欢“火辣辣”、“真情性”的丁玲,她的文体风格必然与此密切联系。
尼姆·韦尔斯认为丁玲“是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首先她是一个女性作家,有女性作家的敏感、细腻。她善于记录人物一阵阵心灵的悸动,一声声灵魂的叹息。人物丰富的心灵世界和情绪世界,往往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写得精确细腻。但丁玲又非“女子气”。司马长风认为“她直吐胸臆的风格,有男子气,长风破浪的豪放”。苏雪林认为:她描写场面魄力沉雄,语气淋漓酣畅,有男子汉的作风。
许多评论者认为:丁玲的小说创作又往往将分析和议论揉进叙述和描写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生、人的命运、人的价值的认识与评价;对理想的追求与憧憬,对社会痼疾的忧患;对生活哲理的思考……。这样,一便为她的作品增加了力度和深度,表现出一种理性色彩。
赵园在她的《艰难的选择》一书这样评论丁玲:
她把波澜迭起的人生带进她的人物世界,使她的人物在与环境的不断碰撞中备受折磨。也像一般的女性作者,她禁不住要参予她的人物的生活,但不是用抒情,而是用分析。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哪个女性作者,把如此浓重的‘理性色彩’带进作品的……她力求‘广大’——潜意识中未始没有对女性的‘传统世界’的否定,但她的力量却并不在于‘广大’,而在她的思考的尖锐性与重大性,在于她特有的理性,以及调和理性与感性的富于个性的方式。这种特点尤其因为作者是‘女性’而格外引人注目。(赵园:《艰难的选择》第17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的确如此,丁玲“引人注目”的原因在于她既有女性作家的细腻又有男性作家的粗犷雄浑;既有发人幽思的柔情,又有刚劲有力的笔锋;既具有女性作家以情感的具象的方式把握世界,同时也善于和男性作家一样作智者的理性思考,以抽象的方式把握世界。这样,丁玲的文体风格,便显示了刚柔相济的审美特质,从容朴厚的作风。但是,这种文体风格,有其形成和发展、成熟的过程。她在追随时代思潮的同时,对小说的表现方式和风格进行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
其一,早期创作的苦闷感伤、焦躁郁愤与精确细腻的文体风格。
一般来说,女性作家的创作一开始往往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以“表现自我”为目的,所以她们的创作往往
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丁玲早期的创作,也明显地有自叙传色彩。她的《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等三个集子中所描写的全是清一色的在黑暗社会的重压下,痛苦挣扎、彷徨苦闷、追求幻灭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一群莎菲式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处境和命运,与那时丁玲的处境和命运相似,有着丁玲的浓重身影。
“五四”以后,丁玲走南闯北,东奔西走,到处寻求出路,可是出路在哪里呢?她到处追寻理想,而理想又无影无踪。于是她感到孤独、寂寞,极端的苦闷。这位狂狷孤傲的女性,没有看清楚方向,她空有冲天的雄心,因而不得不抑郁、感伤、愤懑、反抗。就在这种情况下,她提起了笔,将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对封建传统的叛逆和反抗,对前途的迷惘和困惑,统统写进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并使小说笼罩着一层忧郁和感伤的气氛。
同时,由于创作主体那时的“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她把对社会的反抗和批判、把心中的郁愤和焦躁似沸腾的岩浆喷吐在她的小说中,因而,她的小说使人感到有一股似狂风暴雨般的冲击力,狂燥激越的情绪张力。与此同时,这种郁愤与焦躁的情思,又给作品带来了阴郁感伤的情调,给作品带来感伤的风格。
另一方面,她早期的小说,在描写人物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时,尤其显得细腻。丁玲熟悉女性的生活,她天资聪敏,善于捕捉生活的细微末节,人物心里掀起的波澜。如沈从文所言:她是“一个沉静的人,由于凝静看到百样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恶最细致部分,领会出人、事、哀、乐最微小部分”。
(沈从文:《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版。)她观察细微,描写细腻。她用剖白式语体与大胆的心理分析,以女性的善感细腻地去描写深受压抑而又善感的女性,揭示人物内心隐奥的一隅。
丁玲擅长捕捉人物心灵悸动或感情倾斜时一刹那的闪念,并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心理反应。阿毛只因为进了一次城,看到那繁华、热闹的城市,便使她迷醉,“由于这次旅行,把她在操作中毫无所用的心思:从单纯的孩提一变而为好思虑的少女了”。这次进城,使阿毛的心理来了个突变,她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新式男女的享乐,喜欢摩登女郎好看的衣服。她懂得这都是因为她们有钱,或者她们的丈夫、父亲有钱的缘故,钱把同样的人分成许多阶级,“本是一样的人,竟有人肯在街上拉着别人坐的车跑,而也竞有人肯让别人为自己流着汗来跑的。自然,他们不以为羞的,都是因为钱的缘故”。阿毛不信“命”了。假如自己不是嫁给种田的小二,也不至于被逛山的太太们所不睬。阿毛逛城所起的变化,她的“一刻突变”,给她后来的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要是她不进城,也许她只会眼光固守在这个家上,安分地和丈夫小二甜甜蜜蜜地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安贫乐道。但她终于要和命运抗争,要改变自己贫穷的处境,这种新的欲念促使阿毛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欲望挣钱而拼命干活而终于灰心,最终自杀。就这样,丁玲敏捷地捕捉了阿毛一次逛城心理变化的重要的一瞬,并浓墨重彩地发掘这一瞬在人物生活中的特殊意义,从而生动、细腻地将人物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心活动刻划出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人物感情的涟漪和心理的波澜漩涡。
这种细腻透视,得到许多评论家的赞誉,贺王波就称赞过,“丁玲女士的作品是具有特殊风格的。她善于分析女子的心理状态,并且来得精确而细腻……”。
其二,左联时期,由于语境的迁徒,创作的转型,丁玲小说的文体风格发生了变化,一扫早期苦闷感伤,焦躁郁愤而变为开朗、明快。
每一位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时代环境中,随着社会的变革,随着作家社会实践、生活环境和政治地位的改变,时代的文学潮流的发展,作家的艺术观及其文体风格也可能起某种变化。
三十年代初,丁玲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转型,她跳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生活的狭小天地,投入了工农大众的火热斗争生活,她的浪漫宣告了结束,她告别了莎菲们,也告别了苦闷和感伤,开始描写新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