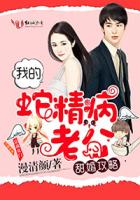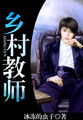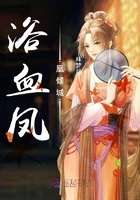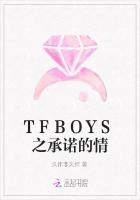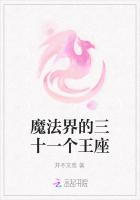先仔细分析一下到底有什么必要非使用杠杆。长期资本早期是做债券套利交易的,原理也并不难理解。政府债券背后的信用支撑一般都很稳定。相邻较近的不同期限债券的不合理定价在支付阶段会最终消失。通过配对交易,做多定价便宜的债券,做空定价昂贵的债券就可以从中获取并不算丰厚的套利空间。但这种套利空间太过于微小了,为了达到较好的收益水平,高杠杆头寸被应用在了交易过程中。后来长期资本也做了很多其他类型的交易,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长期资本竟然不顾投资者的抗议,“迫使其收回了27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极端吊诡的举动,或许长期资本还能蹒跚更久,但毕竟有那么一刻多余的本金让收益率显得并不够漂亮。此刻似乎对于分析杠杆问题已经足够明确了,追求绝对收益和力求放大利润水平是一切的动力源泉。
贪婪和恐惧是个人性问题,不是数量化手段能解决的。笔者特别爱跟一个老同事聊天,“资本是逐利的”是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话本质上来说没错,描述的其实也就是人的贪婪。可问题是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得到点什么就一定要失去一些进行交换。杠杆就是这条朴素的真理在投资领域最好的体现。
配对交易在逻辑上是基本正确的,长期资本动辄40%—50%的收益率就能体现这一点。但贪婪一旦缺少了恐惧来平衡就会变得十分危险。人在春风得意之时很少有自省的能力,而命运就是爱在这个时候给你惊喜。放大一个无风险的收益似乎无可厚非,可这里的前提一定是算法的制作人已经彻底的领悟了研究对象,保证不会有意外发生。只要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有几个人狂妄到敢打这样的保票?当然,自命不凡的人做出这样的举动要比普通人的概率更大。
摆正心态,不追求绝对收益有何不可?如果没有如此之高的杠杆,虽然成就不了长期资本的辉煌但也不至于落得这么个尴尬的下场。很多人会觉得,这帮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溢,一辈子早就捞足了。笔者也曾经这么认为过,但实际上这个观点并不全面。昔日风光无限的交易员不得不祈求银行不要逼他宣布破产,“以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还清自己所积欠的2 400万美元债务”。“其他大部分合伙人都至少损失了90%以上的财产,因为他们几乎都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投进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员工大都将奖金作为投资,又投进了公司,最后都落了个血本无归。这结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盆满钵溢”。当投资一旦带上了赌博的色彩,投资者的结局往往也会如同赌徒一样悲惨。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严格控制杠杆化程度,能不使用就不要尝试;(2)采用一些资金管理手段将盈利的一部分移出市场保存起来。尽管后者会使盈利的积累速度下降,但至少不会让投资者因“黑天鹅”的大驾光临而变得一无所有。
某种程度上,国内投资者是幸运的。因为没有那么多金融衍生品作为诱惑向投资者递出镶着金边的请帖。但时刻应该提醒自己的是,随着金融产品的多样化,由技术创新落后所带来的保护圈越来越小这个事实还是明确的。经常提醒自己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追求保值增值,我们付出努力去学投资方法或许还是值得的。如果只是为了披着投资的外衣赌博一下,可能还真不如去趟赌城来的愉快。
(第六节)数量化投资的注意事项——对抗已有观念
数量化方法也要研究员进行设计、编程与校验。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说“数量化方法彻底摆脱了人的因素”是不正确的表述。较为符合现实的评价应该是:“在已有策略执行层面,数量化可以对抗人为不稳定因素的干扰。”而一旦人的因素牵扯其中,就有了对抗已有观念的问题。
不可否认,量化投资是这几年才在市场中开始流行的概念。笔者也仅仅是在2006年左右才开始看到国内有投资者陆续在股票市场进行此类的尝试。这个境况并不意外,国内金融市场起步较晚,而且总是有很多半市场型的因素可以吸引投资者和媒体的注意力。再加上引入一个概念需要时间,所以量化投资自然而然也就排在了价值投资观念之后才有机会浮出水面实际上,操作意义有限但“红得发紫”的价值投资也一定程度的符合监管导向。在投资者教育这个问题上,投机气氛浓厚的历史问题最好的导引手段确实是格雷厄姆那一套。但过分片面的宣传一定会激起人的抵触情绪,笔者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的市场大跌给自以为是的投资者及时的泼了冷水应该是长远意义上的重要事件。
观念的形成必然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在设计算法阶段时刻提醒自己尽量不要带有偏见至关重要。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接触的数量化投资领域,基本面分析往往都是先入为主的观点。无论是“自上而下”亦或是“自下而上”,接受过金融训练的人都或多或少的会考虑经济因素、行业因素与公司因素。这没什么不妥,实际上增大信息集对于算法的训练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坏处。但接受的知识所能带来的优势也就停留在这个层面了。我们学了很多应该怎样的理念,但负责的教授往往也会加上一句“现实可能并非如此。”
“对或者错”在金融市场里面似乎从来都不是什么重点。因为在坚持看到自己的观点正确之前,可能就已经被资本市场消灭了。交易的天平在面对蛮力与智慧时,往往会倾向于前者。在这方面,长期资本又一次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实例。根据《创造金钱》一书的描述能够发现,至少在波动率这个问题上,长期资本的态度完全带有接近于偏执的观念。
1997年陆续开始退出长期指数期权市场的投资银行们“必须回购已被出售的波动率”。而长期资本则“向所有需要者提供珍贵的波动率……他们如此渴望交易,以致在伦敦的股票衍生物交易员中获得了一个绰号:波动率中央银行……当然,从长期资本的观点来看,这是无本之利。数据显示,欧洲市场的历史波动率接近15%。由于市场的预期波动率将是23%或25%,长期资本的收入十分优厚本段引用出自《创造金钱》,但由于这本书已经绝版了,为避免读者的麻烦,笔者极不情愿的抄了下来。实际上,笔者对于长期资本的了解也是通过书籍,毕竟对于笔者来说,1998年时的网络还只是用于跟高中同学打游戏的必备而存在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像长期资本这样的对冲基金公司,除了内部人士(往往又对自己的失败守口如瓶),恐怕大都也只能是通过读书的方式才能了解吧。”。从《拯救华尔街》一书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描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抛空股票期权的价格,是以市场价格每年的波动幅度为19%作为基准的。”
尽管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但遗憾的是长期资本也没有撑到能见证自己正确的那一天的到来就出现了危机。从这个层面来看,说其是赌博也并不为过。这实际上与赌桌上没有足够的金币情况一致。2000年11月西蒙斯在接受过记者的采访时被问及“长期资本管理是一家数量化交易型企业,正如复兴技术一样。你是否从它的坍塌中学到了什么?”西蒙斯的回答是:“公司中的每一个人都读了关于长期资本的书。通常意义上来说,它会让你谨慎。我们的方法是很不同的。我们不从模型开始,而是从数据开始。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寻找那些可以被千百次复制的事情。收敛交易的一个麻烦在于时间。你说事物终究会走到一起。好啊,终究是什么时候?”
西蒙斯的见解是一针见血的。投资是个时间敏感的概念。没有人会用一个说不出究竟是多久的时间段来验证一两个人观点的正确与否。当一个律师在荒郊野外踩到一个野蛮人的脚时,说“打人是不对的”恐怕也避免不了身体上的被摧残。或许只要律师还有口气在,跑回来跟其他人说“野蛮人打人不对,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其他人还是可以赞同倒霉律师的说法。但有什么意义呢?
要对市场有几分敬畏之心,无论知识背景丰厚到何种程度都要如此。因为人能分析的只有理性的那一部分,还很有可能分析不明白。市场表现出的非理性成分很有可能就让我们的报告或模型变得一无是处。长期资本的对冲是精致的,对某一特定金融产品的拆分往往涉及多个领域(至少在其豪赌价格波动幅度之前)。可过分的精致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倒金字塔也好、创新螺旋也好,一个部位的破损往往会招致大面积的垮塌。从这点上来看,为策略模型设计一个松散的结构并强调鲁棒性或许是条出路。
(第七节)数量化投资的注意事项——数据与模型
既然是基于数量化的分析手段,数据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最重要的输入。这里笔者想着重谈两个方面。
首先,《解读量化投资》一书中介绍说,西蒙斯使用“每笔交易数据库”(记录每一笔交易的价格变化,而不是每分钟的价格变化)。信息量损失越少,应该越有利于模型的开发。可对于股民来说,现实问题是这个数据库在国内还真是不好获取。至少,从大众普遍的意识中,上交所逐笔数据的获取应该是从2006年8月开始。此时,上交所Level—2行情数据的公布才有可能具备逐笔交易的信息,之前所显示的都是撮合数据。而深交所的Level—2行情数据也基本上能追溯到2009年。理论上讲,既然公布出来这样的数据,就可以获取。从数据量上来说,时间段有限可能对于算法的校验、训练会产生障碍。
其次,“T+1”的交易制度让快进快出型的股票日内交易受到一定的阻碍。虽然有一种非满仓滚动的操作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但毕竟还要受到操作次数和基数的限制。
在股票操作这个问题上,一种处理思路是更改以日内交易为目的的算法设计,用基于日线级别的数据来予以替代。尽管这往往意味着需要将算法的设计理念调整为类似于基金式的长期持有,但也仍不是必然选择。不过,还是有必要来重新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强调将算法交易仅仅只是瞄准在与基金业绩比较的层面就已经存在意义。
基金作为专家理财,实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承认基金经理可能在金融教育和市场经验上有超过普通投资者的现实很重要。很多问题应该换位思考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答案。很多投资人是自己做不好才把资产交给基金进行打理的。基金赚钱的时候觉得理所应当,赔钱的时候就有种“还不如我”的心态,这十分不可取。如果我们有方法可以打败基金,这实际上已经实属不易。只要方法有效、稳定且可以扩展,读者其实就已经掌握了价值不菲的技术。实际上,笔者在考虑算法设计的时候,也主要是以尝试打败指数或者打败基金为目的来建立算法应用的。至少,依照笔者所接受的金融教育和国内基金普遍比指数走的好的现实,这个并不“高远”的目的可以让我自己感到知足了。
正如笔者所指出的一样,投资这种事没什么绝对。据笔者了解,在期货市场有一种炒单现象。做得好的炒手甚至可以每天有稳定的盈利。这或许就是普通投资者操作的另一个出路。调整好两者比例,或许才是至关重要的。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股票市场的门槛还是相对较低的。而且,国内期货市场算法交易发展的进程要远高于股票市场,投资人往往也格外的老练。所以,在没有较好的准备之前,投资人还是不要轻易涉猎比较稳妥。
这里其实也涉及到了上一节的一个遗留问题。“不从模型开始,而是从数据开始”到底是什么意思?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含义:1.避免以定价模式来尝试推测变量的目标值;2.其极有可能是从数据挖掘的角度来尝试搜寻算法,并依托统计套利的模式进行策略执行。
这第一个方面容易理解,实际上笔者从本书的一开始就表达了对内在价值在应用层面的不认可。认为“金融工具存在内在价值且价格要向价值回归”这种观点更接近一种信仰。而信仰往往是不需要(也没办法)证明的。在金融市场里有信仰可不见得是个好事。长期资本的例子已经比较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方面可能略有些问题需要解释。套利已经在前文中有所涉及,但统计套利暂时还没有。
金融投资领域的统计套利实际上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方面。在学术领域统计套利是以针对确定性套利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统计套利是通过对资产价格的统计研究尝试寻找已有模式下的错误定价。而在对冲基金中,统计套利泛指短期均值回复策略。而这种策略是建立在大规模操作,短期持有,坚实的计算与交易的信息技术构架之上。
安德鲁·波尔在《统计套利》一书中指出:“统计套利的方法范围,从最古老的纯粹的匹配交易机制到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模型,应用的技术包括神经网络、小波分析、分形分析——几乎涵盖了统计学、物理学和数学上的所有的模式匹配技术,这些技术被测试、检验,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遭到摒弃。后期融合了多种因素,包括交易经验、更多的实证观察值、实验分析,并且从工程学和物理学的视角,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
作为一个行业词汇,想要精确的定义是有困难的。但不难看出,统计套利普遍涉及到了模式的探索、校验和大基数的应用。至于研究方法则没什么限制,只要是能数量化的领域就可以借鉴使用。换句话说,这种研究方法是在假设过去的盈利模式仍然适用于现在,不适用的策略算法就要被舍弃。显然,算法池式的管理结构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应对方法,这也是笔者之前强调松散结构的原因。
到此为止,似乎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长期资本管理这种倒金字塔式的策略结构可以应用到量化交易中。那种强调衍生品式的模式可以被一种相对扁平的结构所取代,而分析师则更像是一个维持优胜劣汰比例的阀门控制人,以及为种群添加新个体的造物主。
(第八节)数量化投资的注意事项——算法复杂度
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看上去极度精巧复杂的工艺品更招人喜欢了。迈克尔·贝的“变形金刚”有着如此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至少部分与其摒弃了(相比之下)孩之宝较为弱智的变形风格有关。创新螺旋某种程度上也似乎是如此。可问题也同样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复杂度和鲁棒性是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