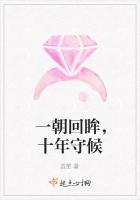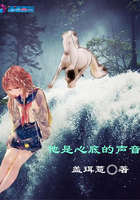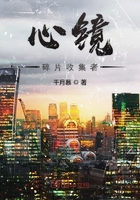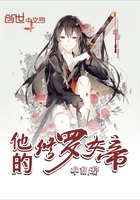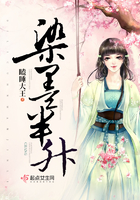“基金公司和基金产品表现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这是本节想要传达的第一个观点。事实上,读者只要愿意,在知名的基金公司中找到几个走势平平的基金产品并不难。慕名而去,发现想买的基金暂停申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估计都是问问销售人员“有什么现在可以购买的基金产品么?”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笔者也是如此,但这样做却往往是错误的(就此说其为“诱饵调包”有些过分,但还颇有几分相似)。基金市场有一个现象,表现好的基金往往都已经不再接受新的投资,基金公司通常会通过发新产品的方式来满足多余的认购需求,有一些是明星基金经理操作,有些却并不见得。但往往新基金的表现要逊色于老基金。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国内基金市场上找到例证。
关于如何选择基金,首先还是要明白三个问题:
(1)选择基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暗含着基金盈利模式可以持续的假设;(2)基金宣传的运作模式可以与持有人的预期有很大的偏离;(3)某些基金的耀眼业绩也可以是与一两次重大的择时决定直接相关。
如果细分析起来,接受这三个假设需要极大的勇气。
1.盈利模式可以持续的假设本质上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要指望基金经理能较好的保护好这些秘密。以“价值”和“成长”为卖点的基金很多,可却没有几个基金真的走出了价值领域和成长领域大师级的收益率。部分原因可以被“随着使用的人数增多,利润空间下降”来解释。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局面。名声越大的投资策略,收益率往往越普通。其实,这应该也不是一个陌生的现象。巴菲特曾经指出:“这些投资所承诺的利润是虚幻的。我们的竞争者,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都会陆续进行相同的投入……从个体上看每个公司的投资决策似乎是划算并且理性的,然而总体上看来,各个公司的决策相互抵消。”这个公司经营决策上的道理似乎也适合在投资领域。西格尔在《投资者的未来》中提到的“合成谬误”也适用于这个领域。
2.投资者预期与基金运行上的差异是个难以避免的棘手问题。比如曾经在市场流传过一篇“争议基金经理:××量化核心×××”的文章就是一个奇怪的案例。首先,暂且把文章有导向性的言论放在一边,我们看看该基金经理究竟做得如何。公开资料显示,该基金经理2007年6月26日任职,2011年4月26日离职。简要的评述一下其业绩,2007年其接手前该基金就跑输市场,2008年末基本与市场走平,随后一段时间虽一直没有打败沪深300,但差距也并不明显。直到2010年下半年起,基本和市场走平直至离任。客观的讲该基金经理还是对此产品有一定贡献的。正如笔者前文讲到的,很多基金经理打败沪深300也是靠2008年的仓位调整才有的业绩,其余时间也只是能做到跟随市场。仔细看看该基金的属性,投资者一定会发现这样一句话:“本基金在正常市场情况下不作主动资产配置,股票资产的基准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90%,浮动范围为85%—95%;现金的基准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10%,浮动范围为5%—15%。”这表明产品设计上其实就很类似于指数跟踪,并没有给基金经理过多的空间以发挥。至于文章所谈的不调研显然也没什么不可以,调研过的人肯定对调研的作用有自己的评价,笔者也有自己的态度不必多谈,但要求量化基金一定要调研显然有点奇怪。
如果只是为了平反,那真的不用介绍这个事例。这个世界每天冤枉人的事都在发生,也说不过来。但笔者发觉了该量化基金经理的一些言论不符合量化分析的思路却与本小节的主旨极为吻合。虽然数量化投资是后面几个章节才会开始考虑的问题,但显然这里就有必要先说一句。笔者就根本不认为数量化投资也一定要来搞估值这里的概念暂时不宜过度扩展。毕竟,很多(衍生品)定价问题都是通过数量化手段完成的。不过,A股投资者暂时接触不到。所以,不严格地说,这个表述问题不是很大。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笔者认为估值这么不可靠的东西就不应该作为数量化的一种思路。有一种说法认为:“定量投资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对基本面的深刻理解和细致分析上的,其本质就是定性思想的理性应用。”笔者是万万不敢苟同。数量化的优势往往在于其模式确定后的执行纪律与模式迁移识别。把定性的、根基模糊的东西加进去简直是逻辑错乱。作为数量化基金,不调研无可厚非。但其思路绝对是有诸多奇怪的闪光点,而就是这些闪光点与数量化投资一路走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完全相违背。真是应了“求人不如求己”的老话,很多事情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动手。
3.正如上一节指出的一样,2008年的大幅下跌让部分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基金逃过一劫,仓位调整使得基金受损幅度有所减弱。而后,很多基金的走势虽然平平,但由于这仓位调整的底子打得好,谈起收益率水平仍然可以有卖点。巴菲特也确实表达过,“人一生只要做对几件事情就可以了”。但我们显然更喜欢能经常做对事情的人,尽管我们也要面临基金从今开始有可能做错的风险。
笔者写作本节时,依照wind数据库的分类,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共有546只。从2007年11月开始,存在市场数据的基金数为235只,截至2011年5月23日,92.34%的基金都打败了市场。按照2008年11月初仍然存在市场数据的基金数上升至281只。此时间段内打败市场指数的基金有91只,打败市场的比例下降到32.38%。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之间,几乎所有的基金都打败了市场。2007到2008年的极端下跌行情,基金可以通过仓位控制的方式进行降低持股比例的操作,由于此次下跌行情持续时间过久,即便时间过去半年才发觉市场时机不对进行仓位调整仍然可以有打败市场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了长时间下跌行情中绝大部分基金打败市场的现象,可一旦市场开始回暖,打败市场的基金比例就骤然下降至三分之一,这在侧面说明了持续打败市场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下跌阶段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仓位调整的方式进行市场风险的规避,但上涨阶段却没有太多的选择。数据段移到2005年7月到2007年10月,有效数据量下降到96,打败市场的基金只有7只,占比7.29%。数据段移到2006年7月到2007年10月,有效数据量上升到137,打败市场的基金只有1只(还是只ETF)。尽管这种时段的划分近乎于苛刻,但说明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在极端的上涨阶段,基金也很难打败市场,原因包括择时、择股等多个方面。很难相信2007—2008年这种过山车式的走法说明了市场的有效,基金经理的决策也很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极端下跌阶段,基金经理却可以通过仓位控制打败市场实际上,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公布的报告中发现股票所占基金净值比得出一个大概判断。而基于更高时间频率的仓位估计是之后才会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一旦进入正常市场走势时间段,能打败市场的基金经理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还是存在的。细分起来,基金经理的价值至少在市场择时判断上得到了体现。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公正的结论。
如果读者经过仔细分析过后认为,基金行业值得信赖,笔者可以粗略的给出三条建议,让适合购买基金的读者自己进行筛选:(1)过去几年收益率居前;(2)基金操盘人员稳定;(3)最好能与基金有关人员经常聊聊。
前两项是基于公开信息就可以获得的选择范围,稍微有点数据处理能力的读者都可以自己做到。实际上,上文所述的内容就可以作为一种简单易用的筛选方式。当然,需要在打败市场的指标条件上予以放松。然后将基金进行汇总,查看收益率稳定居前且表现出较好的择时择股能力的基金,并翻看基金的有关介绍,确定基金经理的稳定性。市场上很多数据库都可以帮助你很轻松的实现这一切。当然也可以用数据库本身提供的一些指标做其他的分析,包括回归模型判断择时、择股能力等。这些工作对于爱探索的读者来说并不困难,而且数据处理过程并不复杂。笔者不想用一个“不专业”的眼光剥夺读者更多的快乐或咨询“专业”人士的机会,但一个方面还是要注意的:就笔者的经验看,单一指标的单一数值描述意义很小,单一指标的时序数据的分析意义更为重要。尤其是当市场情况出现变化的时候,用于描述市场某一属性的指标可能会产生波动。而通过时间段的选取可以抹掉差异性的做法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个综合的评价,意义并不十分明确。尽管这往往意味着需要增加一些自定义的算法判断状态,但笔者暂时尚未发现更有效的简便方法。
笔者其实想强调的是第3点实施的重要性。笔者曾在2007年招商银行组织的一次客户服务中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就是基金销售人员与银行网点的一次联合活动,对存在购买潜力的客户进行产品宣传。了然无趣的介绍很快就过去了,无非就是一些老故事,劝大家长期投资,共同见证复利的力量云云。提问阶段,一个客户问道:“贵公司的×××基金如何防范系统风险。”笔者顿时很感兴趣,因为已经四千多点了,笔者觉得有些高过了头。仓位和资产调配上要是降低对股票市场资产的调配还是可以的。关键是基金方面是否认为该到了这么做的时候,于是能得到基金方面的意见当然还是不错的选择。但该基金人员竟然一边思索着一边回答:“我们公司的交易系统很强,不会出现什么运行风险。”笔者当时就下定决心,就这水平,要笔者买贵公司的产品那是一万个不可能。今天回过头来细想,销售人员和操盘人员毕竟不是一回事。而且当时笔者的内心也已经有了倾向,很难保证会客观公正的听取其意见,所以无论得到什么回答可能内心都会只愿接受相同的判断,而一旦面对不同意见就产生抵触情绪。不过,如此答非所问的不专业还是在笔者内心留下了阴影。只要还有选择,笔者是轻易不会与该基金公司打交道了。
(第三节)基金配置的粗略规则
为什么是粗略规则?答案超乎想象的简单。因为根本没有通用的精细规则。特许金融分析师的3级考试很大篇幅是用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但相信也没几个脑袋正常的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在那么几个粗糙变量上。“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道理至少在这个领域还能应用。
再回到基本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基金作为家庭理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忽视。毕竟对还有其他重要工作的个人投资者来说,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投资上并不划算。一般情况下,将50%左右的资产配置于基金是可以接受的选择。投资者进行基金投资一定要摆正心态,不要本着快速致富的幻想,不要苛求基金能给你带来太多打败市场的惊喜。时刻考虑一个问题:“投资者自己操作能不能做得更好?”如果答案是可以,那就自己去投资。如果不行就不要如同积攒了无数怨念的恶妇一样喋喋不休,毕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人强迫你非要购买某一不靠谱的理财产品。
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规则是参考投资者个人的现金流需求。如果读者的现金流需求较为复杂又不喜欢自己动手,不妨去各大银行网点的理财规划师那里咨询一下,让他帮你设定一个较为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如果投资者能承担一定风险,并且只是为了让个人资产有个比银行定期存款更好的去处,那这么做或许也没什么不可以。
索林的“世界上最聪明”办法的核心是在国内股票资产、国际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三者间进行权衡。虽然笔者受到的金融教育一直都强调要分散风险,很多时候教科书也是推荐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但可能是受到“价值投资”的影响,对于那些远在异国他乡的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究竟能了解到什么程度真是心存顾虑。更何况全球配置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散风险,单纯的按照收益来衡量是逻辑错乱的一种处理方法,这也让追求收益的投资者多了几分徘徊于门外的理由。而且一旦采取全球精选的策略,那基准的参考意义其实就更小了。一旦如此,投资者连最后的可以用来衡量业绩的工具也要大打折扣,所以笔者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应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如果想体验一下全球配置的经典教科书做法,那就依照个人喜好买一点QDII。一点不配置也未尝不可,至少笔者看不出违背了什么重要的投资准则。当我们二分的看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时,问题只是如何调配比例。一个简单的规则是年轻不需要稳定现金流收入的时候股票型资产权重较高,年老需要稳定现金流收入时债券型资产权重较高。具体比例因人而异,如果生活殷实,甚至可以在配置问题上体现自己对股票市场未来走势的看法。但是读者一定要知道一点,“资产分配能对任意一个资产组合期望收益的90%或者更高比例作出解释。”所以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风险自担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