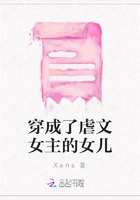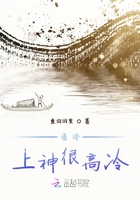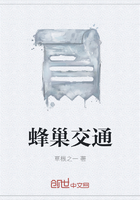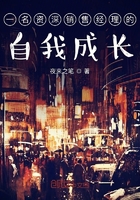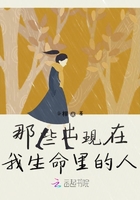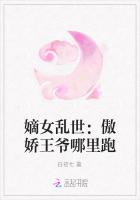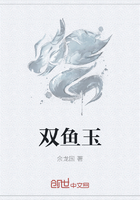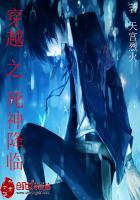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聂鲁达
“中国的忧伤”:黄河周期性泛滥
大约10000年前,农业革命导致中国史前人口爆炸后,中国的总人口在1000万。根据学者王建华(2011年)推断,龙山晚期河南为209.4万、陕西为275.5万、山东为161.4万,所以龙山晚期河南、陕西两地总人口竟然多达500万左右。巨大的人口压力,必须开荒,砍伐森林,以便提供住处和获得耕地。《孟子·滕文公上》中生动地记述了3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开疆拓土的场景,“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农业生产必须有水,“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可以推断被焚毁的“山泽”一定是黄河岸边的森林。
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松软肥沃土地的耕种面积不断扩大也导致了对土壤的严重侵蚀,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的植被开始遭到破坏,河边的森林开始后退。结果,致使黄河对泥沙的冲刷更为厉害,并形成一种周期性的危害。特别是,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区土质松散,垂直节理发育,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挟沙水流进入黄河下游的宽浅河道流速减慢,挟沙能力下降、造成河道严重淤积。根据估算,平均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高达16亿吨,其中4亿吨淤积在黄河下游。唐代刘禹锡《浪淘沙》感叹,“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大量泥沙淤积使下游河床日高,河道滩面一般高出地面,成为举世闻名的悬河。
“屋漏偏逢连夜雨”。受到亚洲季风的影响,中国的降雨量集中在夏天,暴雨多集中于中游,下游又没有湖泊调蓄,因此洪水有暴涨猛落的特点。黄河容易泛滥成灾。一旦地上悬河决口以后,居高临下,难以立即堵复,有时就酿成改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河道极不稳定。据历史记载,在1946年前的三至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河道因泛滥大改道共26次。与黄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就其水量与流域面积而言,都比黄河大得多,但沿河两岸平坦,河道宽阔,水面平缓,沿河形成宽数十公里的冲积平原。
如果说炎黄时代黄河泛滥主要是天灾,舜时代的黄河决口主要是人祸。国际历史学家们给黄河泛滥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中国的忧伤”(China’s Sorrow)。人口增长导致黄河河岸植被破坏。随着黄河缓慢地流经下游冲积平原,越来越多的泥沙便沉淀下来,造成河床抬升,黄河越来越频繁地决口泛滥,有时人们还没来得及修建起新的大堤,它又再次决口,淹没广袤的土地,开始了新一轮的轮回周期。
黄河决口后,部分难民沿着陕晋峡谷方向很可能向“关中平原”逃难,导致关中平原人口更多。人口压力导致更多的砍伐森林。黄河中游有人为破坏外,又加上气候干燥等不利的自然因素,更使不少地区变成了荒山、荒坡和沙丘,于是呈现“马太效应”,即越发水越砍伐,越砍伐越发水。先秦的文献中找不到“黄河”一词,成书于汉武帝征和年间的《史记》全篇也不见“黄河”的说法。据考证,“黄河”一词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常山郡·元氏县”的释文里。
不幸中万幸:永不干枯的河流
人类对于自然的冲击始于森林砍伐,以便提供住处和获得耕地。随着人口的增长,更多的森林被清除,无可避免地造成土壤侵蚀。戴蒙德2005年流行全球的作品《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复活节岛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以残缺的巨大石像知名——12吨重的巨石放在几十吨重、数十英尺高的石像头上,显然是某种人类文明的遗存,而现在,这个岛已经成为不毛之地,连一棵大树都没有。根据岛上沉积物中的花粉和坚果化石证据,科学家推测:很久以前,岛上曾有巨大的棕榈树。这些棕榈树曾与岛上的其他植物一起,共同组起了一片繁郁茂密的森林。后来为了彰显部落的权威,部落首领砍伐森林,运输巨石,建造石像。森林越来越少,水土流失就开始严重,而复活节岛的独特气候更加重了这种影响,最后饥荒发生,社会最终崩溃。
有趣的是,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对中亚文明因环境脆弱消失做了生动描述,可以与复活节岛对比。我长篇引述如下:“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新月沃地由于当地集中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拥有了领先优势。如果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优势,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可言。这种领先优势在一些强大帝国西移的过程中消失了,这种情况可以详细地描绘出来。在公元前第4千纪(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国家兴起后,权力中心起初仍然在新月沃地,轮流为巴比伦、赫梯、亚述和波斯这些帝国占据。随着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于公元前4世纪末征服从希腊向东直到印度的所有先进的社会,权力终于第一次无可挽回地西移。随着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希腊,权力又进一步西移,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权力最后又向欧洲西部和北部转移。”
只要把现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对它的描写加以比较,促使权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新月沃地”和“粮食生产世界领先”这些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受到严重侵蚀或盐碱地的土地。这个地区的某些国家的短暂财富是建立在单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现象掩盖了这个地区的长期贫困和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
然而,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都覆盖着森林。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变成受到侵蚀的低矮丛林地或沙漠的过程,已经得到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明。它的林地或者被开垦以发展农业,或者被砍伐以获得建筑用的木材,或者被当做木柴烧掉,或者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雨量少因而初级生产力(与雨量成正比)也低。这样,植被的再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是这样。由于没有了树木和草皮,土壤侵蚀发生了,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环境里的灌溉农业导致了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直继续到现代。例如,现今约旦的古代纳巴泰国首都皮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希贾兹铁路时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入7000年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
实际上,中国农业革命后对“美丽中国”的破坏不比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轻多少,也是生态严重破坏。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没有注意到中国地理环境与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河流的海拔。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的河流海拔低,容易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而中国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海拔在4000米以上喜马拉雅山脉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气候异常很难影响到河流存在。李白在《将进酒》中描绘了黄河沿着中国地势流淌的气势,“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巨型孤岛是东低西高,黄河长江发源地在青藏高原,必然会滚滚向东流入大海。
受到亚洲季风的影响,中国的降雨量集中在夏天,黄河长江容易泛滥成灾,特别是黄河。按美国学者罗兹·莫菲的《亚洲史》,则有所谓季风亚洲的概念,该地区与亚洲其他部分之间多有高山阻隔。夏季,远离海洋的亚欧大陆中央区会迅速升温形成热空气团,热空气上升,周围海洋饱含水蒸气的较冷空气涌入,到达陆地上空,特别是遇到丘陵或高山时,被迫上升的湿气团迅速冷却、凝结形成降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