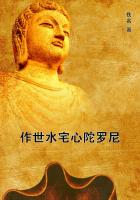即使一个再要强的女人,在渴望金钱时,也会变得亳无尊严可言,比如我。
低头看着一身暴露的黑色紧身短裙,镜子的自己妖艳而陌生,今夜,我将出卖自己的身体跟灵魂,即便是为了妈妈的医药费,也掩不住从心底范起的自我厌恶。不知幸或是不幸,在这家全台北最大的夜总会的工作,一夜的出场费顶我两份兼职的工资外带奖金,更不用说推销酒水所带的提成跟客人给的小费。
微微苦笑,我收起自哀自怜,转身走出换衣间,进入大厅那刻,满上挂起媚人的笑容。
大堂经理是个又矮又胖的秃头,脖子上带条金链子,纹身从脖子一直到脚腕,见我走进大厅,笑开来,露出好几颗金牙,满意的连点头。
“伟哥。”我轻声叫着,声音嗲到骨子里。
“不错不错,个头儿是小了点,不过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都小。”肥手在我腿上拍了一下。
笑容未变,心底却恨不能把这肥爪子给剁下来。
“叫曼儿是吧?你跟着小丽还有阿娴去六号包箱,今天来的可是日本有名的大人物,我想你应该对那客人的口。”
我点点头,跟着先前见过得两个小姐走进六号包箱,进门,看见一个腰肥腿短的五十来岁留着日本人特有小胡子的男人正抱着个小姐喝酒,见又有三个女人进来,兴致高昂的叫起来,“来来来,都过来坐,你你你,对,就是你,穿黑衣服的小娃娃。”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我媚笑着走近他,纤纤指搭上他的肩,人也顺势坐进他怀里,今晚的目地很简单,就是跟这个大人物出场,然后拿一笔出场费为妈妈交纳明天的医药费。
“小妖精!”日本人的肥手又溜上我的大腿,顺着我光滑的腿摸下去,另一只手忙着把酒把往我唇边送,其它几个小姐围上来,左右开弓,逗得日本人大笑连连,拿出钞票开始分。
很不耻地接过钱,有谁知自己的心在流血?
“你叫什么?”日本人问,酒气喷得人作呕。
“我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