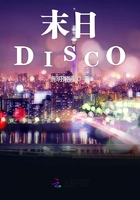诺木像一尊石雕一样呆立在船尾,眼皮上翻,手足颤抖,神情露出极度的恐慌,仿佛一瞬间被魔鬼摄去了魂魄。手中的单桨已经掉进了水里,他却浑然不觉。
容光斗和韩奇对视了一眼,都大惑不解。容光斗以为他中邪了,想走过去拍他一下,诺木却一头扎入了海水,没命地向着岸上游去。韩奇操起船桨,一边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划水追赶。晨风很大,吹得独木舟几度打横,等两人登上了岸,却发现诺木已经钻到一片林子去了。
等两人找到他时,发现他半卧半跪地瘫软在草地上,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容光斗小心地接近了他,过了片刻,起身向韩奇摆了摆手,表示不碍事。
三人很快就离开了苔藓岛。唯一的不同是,来的时候划船的人是诺木,现在变成了韩奇和容光斗轮流操桨。当天晚上,草草地吃了点食物后,容光斗和韩奇一左一右夹坐在诺木身边,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了这个样子。
“神灵的预言,神灵的预言……”诺木像个留声机一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在篝火的映照下,他原本矮壮的身体已经瑟缩成了一个圆球。
容光斗开口了,两人用马来语交谈了起来。韩奇听得不大明白,不过看容光斗脸色的变化,就知道事态非同寻常。夜深了,诺木已经躺到草铺上去了,容光斗还坐在火堆边发怔。
“诺木说,根据祖先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说法,那个翡翠岛是个鬼岛。平常谁也看不见,可一旦现形就会有大难降临。明天一早,我们要一起去极乐岛。诺木说那里有一个神庙,他要把这件事报告给庙中的长老。如果运气好,长老开了恩,还能做一场消灾祈福的法事呢!”
可想而知,这一晚三个人都没有睡好。不知怎么回事,韩奇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自己又坐在了堪察加半岛的火山灰中,而容光斗却不知去向,这真不是个好兆头。
天一亮,三人又上路了。一路上,容光斗继续和诺木交谈,韩奇知道他想打探有关神庙的详细情况。三天之后,极乐岛就遥遥在望了。还没到码头,就望见了椰林掩映中的那个神庙。让人称奇的是,它不但是全岛最高的建筑,竟然还是用巨大的石头垒起来的,这在珊瑚礁岛群中可谓罕见。
在神庙的大厅里,诺木匍匐在一个头戴草冠腰束布裙的巫师前,讲了一大堆话。巫师一言不发地听着,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不一会儿,陆续进来了几位老人。看模样,他们应该就是诺木所说的长老了。众人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同样也是一言不发。不过,他们严厉的目光却不时扫过容韩二人身上。
诺木终于讲完了,他爬起来就呆呆立在一旁。长老们打破了沉默,开始用土语进行交谈。他们一开始似乎有分歧,但最终达成了一致。于是,诺木被带到了神庙后面一个并不显眼的屋子前。不过,它的门前却有四个手执长矛头戴羽冠的卫兵。显然,这是重要人物的居所或宗教圣物的供奉之处。
诺木手指着两个中国人,对着长老们说个不停。韩奇明白他在请求让两人也进去,但遭到了断然拒绝。这时,容光斗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双脚合拢,脊梁绷紧,躯干前倾,双手合拢,十指相对,做出了一个似圆非圆、似尖非尖的形状,还上下摇动不已。
长老们的眼睛顿时瞪大了,他们没说什么话,连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可是韩奇却感觉到,原来弥漫着的敌意突然间消散了。
韩奇还没弄清楚导师为何要学天桥杂耍艺人玩了一手“仙猴献桃”,就被容光斗拉入了一片黑暗中。等目光逐渐适应环境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狭长的屋子中,四壁一扇窗户也没有。墙壁上挂着几盏鬼火般的油灯,灯芯是用草捻,灯油是鱼油,不但发出的光很弱,还有一股呛人的味道。
屋子尽头放着一张石桌,圣物就被供奉在上面。一刹那,韩奇和容光斗同时停止了呼吸。
它竟然是一件四足方鼎!
两人跟在诺木的身后,默默走向它,然后弯下腰身,轮流伸手去抚摩。就在触手的瞬间,韩奇真想掐一下胳膊,以确定自己从前晚的那个恶梦中清醒了过来。
在仅有的几秒钟里,两人瞪大眼睛,尽可能把方鼎的每一个细部都刻进自己的脑子。它有中国北方人家烧火的炉子大小,表面已经结了一层又一层的绿锈,显然年代久远,但饕餮俨然,云纹古朴。韩奇的手指顺着熟悉的回字形花纹盘旋而下,停留在了一个地方,即使闭上眼睛——不,即使刺瞎了眼睛,他也知道那是一只玄鸟的造型!
手指继续向下,韩奇的心突然不跳了,因为他清楚地摸到了两个汉字:天王!
很快,三个招灾惹祸的扫帚星垂首走出了神庙。厚重的大门在身后轰然关闭,谁也不知道下次开启会是什么时候。回到住处后,诺木依然忧心忡忡,但似乎已经不那么恐慌了。看来,宗教即使不是精神鸦片,也能起到镇静剂的作用。容光斗看上去也很平静,唯有韩奇激动得像一个被抽打的陀螺,一刻也停不下来,仅仅因为有外人在场,他才能勉强闭上了自己的嘴巴,却忘记了诺木根本就听不懂汉语。
等屋子里只剩下师徒二人时,满腹话语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滔滔奔涌。容光斗和韩奇的看法完全一致:这绝对是一件中国古鼎!而且,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这是一件商朝王室专用的宫廷宝鼎!“玄鸟生商,受命于天”。铸有这个神圣徽号的器物,只有地位显赫的王室成员才可以享用,臣子是万万不敢僭越的。而按照古籍中的记载,商朝大军出外征战时,军队的最高统帅十之八九就是世子!
现在的问题是:它怎么会在这里?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四处打听这尊鼎的来历,结果却让人失望透顶。所有人的说法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件鼎自古以来就供奉在庙里,是天神用来镇压翡翠岛上妖魔的法器。
但这并没有浇灭韩奇心头的激情,一想起这个荒远的太平洋岛屿上竟然供有中国商朝青铜鼎这一事实,就不由得浑身发烫。他的头脑中浮现出千奇百怪的念头,但仔细推敲,没有一条合乎逻辑。与之相比,容光斗就完全不同了,他似乎并不怎么兴奋,甚至有点怅然失落,时常一个坐在那里呆呆出神,也不知在想什么。
当然,韩奇并没有忘记请教导师,他究竟是怎么打动长老们的。容光斗告诉他,在远古时代,太阳是自然界唯一的能量之源。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火就取得了与之对等的地位。世界各地原生的神,或多或少都与之有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距今四千年前,在亚欧非三大洲广泛流传着救世主——光明之神弥赛亚——中国人称之为弥勒佛的传说,犹太教、基督教、祆教和佛教的起源无不受之影响。时至今日,崇火的仪式还残留在南方的傩舞和北方草原的萨满教仪式中。
“我想碰碰运气,就摆了一个火焰的形状,没想到竟成功了。显然长老们也认为:一个信奉光明的人,一定是个好人。”
容光斗说完,想想自己那副滑稽样子,也忍不住好笑。韩奇却又一次哑口无言了,看来,与导师相比,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还真不少。
既然天王鼎和翡翠岛之间存在着神秘联系,要想揭开它的底细,就必须亲自到翡翠岛上走一趟。但多风的春季到来了,海面上风急云低,浪涛汹涌,当地人的小舟根本出不了海。更糟的是,韩奇在中美洲染上的疟疾又发作了,身体寒热交战,呓语连连。极乐岛上别说奎宁了,连一盒风油精也没有。容光斗心急如焚,一俟天气好转,就用小船将韩奇送到了群岛的首府凤凰岛,那是唯一能与外界通航的港口。
在太平洋战争中,凤凰岛附近爆发了一场惨烈的登陆战,之后又成了美军的后勤中转站,各类军品堆积如山。现在,码头上依然一片繁忙,美国人正忙着将剩余物资运往中国打内战。没费几句口舌,容光斗就轻松地拿到了特效药,还为韩奇预订了一个回国的舱位,而他自己却坚持留了下来。
“你还没有结婚。”面对韩奇有气无力的反对,容光斗一句话就把他压下去了,“献身学术固然崇高,但人伦亦不可废。何况,万一我此去有什么不测,儿子以后就全靠你了。”
韩奇看着导师清隽的面容,眼泪快要下来了。可还没来得及表决心,容光斗又给他提出了一个简直让人无法容忍的要求:今生今世,不可撰写任何与商朝军团有关的论文。
“老师这个忠告,看上去很不近人情,甚至断了你的学术前程。但是,人情反复,世事难料。说到底,我还是怕你吃亏啊!”
韩奇艰难地点了一下头,心头酸涩过后,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涌了上来:即使自己体健如牛,双亲不在,妻出子壮,像和尚一样无牵无系,容光斗也会硬找出一个理由打发自己滚回去。
显然,导师的奇怪变化就发生在看到宝鼎之后。他究竟想到了什么?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情同手足的弟子?那个虚幻如蓬莱的翡翠岛,难道真的是个鬼岛吗?容光斗急于和韩奇分手,仅仅是出于爱护他,不愿意两人都身蹈险地吗?韩奇不敢再想下去了,换一个人,甚至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容光斗为什么要自行割断与文明世界的最后一丝联系,隐身在这个大荒之外的蕞尔小岛?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病体奄奄的韩奇和杀气腾腾的重炮坦克一起被送上了登陆舰的甲板。从那儿向下望去,在夕阳的残照中,容光斗颀长的影子拖在沙滩上,像一棵为果实所累的椰子树,又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问号。韩奇就这样一直望着他,泪水簌簌而落。可是一直等到船开了,容光斗却始终背向轮船,背向故国的方向,仿佛已经预感到了:这就是师徒之间的永别!
一甲子之后,紫禁城又迎来了一个黄昏。
西单繁华的步行街上人潮初起,卢筝从商场侧门的货运电梯中走了出来,马上就眯起了双眼。在阴暗的地下监控室待了一天,傍晚的阳光依然有点晃眼,但真正让人目眩的,却是前面报亭旁一个瞧着他笑个不停的姑娘。
“又被我逮着了吧?看你还能逃到哪里去!”话音未落,她就一下子跳到了卢筝的面前,鼻尖几乎碰到了他的下巴,唬得卢筝慌忙一闪,像只被小鸟追杀的螳螂。
“小妹妹,我已经说了一百遍了:这里是商场,不是商朝的古战场;而我呢,只是一个小小的中控技术员,两天三班倒,喂饱自己这张嘴还不易,哪有工夫管你爷爷的闲事?再说了,也不是我昧心咒老人家,以他的高寿,就算活成了人精,接回来端屎端尿伺候着,也是个有天没日头的累赘事,干吗非要给自己弄个祖宗供着?”
卢筝觉得这番话已经够入情入理了,可是,不晓得对方的耳朵失聪还是智商太低,竟然不能体察他的苦衷和好意。
“我没有弄错,我要找的人就是你。”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瞳仁黑亮,睫毛浓密,像个玩具娃娃,或者望着心爱玩具的娃娃。
卢筝最吃不消这种装天真扮可爱的眼神了。他皱眉撇嘴,却又无可奈何。这个名叫容妤的女孩子已经纠缠了他半个多月,不管说好话还是瞪眼睛,人家就是油盐不进。连同事小王都怪卢筝不懂得怜香惜玉,要是换了他,凭那丫头一个眼风,连人带魂儿都被勾走了,别说去那个叫什么“波利尼西亚”的小国,就是天天吃玻璃渣子也愿意!
不过,今天的卢筝有备而来,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借口,足以斩断天下一切货真价实或子虚乌有的情丝。
“我马上要结婚了。”这句话里包含着三层意思:其一,我即将入洞房,没时间和你斗嘴玩虚的;其二,连江湖上的朋友们都知道“坏人好事,犹如杀人父母”,你再逼我,难保我不会狗急跳墙;其三,如果你总是这样粘人,我一个破落户倒也无所谓,你清清白白的姑娘家,难道就不怕旁人嚼舌头?
“真的吗?——别哄人了!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敢见人,整天缩在这个老鼠洞里了!”容妤似乎不怎么相信。果然,她看到卢筝的脸色变了变,于是又重重地加上了一句:“既然我已经看上了——盯上你了,你想跑也跑不了!”
撂下了这句话,她就轻袅袅地走了。卢筝待在原地,望着容妤背影消失,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半晌,才想起来自己出来匆忙,将皮包落在了监控室,那里面装着一大沓订金。他今晚和顾雅莉约好了,一起去看婚宴的举办场地。——千真万确,卢筝现在的身份是个准新郎官。
卢筝没精打采地回到了监控室,看到小王幸灾乐祸的笑脸,突然明白了过来。“是你给她通风报信的?真是家贼难防啊!”他的拳头还没沾到衣边,小王就大声呼痛,说下次再也不敢了。卢筝笑了一声,饶了他,然后拿了包匆匆消失了。
婚期定在了今年的五一,现在万事俱备,连最让人揪心的房子也装修一新了。这一切当然不是卢筝的能耐,而是沾了未来老丈人的光。作为商场中最有实权的采购部经理,老顾同志之所以看上了卢筝,还不如说是看上了他的家庭。——千万不要误会,卢筝的父母可不是什么高官富户,仅仅是因为他们已过世多年了。在习惯于挑肥拣瘦货比三家的老顾眼中,这样的小伙子做女婿最好了,既可以全心全意为自己送终,娇气惯了的女儿也免了当小媳妇的委屈。
下班的时候,正是地铁运营的高峰。卢筝像只勇敢的冲锋舟一头扎进了人海,到了建国门站,又像潜艇一样在喧嚣的泡沫中浮了出来。可紧赶慢赶,最终还是晚到了一步。
顾雅莉已经下了商务楼,先把私家车开到了道边。卢筝刚上了车,屁股还没有落实,车就箭一般窜出去了。不用看女友的脸色,卢筝就知道今天没什么好果子吃了。果然,这一晚她和卢筝闹了数不清的别扭。卢筝虽然是个倒插门的女婿,但也知道婚礼对一个家庭社交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顾家这样有一定根基的老北京来说,更是马虎不得的。可是,只要他一张口,无论婚宴的酒类还是请柬的格式,都被顾雅莉毫不客气地驳回了。当事人——未来当家男人的难堪不说,连陪在一边的前厅经理都想开溜了。好不容易一切都敲定了,两人将要分手时,顾雅莉突然冒出来了一句:
“我听人说,最近老有一个女孩子来找你,还是美院的学生,人长得忒漂亮,你不会脚踏两只船吧?”
这句话一钻进耳朵里,卢筝的第一反应就是:小王是个双重间谍。可转念一想,又有点吃不准了,因为卢容二人会面都在大庭广众之下,通风报信的人也许不止一个,自己想赖也赖不掉。再说了,老顾的家底众人心中有数,宝贝女儿又是名牌大学的硕士,现供职于外资企业,保不定有人妒忌卢筝的桃花运,正想着取而代之呢!念及此,卢筝立即赌咒发誓,说那个女孩子认错了人。对于他的表态,顾雅莉虽然不大相信,但也并不真的认为是什么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