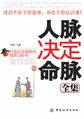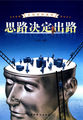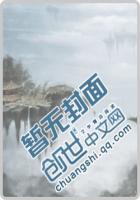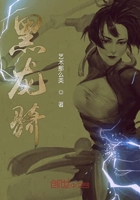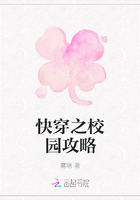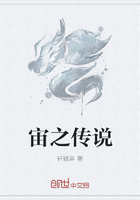他定了定神,立刻怒火中烧,此次失败全怪兄弟公子卬,是谁授权他阵前与敌讲和?娘希匹!是谁让他擅作主张,致使中计而全军倾覆?娘希匹!这个大罪人……魏罃在几乎失去理智的情况下,下令杀掉公子卬的全家大小。等到听说,公子卬因为绝望伤心而投降归顺秦国,才又拜天哭地,略有悔意。
如今国内空虚,国力衰竭,只有遣使求和一条路。
从此,黄河以西地区全部归秦国;魏国只得把重心不断的向东转移,从安邑搬到大梁发展,正因于此,有人开始把它叫成梁国了--耻辱啊,魏惠王变成梁惠王!
好在他还未清醒意识到,自己在兼并战争中已经第一个出局,永远丧失称霸天下的机会和资格,否则会当场吐血而亡。
良药苦口能治病,忠言逆耳可救命
与魏惠王的落魄相反,如今的秦孝公是喜气洋洋;高兴之余,他把於、商等地的十五个都邑赏给公孙鞅,封号为商君。公孙鞅从此又多一个称呼,大家背后都管他叫商鞅--把他原来的大名都遮盖了。
此时的商鞅,那是真的发了、阔了;每次出门,都要带着几十辆装甲车(装有甲士的马车),由威猛的武士贴身护卫着,另有手执长矛、短矛的武装卫士跟车奔走。
如果没有这样的排场,他则宁可不出门去。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为了显威风摆阔,其间也有考虑到安全因素的。
其实,商鞅在秦国替自己收获功名利禄的同时,也得到一种令人不快的副产品--仇人。公孙鞅担任宰相初期,为了树立“法治”威严,除立木悬赏进行利导外,还有更加立竿见影的措施。
他曾经在渭水岸上,对那些反对改革或触犯刑律者,亲自审理诉讼,立判立决,杀人无数,据说渭水都成了一条血河。
做丞相十来年间,把嬴氏的君亲国戚也得罪光了。就在第二次变法后四年,倒霉的公子虔又撞到枪口上,再次触犯法令,鼻子都给割了(劓刑)去,害得人家八年来都是闭门不出--没面子啊!
这一回,商君经友人孟兰皋介绍,认识一个叫赵良的高人,据说十分贤能;商君希望和他结成知交,就这样两人相会。攀谈了几句,似乎话不投机,赵良便干脆说--“千人之喏喏,不如一士之谔谔。我这人喜欢实话实说,习惯直言不讳;要不,就索性不说。我想请求终日直言相谏,不知能不能不受刑罚啊?”
“动听的话是花朵,真实的话是果实。”商君透着无限真诚脱口而出,“良药苦口能治病,忠言逆耳可救命。我既要拜师求教,先生何必拒绝推托呢?你尽管直说就是,不必忌讳,自然也不会怪罪于你嘛。”
话虽如此,道理也是这样的;可明白道理容易,实际操作就困难。对话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该说不该说也都忍不住要说上一说了。
“我听说啊,”赵良开谈了。“从前五羖大夫(百里奚)做秦相时,不管多累都不坐车,炎炎夏日也不打遮阳伞;在国内来回巡行都是轻车简从,几乎不带保镖和护卫什么耶。”
“先生说得对,”商君知道,反驳人家要先从赞同开始。“可是,那都是将近三百年前的古老话,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如今咸阳那么大,都走路的话革命工作就没法开展--是不是?而且,现在社会治安也有点问题的,个别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丧失既得利益,亡我之心不死;加强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正是阶级斗争警惕性高的一种谨慎表现嘛!”
“可是,哈欠、哈欠,”赵良差不多被商君的官腔弄糊涂,一时间接不上话头。“这个这个……算了,咱换个话题。你如今做秦相,大筑门阙,大兴土木,基本上是劳民伤财,这也谈不上什么功绩。对国家来说,造房子那是最小儿科的事情,随便叫上一些农民工造个三层楼、五层楼,举手之劳罢了……”
“是啊,我很高兴能听到先生的诤言。”商鞅耐心说服道,“有些事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就看怎样去理解。我这样移风易俗,使国家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先生难道说不好吗?”
赵良的每一个话题,都被商君礼貌地挡在了耳朵之外。
他想了想,挠着后脑勺接着说:“《诗》云:‘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可我看你,习惯用严刑峻法对待百姓,仿佛他们只是一些会说话的牲口,并没有个人的意识和尊严;凡事不以人为本,完全像计算财物一样计算着得失,这实在是积怨蓄祸,压根儿也谈不上什么教化嘛!”
“我是这样想的,”商君很有耐心的辩解说。“一开始,大家也许会有些不适应,时间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其实,社会就是需要组织嘛,组织起来才有强大的力量--几千年后,先生就会理解我的话是多么有道理的啦。”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赵良总想说出一个理来,“有些事还不是单靠强力所能改变,人性就是其中之一。法也罢,律也罢,完全违背人性的东西,终归不能长久。你譬如说,在非常时期特殊环境,让大家憋足劲去完成一个使命,也许做得到而且有意义;可是如果无限期无休止,让百姓任劳任怨吃苦到底--那还有意义吗?那肯定就是扭曲人性了!
“承蒙您高看我。所以,我还是给商君您一个忠告,不如归还国君赏赐的十五个都邑,到乡野去耕田务农;反正你想干的,你也干成了。再劝国君举用在野隐居的贤士,续用有功的人,尊重有德的人,赡养老人,抚育孤儿……这样,就会得到一些安全。您要知道,如果继续把持秦国教令,积蓄百姓怨恨,等到君王撒手人寰时,你想全身而退恐怕也难了哇!”
“可是,”商君很为难。“先生以为,我真的只是为了一己的富贵吗?”
“无论为一己,还是为一国一天下,”赵良说。“凡事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发展,结果都不会很妙。更何况,谁又能包打天下呢;该收手时就收手,对哪方面都更有好处。”
功高盖主的下场
看起来,赵良的话也是多余。
就算商君真准备言听计从,彻底实行归隐退休策略,那也有可能来不及。
何况,商君压根儿就没打算那么做,辛辛苦苦得来的荣华富贵,岂能拱手送出去哩--那不是白忙活吗?除非人类进化成了不吃人间烟火的活神仙!
“再说,”商鞅也认真考虑过。“国君正值盛年,离‘君王撒手人寰’的时候,还遥远着哩;至少还可以享受几十年,到时候再看情况嘛。”
也许给赵良乌鸦嘴讲坏菜了,人到中年的国君嬴渠梁居然真的开始生病。
那时西医未传进中国,中医还不发达(当时的西医也不发达嘛);医师只一个扁鹊,也不清楚到底在不在世……所以,但凡得病就只好听天由命,哪怕小小阑尾炎都可能送掉大人物的老命。
当然,暂时还未考证清楚:嬴渠梁到底得的是急性病还是慢性病,唯一确定的是他在商鞅和赵良谈话五个月之后就死了。临终前,据说国君曾有意出让秦国给商君,商鞅“辞不受”--或许只是试探性质的“阳谋”呢?虽然利令智昏,他可不敢答应!
四十四岁的秦孝公,不治身故。
接着,太子嬴驷即位,就是后人叫的惠文王嘛。
公子嬴虔,终于意外地等到了时机。
为了给自己的鼻子报仇,他手下的党员第一时间就揭发商鞅,说商鞅这个反革命分子,一眼就看得出来有造反的想法和念头。造反证据不很多,但是根本没法排除嘛。
有人提醒刚执政的嬴驷,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现如今连居委会老太太和少先队员们都在认真学习商君之法,不说主上之法。如此情形是商君反为上司,国君变为下属。而且,商君还是主公仇人啊,希望趁早下手。”
随即,“国安局”向全世界发布A级通缉令,派国际刑警逮捕“企图造反”的商君。
这时的商君,虽然芳龄只有五十三岁,身体棒棒的,行政经验又特丰富,可再想继续为革命工作半个世纪已是不可能。他只得撒开脚丫,像兔子一样逃跑。
逃跑中的商君带着老母亲和家属子女,狼狈到达函谷关后,想找个国营招待所(旅舍)休息一下;十分守法的招待所所长不假思索背书说:“商君的法令有规定,凡是没有证件的旅客,你去收留他,你就犯罪了。所以客官,实在对不起,我不想犯罪。”
商君此刻可不敢说:这正是老子我规定的嘛。
他只好自认倒霉,悄悄地叹着气说:“这才叫‘作法自毙’呀。真是糟糕透顶:我没有造反,是人家诬告的;可我寸步难行,插翅难飞……而且有冤屈也无处申诉啊!”
商君好歹还是混过函谷关,逃到魏国地面。然而情况非常不妙,当魏人认出他的“秦国总理”身份后,居然没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更没有人送上鲜花,而是斜着眼鄙夷怒骂起来--“就是这个卑鄙小人,前年用欺诈手段绑架了魏将公子卬,灭了魏军;你也有今天的下场啊,实在太好,报应还真快哪!Goaway!你给俺滚犊子--哪来回哪去!”
商君这才感到有理说不清的痛苦,战场上的“兵不厌诈”,却被普通老百姓理解成“做事情不地道”!他不敢理论,准备投奔别的国家去;说实在,附近也没有几个国家敢冒犯秦国,商君这个“秦国的逃犯”被义愤填膺的魏国人扭送回秦国了。
回到秦国地面,商君一行逃难的更是走投无路。
不得已,只好带着家眷一路狂奔猛赶,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
商君自己觉得很委屈,西向入秦二十余年以来,为秦国中兴大业可谓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对秦国忠心耿耿到了“忘我”的走火入魔的崇高境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嘛……对此,落难中的公孙鞅、卫鞅、商鞅、商君,怎么也想不通。
“既然都说我造反,”商君横下一条心来。“他妈的,那就反一回吧。”
下定决心后,也就不怕牺牲了。商君与部属家臣,放手发动守邑的兵丁,很快组织起一支队伍,向北去攻击郑县,企图在地球上寻找一条新的活命之路。
秦国于是发兵攻打,在黾池一带擒获商君;按照商君亲手制订的法律条款,造反的商君被国君嬴驷处以“车裂之刑”。不久后在彤那个地方,上演一幕五马分尸的血腥闹剧。
当地百姓都赶去参观,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他们愤怒声讨血泪控诉犯罪分子的滔天罪行,向临刑前的商君丢破鞋、扔臭鸡蛋……像过节一样扭秧歌,高唱着“新国君决定真英明、真英明,千万人民齐响应、齐响应……”
总之,欢天喜地庆祝伟大祖国的“伟大胜利”。
历史真实地记载说:秦人不怜(商君)。
商君被镇压后,秦国依法灭了商君之族--妻儿老小一窝端。
伟大领袖嬴驷告诫大家说:“不要像商鞅那样造反。”
这一年,正是公元前338年。
下面是战国七雄最高领导人及其在位年头的简表。
我敢担保,这儿每个名字后面曾经都是富贵逼人的一段鲜活人生,充满美丽和哀愁;也与此刻的你我一样,怀着喜怒哀乐等七情六欲,走过春夏秋冬、惯看春花秋月……想想吧,两千多年前就在我们生活的祖国大地上,有七个政治集团(相对较小的那些且不算)为着自己的理想和利益,各聚英豪、裹胁芸芸众生互相残杀,进行殊死搏斗。
这一斗就是两三百年,殃及十几代人,无数生灵惨遭涂炭。
欲望无极限,道德无底线。
如果想窥探一下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看书恐怕是不行的,但完全相信书本上的话也是不行。因为,历史教科书多数由胜利者书写嘛。请问,有谁愿意为失败者辩污呢?
要了解那一场旷日持久的“跨世纪”大战,其实很不容易。后人中的无数历史专家们孜孜不倦,试图厘清先人们的光辉事迹;尽管怎样努力,都难免挂一漏万,或者干脆张冠李戴,让牛头对上了马嘴。
本人作为草根中的非历史专家,想讲述那个漫长而遥远的故事还试图避免过分的离谱,于是先开列出一些简表,权当正文说事之基本依据。OK,如果您觉得没必要看图表,只图个轻松一乐,那就直接跳过去看正文得了。
万一出现“关公战秦琼”的精彩片段,务必请同志们多多鼓掌、不吝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