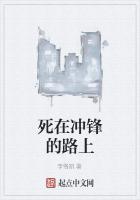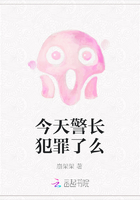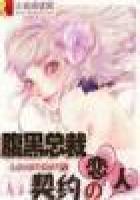秦王遂拜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秦人皆知张禄为丞相,无人知张禄便是范雎。
魏国闻听秦王用丞相张禄之谋,欲东伐韩、魏,遂遣中大夫须贾前来秦国求和。范雎闻听须贾至,喜曰:“须贾至此,吾可报仇矣。”于是,穿上破衣烂衫,装作寒酸落魄之状,来到馆驿,求见须贾。
须贾一见,大惊曰:“范雎别来无恙乎?吾以为汝被魏相打死,何以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时吾尸被扔郊外,次早方苏,刚好有客商经过,闻听呻吟之声,出于同情,救吾一命。我不敢回家,逃到秦国。不想在此又见大夫之面。”
须贾曰:“汝可曾游说秦国乎?”范雎曰:“某带罪之人,逃命在此,只望苟且偷生,岂敢游说秦国乎?”须贾曰:“汝在此何以为生?”范雎曰:“为人作佣,聊以度日。”须贾面露后悔之意。是啊!要不是他须贾,此人何以背井离乡,如此狼狈!
须贾叹曰:“想不到范雎贫寒如此。”看范雎破衣烂衫,冷得发抖,遂请一同就座吃饭饮酒,又命取衣袍一件穿在范雎身上,范雎曰:“大夫之衣,小人如何敢穿?”须贾曰:“你我同是魏国人,今在异乡会面,不必客气。”范雎连声称谢。
范雎问曰:“大夫来此何干?”须贾曰:“吾奉命出使秦国,欲求秦国不加兵于魏。今闻丞相张君用事,吾欲通之,恨无人引见。汝在秦日久,可知有谁能为吾引见乎?”范雎曰:“我家主人与丞相关系不错,丞相也喜欢我能言善辩,因此,我可以为大人引见。”
须贾大喜曰:“既如此,烦请范雎与丞相约定时日,以便下官拜见。”范雎曰:“丞相平日事忙,今日正好闲暇,可以相见。”须贾曰:“吾马染病,车轴折坏,不方便即行。”范雎曰:“我可为大夫借我主人之马车。”须贾十分感谢同乡的大力帮忙。
范雎亲自为须贾赶车,快到相府时有认识丞相者,皆敬而让路。须贾以为人们敬重自己,颇为得意。来到相府门口,范雎曰:“汝在此稍候,待我入内禀报。”须贾等了半天,不见回音,遂问门人曰:“范雎入内禀报丞相,为何不出?”门人曰:“君所言范雎,果系何人?”须贾曰:“刚才为吾赶车者。”门人曰:“赶车者乃丞相张君,何言范雎?”
须贾闻听此语,如梦初醒,犹如晴天想了一个炸雷,只觉脑子轰的一声,险些晕倒。待他回过神来,头上冷汗直冒,浑身抖个不停。遂跪倒于相府门外,口称死罪,谓守门者曰:“请禀告丞相,魏国罪臣须贾,在门外跪拜候死,请丞相发落。”
守门人也被弄糊涂了,此人刚才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如今却如此模样。既然他让禀告,守门人也只得照办。范雎命须贾来见。须贾匍匐而进,跪拜于堂下,叩头不断,心惊肉跳,口里不住地言道:“罪臣实为死罪,还望丞相念同乡之谊,从轻发落。”
范雎高坐大堂之上,怒视须贾曰:“汝罪有几?”须贾曰:“臣罪不可胜数,比臣头上之发更多数条。”范雎大喝曰:“汝罪有三:我为汝巧对齐王,使汝使齐成功,汝却恩将仇报,诬告我通齐,罪一也;魏齐以酷刑拷打我,使我血流满面,折齿断骨,汝无一言谏止,罪二也;我当日昏死过去,被弃厕中,汝竟率众宾客以小便溺我,汝何以如此残忍乎?罪三也。有此三罪,本当斩汝之首,但汝却在馆驿见我贫寒送袍赠食,尚有一点人性,尚念故人之情,故饶汝不死。”
须贾听到“不死”两个字,才将提在嗓子眼上的心重新放回到肚子里,连忙叩头谢恩。范雎命他回馆驿候命。须贾抱头鼠窜,仓皇而去。范雎遂入见秦王,将他蒙冤受难、隐姓换名、逃来秦国的事一一告知秦王,请秦王恕他欺君之罪,并说魏现在遣须贾前来求和。秦王叹曰:“不想相国蒙此大冤,今须贾至此,可斩其头,以慰相国。”
范雎奏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况求和乎?臣岂敢以私怨而伤公义!且欲致臣于死地者,魏齐也。”秦王曰:“卿先公而后私,真忠臣也。魏齐之仇,寡人当为卿报之。须贾任卿发落。”范雎谢恩而出。
秦王听从了范雎的建议,准了魏国的求和。须贾来辞别范雎,范雎曰:“故人至此,不可不吃一顿饭就走。”遂令两个小卒领须贾到一间小房候着,须贾谢天谢地而去,小卒让他进入小房,小卒在外守着。
时值隆冬之际,房中无火炉,又无茶水,冰冷无比。须贾自晨至午候了两个多时辰,此时又冷又饿,并不见人来请他吃饭,也不敢问小卒,两个小卒轮流吃饭,只有他须贾无人理睬,又不敢发作,只得忍着。
又候了两个时辰,直至天快黑时,才听到外边人声嚷嚷,人言丞相设宴请客。此时须贾已知范雎并非真的要请他,但他又不知范雎要把他怎么样,因而,心里七上八下,又愁又怕;感到口干舌燥,肚子又饥又饿;浑身又冷又困。此时的须贾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无边无际的苦海深渊,陷入绝望境地。
他想难道范雎又生变卦,欲杀自己不成,或者莫非他想把自己困死在秦国。正当须贾百思不得其解时,忽听来人传话曰:“丞相令带魏国使臣用餐。”两个小卒带须贾来到范雎面前,须贾见宾客满座,看到桌上美酒佳肴,十分丰盛,顿感更加饥饿,口里不住地咽唾沫。
范雎命另置一小桌,桌上并不放酒食,只放一些喂马用的料豆,令两个面部刺字的囚徒手捧料豆喂须贾,如喂马一般。众客甚过意不去,问曰:“丞相为何如此恨此人?”范雎遂将前事细讲一遍。众客曰:“果如此,该有此报。”
须贾虽然受辱,但不敢违抗,只得勉强食之,食毕还要叩头谢恩。范雎怒目骂曰:“今留汝命,回报魏王,速将魏齐之头送来。不然,我将亲率大军来屠大梁。”唬得须贾魂不附体,连连叩头称是,连夜跑回魏国复命。
魏齐闻听范雎为秦相,欲索己头,遂逃奔赵国,藏匿在平原君家中。秦王诈招平原君入秦赴宴,平原君不敢不往。最后秦以平原君为人质,索要魏齐。魏齐走投无路,不得已,遂自杀。赵王遂派人送魏齐头于秦王,秦乃放平原君归国。
秦王派人送魏齐之头于范雎。范雎看到仇人之头,切齿骂曰:“汝既为相国,却偏听偏信,欲致我于死地,酷刑拷打,使我血流满面,折齿断骨,何太残忍乎?幸苍天庇佑,我大难不死,得报此大仇。汝今日得死,实咎由自取也!”
四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一日,范雎遇见王稽。王稽说范雎如今高居相国之位,大仇已报,不该忘记王稽带他来秦之功。范雎听了虽不太高兴,但觉王稽说得有道理。
遂入见秦王曰:“臣本布衣,遭人陷害,几不得生。幸来秦国,得大王重用,官至丞相;大王又为臣报了大仇,臣愿足矣。然臣非郑安平不得活命,非王稽不得入秦,臣愿大王降臣官爵,加封此二人,让臣报二位之德。”
秦王于是加封王稽为河东守,加封郑安平为将军。王稽、郑安平二人谢恩,各自领命赴任而去。
秦王既许魏国求和,遂用范雎之谋,远交齐、楚,一心一意蚕食韩国,两年里三次伐韩,韩国丢失了不少城池,遂向东求救于赵,上党守将不敌秦军,遂率上党郡十七城兵将投降赵国。
秦国遂加兵于赵,赵用廉颇为大将。廉颇老谋深算,智勇双全,知道秦国兵强将勇,但路途遥远,粮草接济困难。因而深沟高垒,只守不战,并传令:“擅自出战者,即使获胜,也要斩首。”与秦兵相持四个月,任凭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兵无计可施。
范雎谓秦王曰:“廉颇善于用兵,今坚守不战,我军难以取胜。若迁延日久,我军粮草不济,必然陷入被动。臣有一计,可去此人,然后方可击败赵军。”秦王大喜曰:“卿有何计,可去廉颇?”
范雎密谓秦王曰:“要去廉颇,除非用反间计,王出黄金若干,如此这般,便可成功。”秦王闻言大喜,即命取黄金若干于范雎。
范雎命心腹人持金连夜从小道入邯郸,贿赂赵王左右,布散流言曰:“赵将只有马服君善于用兵,闻其子赵括勇猛无比,更胜其父,若使为将,秦兵必败。廉颇老而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今为秦兵所逼,不敢出战,不日将出降矣。”
赵王亦听说赵兵连吃败仗,使人去长平催廉颇出战。廉颇主张坚守,不肯出战。赵王疑其年迈怯战,加上左右反间之言,遂信以为真。于是,让马服君之子赵括替代廉颇为将,总领赵军,又增兵20万,以拒秦军。
那赵括虽是将门之后,但却一点也未继承他父亲的用兵智慧,且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夸夸其谈,只知死记硬背兵书上的干条条,不懂变通,属典型的纸上谈兵型庸才。更要命的是,赵括以前从未经历过任何大的战阵,而赵王却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此人为大将,岂非上天要败赵乎?
连赵括的母亲也劝赵王另选良将,勿遣赵括。然赵王就是不听,坚持用赵括为将,以敌秦军。赵括谓赵王曰:“秦若派武安君白起为将,臣尚需费心筹划,区区王龁,诚不足道也。”赵王大喜。
秦国探得赵括之语,密令武安君白起从咸阳起程,亲临前线,临阵指挥,令王龁为副将,协助白起攻打赵军。赵括并不知白起已至秦军大营,因而不把王龁放在眼里。两军首战,赵括小胜,遂更加狂妄,自以为数日之内便可打败秦军。
白起就是要让赵括产生轻敌情绪,以便使其上钩。赵括果然中计,秦军遂大败赵军;赵括被乱箭射死,40万赵卒全部投降,不久,一夜之间全部被坑杀。长平之战总计杀死赵兵45万人,只留240人放回邯郸,使宣扬秦国之威。白起遂率大军进攻上党,上党17城全部降秦。
秦军声威大震。白起遂移兵围邯郸,欲以得胜之军一举拿下邯郸,灭掉赵国。赵国都城邯郸人心惶惶;赵国举国上下哭声一片,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母哭其儿,妻哭其夫,大街小巷,号痛之声不绝。
赵王大惧,急遣苏代入秦游说范雎,向秦国求和,使秦撤兵。苏代入见范雎,范雎问曰:“君为何而来?”苏代曰:“为君而来。”范雎曰:“愿闻其详。”苏代曰:“武安君用兵如神,为秦夺得城池七十余座,斩首近百万,虽伊尹、吕望之功,未必过此。今又兵围邯郸,赵国亡在旦夕。赵亡,则秦成帝业,秦成帝业,武安君则为秦之伊尹、吕望矣!君能为其下乎?就算君不计较个人名爵,愿为其下,然秦兵曾困上党,上党之民宁愿降赵,而不愿为秦之民。天下之民不愿为秦民由此可见。假使秦国灭了赵国,赵国之民北可投燕,东可投齐,南可投韩、魏,秦只得一空国而已,于秦又有何益?为君之计,不如许韩、赵割地求和。如此,割地为君之功,攻城为武安君之劳,使其不得独擅伐赵之功,君之功何亚于武安君乎?”
苏代这一席话,正好说到范雎心里去了。范雎遂入见秦王曰:“秦兵在外征战日久,不宜再战,可许韩、赵割地求和,休养士卒。”秦王准奏。
白起正欲围攻邯郸,忽然接到班师诏书,知是范雎之谋,不让自己成此大功,因而深恨范雎。然王命难违,白起不得不班师回朝。
但失此灭赵时机,白起当然耿耿于怀,遂言于众人曰:“长平大战,邯郸城中一夜十惊,若乘胜攻击,不出一月城便可破。可惜应侯不知兵要,主张班师,失此良机!”秦王闻之,大悔曰:“白起既知当时邯郸可破,为何不早奏?”秦王只知责怪白起,并不知范雎让秦撤兵是出于私心。
秦王越想越悔,遂复议伐赵,武安君染病不能行,秦王乃命王陵为将,讨伐赵国。赵王后悔当初让赵括替代廉颇,使赵国一败涂地,遂亲往廉颇家中赔罪,欲廉颇为将抵御秦军。廉颇感其诚意,欣然为将,仍采用坚守不战之谋,却以家财招募敢死之士,不时乘夜间袭击秦营。秦军损兵折将,不能取胜。
半年后,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其替代王陵伐赵。武安君奏曰:“昔长平大败,邯郸城中人人心胆俱裂,因而乘之,其守则不固,攻则无力,可一举而破。今迁延日久,人心已定,又兼廉颇老将,非同赵括。况秦方许赵之和,今又攻之,诸侯必以秦无信义,会联合助赵,如此,秦军会面对多国之兵,必然大败。”
秦王不听,命白起前行,白起固辞。秦王复命应侯请之,白起恨应侯,称病不往。秦王心中不悦,遂命王龁替代王陵。
不出白起所料,楚国出兵助赵,攻打秦军;秦军连连溃败,损失惨重。白起曰:“吾固知邯郸未可破也,今如何?”秦王闻之,大怒,强令其临阵指挥,武安君称病重。应侯往请,也不肯行。秦王遂贬武安君为士伍。
三个月后,秦军依然连吃败仗,秦王好生烦恼,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白起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范雎奏秦王曰:“武安君被贬,颇有怨言,恐作乱。”秦王乃令使者赐白起宝剑,令其自裁,白起遂自杀。
秦王命郑安平领兵助王龁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困,不得突围,竟带2万秦兵降赵。范雎大惧,坐卧不安,遂向秦王请罪。因为秦国之法,荐人而所荐不善者,有罪。郑安平为范雎所荐,按秦律当夷范雎三族。
秦王扶范雎落座曰:“郑安平犯律,与丞相无关。”遂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有罪。”对范雎信任如初,赏赐更多,以安其心。过了两年,王稽又犯通敌叛国罪,范雎更加惶恐不安。
此时,燕国有一辩士,名叫蔡泽,来到秦国。蔡泽以雄辩的口才,列举了文种、商鞅、吴起、苏秦、白起等天下豪杰智士,贪富恋贵,功成不退,死于非命的悲惨下场,并告诉范雎,进退盈缩,与时变化,是圣人处世之常道。今君大仇已报,官至丞相,尚不思退,则文种、商鞅、白起等人之祸,恐难免矣。
范雎曰:“善。吾闻‘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之言,范雎愿听。”遂进荐蔡泽于秦王。秦王召见蔡泽,与语大悦,拜为客卿。
范雎请归相印,秦王挽留不许。范雎曰:“臣年迈体衰,愿归相印以养老。今蔡泽智士,胸中韬略,不亚于臣,大王何不拜为丞相?”秦王准其所奏。
范雎遂回到所封之地,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安享晚年。
范雎对我们今人的启示
1.范雎以前的秦国谋士,可以说主要是以增强秦国的实力为主,从范雎起才制定了一统天下,成就帝业的基本国策和战略方法——远交近攻法。可以说,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国富民强,而范雎的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国一统华夏指日可待。远交近攻策略,对于秦国一统华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远交近攻也成了军事上的一个重计策,古今中外的许多战例中都采用了此计策。它还被广泛应用于其它领域。远交近攻的核心是:面对强大之敌,先与距我较远的敌人搞好关系,分化瓦解敌人,对距我最近的敌人实施重点打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使我方实力逐渐增强,最终全部歼灭敌人。
2.人人都有私心,范雎也不例外。假若范雎不听苏代的游说之词,白起也许乘势一举就将赵国都城拿下了。赵国若灭,秦国一统华夏的速度就可以大大加快。
然而,苏代的到来,却改变了这一切。这都是因人的私心作祟,范雎为了自己的官位,不仅使秦国的一统大业向后推迟若干年,还使战功赫赫的白起死于非命。
范雎当年被须贾、魏齐陷害,险些丧命,他因此十分痛恨此二人,并最终要了魏齐的命。如今他却为了自己的官位,置国家利益不顾,陷害白起,并使其死于非命。难道他就不怕白起的冤魂向他索命吗?
3.范雎不愧为一代明智豪杰,虽然也爱当官,甚至为了自己的官位不顾秦国帝业,将战功显赫的白起置于死地,但不过分贪恋权位,且能听别人的正确建议。当郑安平降赵后,他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后来王稽又通敌,他更加如坐针毡,不知所措。蔡泽的劝说,使他下决心功成身退,这正是他的明智之处。
在这一点上,范雎就要比伍子胥明智得多。范雎、伍子胥都为报仇而投奔他国,然范雎报仇后听人之劝,及时身退,因而安享晚年;伍子胥大仇报后,孙子也曾劝他离开,而他却贪恋权贵,不听人劝,仍久居大位而不退,结果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