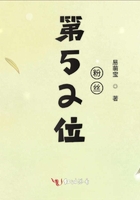寒煊单膝跪在地上,仍由我如何打他,都一动也不动的承受着,一只手死死拽着,如何也不放开。
“放——开——”我喊,声音终究从牙缝中挤出来,带着让人无比难堪与想死的哭腔,两年了,就算是两年前,听到那些所谓的真相时,我也没有哭得这么狼狈过。
凭什么,这半年来,他要理所当然的陪我演戏,说什么是为了要补偿我,不想离开我,那我呢?我这半年****卖笑一样的生活算什么?他就这么享受吗?享受我婊里婊气的模样,到如今还要跟我求婚,还要我们以后一辈子都好好的,他想的倒美!
我都还没有好过,他凭什么觉得一切都可以翻篇过去,还想当然的展望新生活,想当然的将我脱离泥潭,凭什么!
单方面的厮打中,我张开嘴,一口狠狠的咬在他的肩膀,深深陷入肉里。
他闷哼一声,狠狠的抱住我,几乎要将我腰嘞断了,却仍旧不放手。
“铛!”教堂大门被猛的推开。
“暮慕悠,你住手!”一帮人气势汹汹的鱼贯而入,首当其冲的气势如虹的,不是杨九又是谁。
我抬起泪眼看去,软弱与痛苦转瞬收起,化作冷笑。杨九带来的阵仗倒是不小,连柏然都请来了,两年不见柏然老了不少,头发花白,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看上去身体孱弱,一张尖利的嘴脸却还是那么刻薄满满。
不等她们一路气势汹汹的杀到面前来,我已经一改泪流满面的狼狈模样,回头伸出右手,冲寒煊呲牙一笑,道:“你不是要跟人家求婚么?戒指呢?我现在又想要了。”
他一愣,转瞬间便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又要开始演戏报复了。
他分明知道的一清二楚,眼中的痛苦只一闪而过,却仍是毫不犹豫的点头,将那戒指套在了我的无名指上。冰凉的指环套在指尖,手指轻轻一颤,微微凉。
这一刻起,有十字架为证,有牧师见证,有在场目瞪口呆的做礼拜的人的见证,无论它是否走心,我都算,嫁人了。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走出这一步,就不会后悔。
“煊——住手!”杨九哭着喊。
我眼疾手快的抢过寒煊手里的另一枚戒指,拉起他的手,指环不大不小,正好套在他的无名指上。转眼望向一旁的牧师,微微一笑。
牧师正目瞪口呆,触到视线,下意识结巴道:“礼,礼成,祝福你们……”
话音刚落,那群黑压压的人群终于冲到面前,杨九一把打落了空空的戒指盒子,再看到我和寒煊手上那戒指的样式,直接接近发狂——那刻着暮慕悠名字的戒指太过显眼,太过让她绝望。
她一把拽过我的手,就要将那戒指取下来。
她施暴的手刚要行动,就被寒煊冷冷推到一边。
杨九险些摔倒,回头便忍不住哭喊:“煊!你送她那枚戒指——你知道她是暮慕悠!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就不管伯母的想法了吗?乱|伦这种事情你们真的做得出来吗!”
强行被动看热闹的教堂里的众人一片哗然,牧师一时也有些不知所措,我被寒煊藏在背后,拽着他的衣角怯怯的往杨九望去,好不无辜的装可怜。
“杨小姐,你不要血口喷人好不好,人家叫简芙,到底要我说多少次你才明白嘛。”
杨九瞪我,因为恨意,眼里竟然布满血丝,“贱人!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是不是!假装跳海,再整容回来,现在变成狐狸精勾引寒煊,竟然还带你来教堂结婚!妈——你看看寒煊就是这么对我的——”
回头,只见柏然坐在轮椅上,被寒月茹推到寒煊面前,面色铁青,瞪着我:“暮慕悠,我以为你两年前识趣的知道自己消失,没想到你现在还执迷不悟,你没完没了的闹,当真是要毁了我家煊儿才甘心吗!”
我眨巴着大眼睛,眼泪挤出几颗,好不无辜,“阿姨,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暮慕悠啊——”
寒煊将我拦在身后,抢话过去:“无论她是谁,她今天都是我寒煊娶了的女人,从今天起,她就是我的妻,谁也不要再多说了。”
闻言,柏然一口气没上来,脸色瞬间惨白一片,捂住胸口,简直要气死过去,“孽,孽子……”
寒月茹慌张的替柏然拍着胸口,一边给他顺气,一边担忧的望一眼寒煊,“哥,妈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你别……”
她还要说什么,寒煊却充耳未闻,径直拉起我,气势汹汹的就要离开。
“煊——你连伯母都不管了吗!”杨九尖声喊。
她今天是堵上了最大的筹码——带柏然来搅局,柏然是寒煊的逆鳞,因为从小就失去父亲,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所以寒煊对柏然的感情非常深,从前的许多事情寒煊都为柏然妥协过,当初柏然将我赶出寒家就可见一斑了。
我一时也有点拿不准,要是现在寒煊临阵变卦,为柏然再次妥协,那我真是半点办法都没有。
闻声,寒煊顿住脚步,我的心也跟着悬起来,他却头也没回,冷声说:“妈,事不过三,儿子这一次做的决定没有谁能够改变,如果你能顾及儿子这一次,我感激你,如果你依旧不能——别怪儿子不孝了。”
说着,拉着我,继续头也不回的直往教堂的大门外走。
“煊儿——”柏然凄然的喊。
那声音突破长空,带着沙哑的断尾,骤然间,那边乱成一团。
“伯母——你醒醒啊伯母!”
“煊!伯母晕过去了!”
这下子,寒煊是走不掉了。犹豫片刻,他转身回去,视线跟我交汇片刻,我却主动一笑:“不用管我,先送咱妈要紧——”
说咱妈,就是承认我是他寒煊老婆的身份了。
他眼眸一紧,眼眶刹那间竟然有些湿润,却是飞快点头,在众人的合力中,柏然很快被送到医院。其实柏然的病已经是老毛病了,脑部神经压迫,一旦情绪激动,很容易血压就上头,要是情绪再过分的气炸了,她脑袋上的血管爆裂而死都是有可能的。这样的状况下,杨九都能将柏然带到教堂现场来破坏寒煊和我的“婚礼”,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重症监护室外,寒煊始终冷眼,听医生说完情况,没有说话。
杨九说:“煊,伯母现在的病情很危机,根本受不了任何刺激,如果你再——”
“咚!”
一声巨响,寒煊面前的一扇玻璃窗应声而碎,医生惊叫一声,却很快噤声,寒煊冷冷回头,却是连正眼都没有给杨九一眼,“告诉韩院长,我母亲如果再从重症监护室以外的地方出现,这所医院,我不介意亲自替他铲平。”
那医生浑身一抖,下意识看了眼杨九,却是不敢多说一句,唯唯诺诺的点着头,飞快出去了。
“你也可以滚了。”
杨九泪眼一顿,难以置信道:“煊——你怎么能够这么对我!今天我带伯母去教堂,完全是依着伯母的意思,当初的事情你不是不知道,你这样一意孤行,只会害死伯母——”
“杨九。”寒煊突然冷声打断她的话。
杨九一愣,就听寒煊一字一顿道:“我叫你滚。”
泪顷刻滚出她晶莹的眼眸,这次除了委屈,还带着恨。
“寒煊,你非要做到这个地步,无论我怎么做都不回心转意了吗?!”
寒煊面无表情,他从不会重复狠话,他也从来不打女人,所以即使气到极点,也只砸碎一面玻璃,但如果杨九继续说下去,他不确定自己会做出什么失控的事情来。
作为新上任的“妻子“,我轻轻拉住寒煊的手,颇为安慰的拍拍他手背,他浑身微顿,我说:“杨九,说句公道话,你明知道煊的母亲病情很重,却还把她弄到教堂去参加我们的婚礼,真的很过分!你这么做,根本看不出来你是真的在乎寒煊,只会给人感觉,你自私又心狠手辣,为了抢到想要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而已——老实说,作为一个前妻,你到现在还口口声声说爱寒煊,我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除了像条狗一样难缠,摇尾乞怜的求爱,嘶……你什么时候这么没出息的?”
“你闭嘴!”她尖声喊,浑身气的发抖,要不是寒煊将我护着,她几乎要立刻抓狂上来挠花我的脸才罢休。但另一方面,她却也是碍于自己的确理亏——害得柏然现在命悬一线,她知道寒煊恼她。
当即眼眶一红,改口软声道:“煊,对不起……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跟伯母说了那些事情,所以伯母才让我必须带她去找你——我不是故意的!”
我皱眉,一声叹息,好不纠结的劝道:“杨九啊,再多说也无益啊,你现在就消失了好不好嘛,我看煊真的很不想看到你,你不是爱他吗?爱他就放过他嘛,你快走吧。”
杨九再也忍不住,歇斯底里的吼:“暮慕悠!你是不是当****当上了瘾!先是跟自己的哥哥暧昧不清,又爬上我老公的床,现在知道煊跟你是有血缘关系,还要执迷不悟跟他结婚,你不怕被人耻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