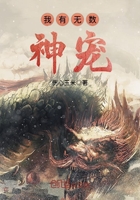莫老五哈哈一笑,道:“这是我祝融国辖地,谁会对我动手?”说罢打马前奔,直入子午谷,一口气跑了五里,停于当地。辛怜气吁吁赶上,叫道:“真的有埋伏!”莫老五面对空山,道:“哪里有埋伏?”辛怜道:“或许就在……”一语未了,耳听有人说道:“二位,俺在此恭候多时了,一同上路吧。”
这声音发自山头,二人抬眼望去,只见山上足有两百人,个个张弓搭箭,杀气腾腾。说话之人昂然挺立在最前面,生得倒有几分英俊,只是有点斜眼儿。辛怜惊道:“大将军,他们果然动手了。”莫老五道:“他们是谁?”辛怜故作神秘,道:“说出来你也不信,就是你的富泰兄弟。”莫老五呵呵一笑,显然不信。
辛怜冲“斜眼儿”喊道:“你受何人指使?”
“斜眼儿”答道:“大将军要我等新贵与隶人平等,还要自耕自食,难道出生入死造反,就想得到这等结果?至于我受何人指使,不用你管,所有新贵都想看到大将军人头落地,我是在替天行道!”
莫老五怒道:“满口胡言!”
辛怜道:“大将军,他说得有理。”
莫老五道:“闭嘴!”摘枪在手,正要催马上山,辛怜忙道:“不可!或许箭上有毒。”“斜眼儿”应道:“算你说对了!箭上果真有毒,沾上星点,登时毙命。”此处无林木遮掩,若山上乱箭齐发,莫老五二人无处可躲,定会死于非命。辛怜又气又急,冲“斜眼儿”喝道:“本姑娘是御妹,若你放下兵器,本御妹可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朝廷大军随时会来,那时你等必被碎尸万段!”
“斜眼儿”哈哈大笑,道:“除非大将军收回‘盛世之法’,否则你二人必死无疑!”
莫老五正急思对策,只见辛怜更加大义凛然,说道:“辛怜纵死,也不许你等伤大将军一根毫毛!”言犹未了拍马便往山上冲。莫老五失色大叫:“御妹留意!”见辛怜奋不顾身迎着利箭扑去,莫老五轰然一震,生死关头方显真情,这一瞬间莫老五对她竟有些原谅。但见辛怜已飞马上得山头,莫老五心急如焚,从马背上飞身旋起,直直飙向“斜眼儿”……
“斜眼儿”表情错愕,显然对辛怜和莫老五在毒箭威胁之下的举动始料不及,只顾“呀呀”怪叫,下令放箭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莫老五、辛怜已同时来到。辛怜手一扬,“斜眼儿”顿时被锦绞索缠住。莫老五初见辛怜身手,又是一呆,想不到她会有这等绝技,不及细想,只见辛怜手一抖,“斜眼儿”倒地翻滚。众人见头人被制,哪个还敢乱动?慌忙撇下弓刀,跪倒在地。
莫老五以为这些人是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弟兄,只是受人蒙蔽,自然不肯下杀手。
辛怜喝道:“说!你受谁的指使?”
“斜眼儿”既已被缚,变得异常乖巧,答道:“富泰将军和大贵大夫。”莫老五喝道:“胡说!富泰与本大将军情同手足。”“斜眼儿”道:“千真万确!”一时难辨真假,莫老五道:“本大将军自会查清。”示意辛怜把他放了。
辛怜一抖锦绞索,“斜眼儿”翻了几个跟头,绳索自解,额头上摔出一个大包,乌青锃亮,却不敢揉搓一下,慌忙跪地磕头。不料就在他跪地的瞬间,忽然摸出一把尖刀,朝莫老五刺去。事起突然,让人猝不及防,耳听辛怜叫道:“夫君留意!”迎着尖刀扑去。莫老五惊叫一嗓,飞步前趋。辛怜惨叫一声,衣袖被划开一个口子,鲜血渗出,白衣溅红。莫老五大怒,毫不迟疑将杀招送至“斜眼儿”眼前,猛听辛怜叫道:“夫君……”叫此一声,仰面便倒。莫老五只得弃了“斜眼儿”,抢步揽住辛怜。
辛怜疼得欲昏欲死,凄然一笑,道:“夫君既已答应放他,就该言而有信。”
莫老五迟疑一下,冲“斜眼儿”喝道:“滚!”
“斜眼儿”一干人惶惶然连滚带爬跑了,不多时便消失在沟壑之中……
经此变故,莫老五对辛怜的厌恶果然去了不少,神情关切,再三察看伤势。其实,辛怜只是受了点皮肉伤,但她岂会放过这等绝佳机会,一时娇媚百态,柔情万种,轻声细语道:“疼!只怕不能骑马了。”莫老五并未多想,道:“无妨,我与你同乘一骑。”辛怜等的就是这句话,因适才在情急之下脱口喊出“夫君”二字,此后便顺其自然,并不显得唐突,喜滋滋说了一声“夫君走吧”。莫老五把辛怜抱于马上,沿子午谷朝前走去……
待二人走远,“斜眼儿”从深沟里探出脑壳,朝身后摆了摆手。
耳听一声叫板,鸠形鹄面的水圣使亮了相,依然拿捏着舞台架势,用戏腔问道:“二人可已远去?”“斜眼儿”双手垂立,答道:“回水圣使,俱已远去。”水圣使放下架势,恢复正常腔调,道:“这御妹也忒过了,为了让莫老五对她情有独钟,竟然把我等招至此地,着实演了一场。不过,还算过瘾!”“斜眼儿”扭了扭脖子,道:“御妹的手真重,把我摔了几个跟头,险些折了脖子。”
原来,辛怜让水圣使带着圣士演了这么一出好戏,还故意把手臂弄伤……
莫老五自然不知辛怜导演了这场闹剧,正与她同乘“雪花豹”走向子午谷出口,辛怜的小红马跟在后面。因顾及辛怜伤势,莫老五不忍颠簸,信马由缰,慢慢行走。辛怜趁势依偎着莫老五,小鸟依人,幸福无比。
莫老五道:“御妹,在去孤竹国救治道长的路上,你神神秘秘就是为了我吗?”辛怜嘻嘻一笑,道:“不错。”莫老五喝道:“你为何羞辱七儿?”辛怜倚仗着有相救之功,仰脸瞧着莫老五,甚是娇嗔,嘟嘟着小嘴嗲声嗲气说道:“夫君,不生气好么?”莫老五叹了一下,道:“七儿身世甚是可怜……”辛怜道:“同情不等于感情,值得同情的人多了,而感情却是惟一的,不允许别人染指。”莫老五道:“这就是你赶走七儿的理由?”辛怜道:“爱不需要理由!”莫老五不想与她争辩,苦笑一下,道:“御妹年纪轻轻,却有如此高论。”辛怜闪着大眼睛问道:“你是夸我还是骂我?”
莫老五没再说话,又走了一顿饭工夫,子午谷出口已遥遥在望。
这时,耳听一声巨响,地上突然弹起道道木桩,木桩上钉满铁刺,犹如一道带刺的高墙挡住去路。“雪花豹”嘶鸣一声,前蹄高高抬起,原地打旋。辛怜尖叫一嗓,惊魂未定,两面山头传出阵阵雷声,只见如碾盘大小的巨石夹杂着滚木,轰鸣而来。那晚辛怜听见富泰和大贵说到“子午谷”时,灵机一动,便想在子午谷演一场戏,却没想到子午谷真的会有埋伏。顷刻之间,二人就会被滚木雷石压成肉饼,辛怜脑子一片空白……
莫老五经历无数战阵,但置身这等凶险之地却是第一次。不过这等战法莫老五再熟悉不过,先用绊马桩拦路,滚木雷石随即飞落,既不叫阵也不对骂,甚至不给对方任何思考时间,杀机突现。这种战法以往为莫老五所惯用,曾让不少王师兵将命赴黄泉,没想到今日自己置身此境,不用说这一定是曾跟随他征战多年的隶人弟兄所为。
急遽之下,莫老五抱住辛怜借马背之力飞向半空,这时木石滚滚而至,莫老五轻点滚木再次弹起,朝山头飙去。经过几次借力弹跳,莫老五终于立于山头之上,回头再看时,“雪花豹”已腾空而起,跃过道道木桩。而辛怜所乘的小红马不及哀鸣一声,被挤压在乱石断木之中,肚暴肠流……
趁莫老五立足未稳,一个矮胖子挺枪便刺。莫老五微微侧身,长枪贴身而过。不容那人回抽,莫老五一把揪住长枪,起脚将他踢入山谷。
山头上约有三百多人,确是祝融国的兵士。莫老五怒极,转瞬之间杀死二十多人。有人叫道:“大将军且住!”一个看似头目的人慌忙跑到莫老五面前,跪倒在地,众人都跟着跪了,那头目说道:“我等不知截杀的是大将军,请恕罪!”
见这些弟兄个个满脸无辜,莫老五压了压心头怒火,道:“怎样?”
那头目说道:“我等奉命截杀叛贼,没想到竟是大将军。”
莫老五道:“你奉何人之命?”那头目往谷底指了,道:“就是适才被大将军踢死那人。”只见那矮胖子躺在小红马附近,龇牙咧嘴,死状可怖,莫老五道:“是谁给他下的令?”那头目说道:“不知。”莫老五喝道:“你不说?”那头目道:“大将军,杀了小弟也是不知。”
莫老五信了,以往他也是逐级传令,那矮胖子既死,背后指使者便再难查出。况且,指使者谋划得定然十分机密,就算此时回去彻查,一时之间也未必能查得清楚。莫老五想到辛怜说富泰欲对他不利,顿时心乱如麻,若果真是富泰所为,那么富泰便成了推施“盛世之法”的绊脚石,就必须搬开。不过毕竟无据,又是手足弟兄,莫老五轻叹一口,说道:“弟兄们,本大将军推施‘盛世之法’,你等可愿意?”众人齐声答道:“愿意!”莫老五又道:“不做新贵,自食其力,你等可有怨言?”众人答道:“没有!”
那头目跪前一步,道:“大将军,小弟如实相告,昔日的弟兄们有的愿意做新贵,不劳而获,作威作福;有的赞同大将军的‘盛世之法’,愿意跟随大将军,拼出一个太平盛世,让天下隶人都不再做牛做马。”
莫老五十分动情,道:“本大将军坚信,多数弟兄都会有这等境界。”冲众人说道:“弟兄们,造反会死人,推施‘盛世之法’同样也会死人。如果本大将军的死,能换取‘盛世之法’的顺利推施,本大将军立死无憾!请你等将本大将军的这番话广为传播,吓死那些阴毒小人!”
众人听得热血沸腾,说道:“遵大将军令!”
莫老五怀抱辛怜飞身上了“雪花豹”,朝谷口奔去……
待莫老五二人去远,从另一侧的山头上探出两个脑袋,正是富泰和大贵。大贵道:“竟让他逃去了。”富泰道:“实施第二计划,暗杀!”大贵道:“若再次失手,就会被大将军顺藤摸瓜查出你我,那两个杀手行吗?”
富泰阴阴一笑,道:“一个是神箭手,一个是施毒高手,放心吧!”
且说帝辛等人随华士登上蓬莱岛。
天空清透,树林静谧,小路悠长。众人沿着崎岖小路走去,来到一个山洞前。华士道:“请陛下随我进去。”说罢钻进山洞。洞里黑咕隆咚,从里面吹出股股冷风,帝辛迟疑一下,跟着钻了进去。攸喜、满仓正要往里进,从洞里闪出两个魁梧武士,手持短刀,面无表情,道:“只允陛下一人进。”
攸喜喝道:“找死!”
攸喜、满仓一抓一拉,拧身一甩,两个武士惨叫一声,一个扑倒在地,一个飞向半空。攸喜“哼”了一声,正要进洞,这时又出现了四个高大魁梧的武士。攸喜指指四人,道:“滚!”四人并不搭话,拉开架势。攸喜腾空而起,双脚连环踢出,四人倒地。接着闪出八个武士,仍是身材魁梧,目无表情。攸喜冷笑一下,只用了几招便将对方尽数击倒。
这时闪出十六个武士,与先前被打倒的武士身高打扮几乎一模一样,打斗招式也差不多。攸喜、满仓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应战。只是打倒一批又来一批,每一批都是上一批的二倍,数量倒也很好计算。
眼前出现六十四个武士,攸喜禁不住往里张望一下,真不知里面藏了多少人,纵是攸喜武功再高,也架不住武士的成倍增加。攸喜收住架势,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本将军只是对陛下放心不下,能否让我进去?”
一个武士搭了话,还是重复原来的那句:“只允陛下一人进。”
攸喜、满仓等人再不搭话,同众武士打到一处……
帝辛随华士进了山洞,并不知洞口在打斗。脚步“沙沙”,二人走了好一阵子,忽然飘来阵阵花香,沁人心脾。只有百花怒放才有这等袭人香气,时下已是初冬,哪里来得百花齐放?帝辛四下打探,因光线昏暗,四周景物看不甚清,只闻偶尔传来的叮咚泉声。
华士看出他的疑惑,道:“陛下,这是仙人洞,花草繁茂,冬暖夏凉。”
耳听有人轻咳一下,因洞中回音,咳嗽之声环绕耳际,帝辛惊道:“谁?”那人嘿嘿笑了,十分诡异,让人毛骨悚然。帝辛道:“可是狂谲?”耳听有人说道:“陛下,请往前看。”
面前是一道石壁,高及洞顶,漆黑阴森。帝辛将目光从上往下移动,当移到正中时,不由倒抽一口冷气。虽然光线昏暗,但帝辛还是看得真真切切,石壁内镶嵌着一颗白发白眉白须的人头,嘴巴张张合合。帝辛根根寒毛直竖起来,身不由己退了两步,睁大惊恐之目,盯住这颗人头。
那人嘿嘿笑了,道:“草民正是狂谲,没吓着陛下吧?”喊了一声“掌灯”。
一霎时亮起无数火把,亮如白昼。只见洞天高阔,寂静幽雅。洞府内有一个不小的湖泊,湖面如镜,清澈见底。湖泊四周长满怒放之花,姹紫嫣红,美不胜收。光照静水,水映火光,让人满目辉煌。火把沿洞壁布列,每个火把下站着一位武士,总有两百多人,雄赳赳气昂昂凛然莫犯。
面前这道巨大的石壁,中间挖去一块,一位白发白眉白须的老者盘膝坐于其内。此人面色青灰,身着青袍,盘膝垂手,毫无生机。帝辛恍然大悟,原来黑暗中狂谲因着青衣,只能显出一颗头颅,难怪让人发瘆。
狂谲朝武士挥挥手,众人鱼贯退去,步履轻盈,无声无息。狂谲朝帝辛抱拳躬身,说道:“陛下,草民下肢已残,不能恭行大礼,请勿怪罪。”帝辛回着礼说道:“无妨。”狂谲指指旁侧的一个石墩,道:“请陛下屈尊一坐。”帝辛坐了,说道:“人说狂谲、华士兄弟乃当世大贤,没想到隐居仙岛,深居仙洞,倒似仙人。”狂谲笑道:“陛下只知草民本名狂谲,却不知草民还有绰号,人称‘墨鲨’。”
帝辛惊得脱口而出:“原来你就是‘墨鲨’!”
墨鲨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名满天下,武功与北熊齐名,乃是武林至尊高手。
帝辛道:“墨鲨闻名遐迩,只是鲜有现身,只是你的脸……”
多年前,有一次墨鲨在大洋深处猎取鲨鱼,与一头千年巨章不期而遇。那章鱼展臂时足有百步长短,膂力惊人。墨鲨无法躲避,便在水下与它搏斗。最后章鱼被斩去数臂,逃之夭夭,逃跑时放出乌液。因被乌液浸泡,墨鲨变得脸色灰暗,脸皮僵硬。
章鱼生性好斗,善于变色伪装,现代研究发现章鱼还有复杂的听觉、嗅觉和视觉神经。有的章鱼分泌出的乌液具有毒素,能够麻痹人或动物的感觉器官,甚至危及人的生命。
墨鲨道:“草民因长年在大洋猎鲨,又长有这等面皮,才被人称为‘墨鲨’。”
帝辛点点头,问道:“你用的雕翎箭因何要与众不同?”墨鲨道:“在海里,普通的青铜箭镞极易锈损,飞禽羽毛被水浸湿,射之便不精准,所以草民所用之箭乃钢头鳞尾。”帝辛又问:“猎鲨只为造舟?”墨鲨道:“是。”帝辛道:“造下这么多鲨舟,此举不可理喻,其中定有缘由。”
墨鲨一字一句地道:“因为殷商要亡了!”
帝辛面带愠色,道:“老人家何出此言?”
墨鲨道:“陛下治下之万民,可粗分为三大群类,即隶主贵族、平民和隶人。”墨鲨当时所说的群类,就是后来所说的“阶级”,即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不同的阶级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在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墨鲨道:“先说隶主贵族。隶主贵族犹如殷商大厦之根基,然而时下已离心离德。朝廷用贵族充作“人牲”“人殉”,致使贵族人人自危;擅杀朝臣,文臣武将朝不保夕,人心惶惶;陛下恩准莫老五推施‘盛世之法’,隶人逃亡成风,致使大量良田无人耕种,贵族怨声载道;加封隶人官职,危及贵族利益。”
这些都是实情,帝辛并未辩驳,耳听墨鲨继续说道:“再说平民。平民介于隶主贵族和隶人之间,多为工匠艺匠技者医者,犹如殷商大厦之砖瓦,然而时下民怨沸腾。造鹿台扩宫院建离宫修官道,除了驱用隶人,还征用大量平民,工程之大早已超过国力民力所承受,陛下加收田赋,最终又都落到平民身上。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平民鬻儿卖女,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