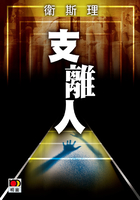水圣使合掌笑道:“正是。”土行孙呵呵笑道:“我说水圣使,你的圣主怎么爱做白日梦?你来索取《周易》,也不看看你爷爷的脸色。”水圣使冲土行孙脸上瞧了瞧,道:“你的脸庞宽大,眼小鼻塌,奇丑无比,有什么好看的?”土行孙道:“难看是吧?这就对了!爷爷的脸色不好看,你还能取走《周易》?”水圣使奇道:“此话又怎讲?西伯侯辛辛苦苦作此经书,不正是想让其广为流传么?”极其大度地朝前一指,道:“本圣使早已在此搭建了房屋,吃喝一应俱有,请西伯侯安居于内,何时默出经书何时上路。”
众人望去,果然不远处有两座草屋。
土行孙道:“水圣使,你是不是在发烧?”水圣使一时未解,答道:“没,没烧。”土行孙道:“那怎么说起胡话来了?你要打得过我,自然可以考虑给你《周易》,你要打不过我,你现在就得滚了。”水圣使道:“本圣使早就料到你等不会轻易答应,比武定夺!”蒙秋道:“说了半天,不还得打嘛?”水圣使道:“我是来求经的,不是来打架的,伤了和气,反倒不美。”蒙秋道:“不打又怎能分出高下?”
水圣使忽然变成戏曲腔调,道:“锵锵锵,真乃匹夫之勇!不用厮杀,同样能分出输赢。”面朝姬昌说道:“西伯侯,如果你等输了,是否肯以《周易》相赠?”姬昌道:“自然。如果你输了,该当如何?”水圣使道:“自然是让道。比试三场,三打两胜,怎样?”
土行孙来了兴趣,道:“一言为定!”
水圣使道:“蒙秋既然有举鼎之力,我二人就比试膂力。”手指山坡上的一块巨石,道:“蒙秋,你把它搬下来。”蒙秋道:“这有何难。”走过去抱住巨石,喝喊一嗓,一步一步搬到众人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巨石落地时,发出一声闷响,击起尘土飞溅。
土行孙见水圣使生得瘦弱,个头不及蒙秋前胸,围着他转了半圈,道:“认输吧。”水圣使道:“我把此石扔上去,蒙秋可认输?”蒙秋道:“我是搬下来的,你若能扔上去,我自然认输。”水圣使道:“好!”抱起巨石,一声吼叫,巨石飞回原地。
众圣士交替发出喝彩声和鼓掌声,极有节奏,显然也经过严格训练。
姬昌等人看得两眼发直,待水圣使用劲拍拍手上的尘土,众人才回过神来。
土行孙心道:“水圣使定是只有膂力,论灵巧未必能胜我。”想到此问水圣使:“第二场比什么。”水圣使往上一指,用戏中腔调说道:“树梢之上,秋果未落,我二人谁先抓于手中,谁是赢家,不过谁也不准使用兵器。”
一句话正中下怀!土行孙斜着眼睛看了,果然有一颗松果独挂树梢,早已胜算在握,道:“听我口令,一二三!”这“三”字刚喊出口,土行孙平地起跳,身如离弦之箭,朝松果飙去。忽觉身旁闪过一道黑影,土行孙大惊,心想这人轻功不在我之下。心念乍闪,只见水圣使高举手臂,已然越过,不过其腋窝正好露在土行孙脸前。此刻不用多想,土行孙朝他腋窝轻轻挠去。水圣使毫无防备,痒痒肉被挠个正着,不由得“扑哧”一笑,丹田之气立刻散尽,“咕咚”一下屁股着地。
土行孙稳稳落于水圣使面前,摊开手掌,正有一颗松果。土行孙学着他的腔调,笑着说道:“我赢了!”水圣使坐于地上,一直懵懵懂懂,喝道:“你使诈!”土行孙道:“谁先抓下松果便是赢,可没说不许使诈。”又故意说道:“你若不服,这一场不算,重来。”
闳夭同姬昌相视一笑,其实他二人并未看清土行孙使了什么手段,但可以肯定土行孙一定耍弄了什么。
水圣使道:“堂堂圣道圣使,怎能言而无信?好!一胜一负,第三场……”
土行孙道:“且慢!前两场比试什么都由你说,第三场该由我说了。”围着水圣使的那匹瘦马转了转,道:“第三场赛马!”水圣使惊道:“要跟‘瘦狗’比?”土行孙面色讶异,问道:“你的马真叫‘瘦狗’?”水圣使道:“是。”土行孙大笑,笑得极其夸张。
蒙秋选了一匹高头大马,道:“让我来比!”土行孙道:“一边儿去!”不由分说跳到马背上,往山谷深处一指,道:“那儿有棵大树,绕过大树转头,谁先回来谁赢。”一抖缰绳,飞马而去。水圣使跨上“瘦狗”,一拍马屁股,叫道:“锵锵锵!呼呼嘿嘿,走也!”“瘦狗”得令,倒腾着四条短腿猛跑。远远望去,水圣使的脑袋上下窜动,甚是滑稽。众圣士声调一致齐声助威,锣鼓笙箫按节奏发声,赛马场面倒也热闹。
只见高头大马风驰电挚般跑到大树旁,嘶鸣一声,四蹄离地,回奔时依然一路烟尘。“瘦狗”跑得张嘴吐舌,愈加像狗。眼看土行孙就要赢得比赛,这时水圣使往“瘦狗”头上轻轻摸了一下,“瘦狗”发出一声闷吼,如同猛虎咆哮。土行孙跨下之马惊叫一声,屁滚尿流,四腿松软,“呼哧呼哧”大喘粗气,再也迈步不得。原来,“瘦狗”是一匹变种野马,生长在深山老林。因山林之中多野兽,此马为了自保,练就这套本领。马听到“瘦狗”的吼声,都会惊悚瘫软,土行孙哪会知晓此节。
直到“瘦狗”立于姬昌面前,那匹高头大马才怯怯走来。
水圣使冲姬昌连连拱手,笑声朗朗,道:“承让承让。”
众圣士喝彩之声更甚,水圣使朝众人一摆手,声音戛然而止。
土行孙叫道:“不算!你这‘瘦狗’使诈。”
水圣使道:“适才你不也使诈了?我等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丈夫一言,‘瘦狗’难追。”
姬昌道:“你赢了。”迈步走向草屋。
水圣使命圣士将草屋围了个水泄不通,席地坐于屋里,目不转睛盯着姬昌。姬昌坐于案几前,案几上摆放着竹卷刀具等。闳夭指指天指指地,姬昌会意一笑。半日工夫,《周易》刻就。
水圣使急不可待,一把抢过,迅速打开,“周易”二字赫然入目,接下来洋洋洒洒,密密麻麻,确是一部《周易》!水圣使心花怒放,高声令道:“锵锵锵,孩儿们动手了!”众圣士诺应一声,张弓搭箭,对准姬昌等人。水圣使道:“《周易》既已到手,留下你等性命何用?”
闳夭道:“你怎能出尔反尔?”
姬昌笑了笑,道:“水圣使,你仔细看看,可是一部完整《周易》?”水圣使惊道:“怎么?”慌忙展开,“周易”二字开篇,接下来刻着“乾卦”,水圣使问道:“这不就是《周易》么?”姬昌道:“实不相瞒,《周易》有八八六十四卦,这里只是乾坤两卦的卦辞。”原来,适才闳夭指天指地就是乾和坤的意思。
虽然密密麻麻,但都是乾坤两卦的重复,水圣使登时头脑晕胀,喝道:“你使诈,找死?”
闳夭笑道:“休怪我等,是你出尔反尔在先。况且,先前你说要《周易》,可没说要《周易》的几段文字。”水圣使气急败坏,咬着牙说道:“不交出《周易》,今日谁也休想活着走出坨坨岭!”闳夭道:“好啊,我等死了,你找谁要《周易》去?你的圣主就只好摘下你的人头了。”水圣使颤巍巍指指闳夭,又指指姬昌,再指指蒙秋和土行孙,道:“本圣使宁可人头被摘,也要出这口恶气。孩儿们,动手!”
蒙秋昂然说道:“谁敢动!”
姬昌道:“水圣使,我来问你。”水圣使已气得鼻眼错位,喝道:“没啥好说的,杀!”姬昌一字一句地道:“伯昌岂是贪生惧死之人!若你为一人之忿,坏了你的圣道‘大业’,这账该如何算之?”水圣使激灵灵一颤,醍醐灌顶,道:“这话倒也不错,不过……”姬昌又道:“你将乾坤两卦先交与你的圣主,如果你的圣主还想要,日后再给。伯昌决不食言,你看如何?”
不管怎样已有两卦在手,水圣使想了想,道:“也罢!日后如你胆敢耍弄计谋,休怪本圣使无情。”说罢以手礼让,请姬昌等人上路。
闳夭走过他面前时说道:“下次你可不能再出尔反尔了。”
水圣使百口难辩,满脸涨红,再也不顾拿捏戏中的腔调和动作了。
过了坨坨岭,进入冀州地界。
这日天色将晚,姬昌等人投宿在一个集镇的客栈内。过了半夜,一个黑影在姬昌的窗外鬼鬼祟祟张望。这人身着夜行衣,黑布遮面,个头不足三尺,上身奇长下身奇短,张望一回,向西疾去。天刚拂晓,一声尖叫“杀人了”划破黎明寂静,让人毛骨悚然。
姬昌忙披衣下床,隔窗张望。土行孙打个呵气,说道:“杀人也不挑个时候,爷爷睡得正香呢。”蒙秋道:“都死人了,你还玩笑。”闳夭道:“蒙秋在此守护,我与土行孙去看看。”
杀人现场就在客栈西侧,茅屋前已围了不少人,一个老妇人坐在门槛上哭哭啼啼。土行孙道:“让开!”众人闪开一条道,土行孙、闳夭急步进屋,只见死者是一个上了年岁的老翁,仰面朝上,头颅破碎。闳夭问那老妇人:“可看到恶贼的模样?”那老妇人道:“没看到,我睡得朦胧,睁眼看时,人已被害多时了。”早有人报了官府,官府差人来到。闳夭、土行孙回到客栈,将杀人之事说了一遍。姬昌道:“此事自有官府公断,我等继续赶路吧。”
众人行得一天,投宿于一个集镇客栈。拂晓时分,一个凄厉叫声传来:“杀人了!”姬昌赶忙披衣而起,闳夭道:“我去看看。”同土行孙一起去了。不多时,二人转了回来。闳夭愤愤说道:“一个少妇在半夜被杀,头颅破碎,与那老丈的死法毫无二致,定是同一恶贼所为。”蒙秋恨恨地道:“鼠辈,别让俺撞见!”土行孙笑道:“别瞎操心了,操心也挡不住明天杀人。”蒙秋心无机巧,懵懂问道:“明天那恶贼还会杀人?”土行孙懒洋洋答道:“或许吧。”说完躺到床上,蒙头睡去。
果真如土行孙所言,次日在姬昌投宿的村镇上,黎明时分又有一孩童被害。
闳夭面色阴沉,道:“我等行得三日,恶贼杀了三人,均在我等投宿之地,难道……”姬昌接道:“不错,恶贼是冲着伯昌来的。”众色凛然,闳夭对土行孙道:“今夜你守在内侧,不可离开西伯半步,我和蒙秋守在门口。”土行孙斜睨闳夭,道:“有俺土行孙在此,恶贼怎敢前来送死?”闳夭喝道:“不可大意!”
当夜,三更已过,月色朦胧。
闳夭、蒙秋藏身于院内角落,蒙秋轻声问道:“那恶贼既然是冲着西伯来的,为何屡屡杀害无辜?”闳夭道:“一时我也想不明白。”言犹未了,忽然“嘘”了一下,用手指指。蒙秋随其手指方向望去,只见在距离客栈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四处张望。原来,这个客栈是集镇的最高之处,居高临下,那人被看了个正着。见那人身着夜行衣,用黑布遮了半截脸,蒙秋道:“定是恶贼无疑,真想一棍闷死他!”闳夭拉拉他的衣角,道:“悄悄跟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手。”蒙秋朝姬昌的房间瞧了,有些放心不下。闳夭道:“只要我二人紧盯恶贼,他就没有机会对西伯动手,再说还有土行孙在此。”
二人再没说话,朝那夜行人悄然欺去。
那夜行人好像在有意摆弄身手,时走时停,时潜时行。闳夭和蒙秋担心被对方发现,也不敢太过靠近。围集镇转了半圈,那夜行人看看天色,朝一个院落疾去。闳夭知他要动手了,忙同蒙秋使了眼色,二人靠了上去。那夜行人只顾专心挑选人家,竟未发觉身后有异。闳夭、蒙秋面色顿变,只见那人装束打扮和身形步伐酷似土行孙!不及细想,只见那人已翻墙入院,二人忙欺到院落门口,那人已在挑拨门闩。闳夭冲蒙秋点点头,蒙秋轻轻端开柴门。那人闪进屋去,蒙秋大喝一声:“住手!”就在这时,屋里传出一声惨叫。
蒙秋箭步逼到门口,喝道:“滚出来!”
那人没想到会被人堵住,慌乱之中冲将出来,正与蒙秋打了个照面。蒙秋舞棍便拍,那人竟不躲闪,一摆手中的“无情锏”,朝蒙秋的“天突穴”刺去。这手法蒙秋再熟悉不过,正是土行孙惯用招式!蒙秋搁开无情锏,就地一划,浑天棍朝他双腿扫去。那人身轻如燕,跃至半空翻了一个跟头,随后身与锏急速旋转,在蒙秋头顶盘旋着压了下来。值此极度恼恨之时,蒙秋并不回护,大叫一声,挥棒便砸,这架势再明白不过,非要与他同归于尽不可!那人尚在半空,已无法变招,只得在浑天棍划过的瞬间,单足轻轻在棍尖上一点,借力前翻,着地时又一连翻了两个跟头,站起身来,这时恰好站在闳夭对面,相距不过尺许。
闳夭怒火乱撞,顺手一扯,喝道:“露出脸来!”一把扯去他的面罩。闳夭的动作突如其来,那人愕在当地。暴露出来的这张面孔,大头大脸黄胡须,小鼻小眼小芝麻牙。闳夭吼道:“土行孙,果然是你!兔孙子……”掴去一个大耳刮,正中土行孙的大脸,结结实实,清脆响亮。土行孙抬手点出无情锏,刺中闳夭肩头,随后缩肩收臀从蒙秋胯下滚出,飞身上了房顶,眨眼之间踪影已无。闳夭手捂肩头,朝土行孙远去的方向叫骂:“兔孙子,丧尽天良!”
这时,从屋里跑出来一个老者,喊道:“杀人了!”
蒙秋道:“老人家,都怪我等来迟,让恶贼得了手。”老者一把揪住蒙秋,声嘶力竭叫道:“你就是恶贼!”因亲人突遭杀害,老者惊惧之下出门即遇蒙秋,便认定蒙秋就是恶贼。蒙秋道:“我不是恶贼。”老者双手捉得更加紧了,怒吼一声:“你是!”闳夭道:“老人家别误会,你看我的肩头,正是与那恶贼打斗时受的伤。”老者怔怔看了,见闳夭肩头汩汩冒血,这才信了,一跺脚,哀声叫道:“我那老伴……噫唏!遭天杀的……”因极度哀痛,欲哭无泪,突然逼视闳夭,叫道:“你可认得那恶贼?”
闳夭面色尴尬,诺诺道:“我……怎会认得。”
老者的叫声惊动乡邻,来了不少人。有人道:“老人家,快去看看人还有救么?”老者转身跑去,只跑出两步,一拍大腿,嚎道:“头都碎了,哪里还有救?”这才惊天动地哀号起来。
闳夭、蒙秋自觉无趣,悄身退去。
这时天已破晓,姬昌早被叫声惊起,披衣下床,正往屋外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