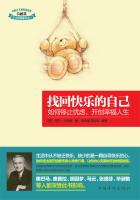段祺瑞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加强对大总统的正面宣传。比如他当年在朝鲜的机智脱险,比如他多年练兵的成就,比如士兵每天必唱国歌“卿云灿兮”,比如他让清廷体面逊位;二是要认清乱党嘴脸。去帝制帝制已去,谋共和共和已成。全国上下,都应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去年宋教仁遇刺,大总统深感痛惜,已经批示彻查,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他们却执意叛乱。不惜毁坏公器,逞一时之快,泄一己之愤,岂能容忍。
说到底,就是要求《河南民报》与政府保持一致。
回家路上的李玉亭,依旧心情愉快。飞机造成的惊惧已去,此刻他脑海里只留下总长的亲民与干练。陆军总长兼河南督军,毫无疑问是一品大员,却肯亲手拉他起来,这情分与面子岂能了得?国家有这等人才可资倚重,那还怕什么。
然而回到家里,等待他的却是坏消息:上午飞机低飞经过,噪音很大。正在窗户跟前晒太阳的柳媚,受到前所未有的惊吓,胎动剧烈,终于早产,男婴不到五斤重。若非寨子里有现成的产婆,只恐性命难保。
段祺瑞抵申前一日,政府恰巧出台一项新政策,与李玉亭的生计密切相关。只因时效的缘故,迟于总长抵达:袁大总统颁布《国币条例》,决定整顿币制,重新铸造银元。一元面值的每块总重七钱二分,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上带嘉禾年号以及袁的头像,所谓“袁大头”。这个消息促使李玉亭彻底停掉化铸银两的业务。他开炉房时,银两其实高潮已过,开始走下坡路,龙洋鹰洋依次登场。侥幸的他就像个散户,莫名其妙地赶上了最后一波反弹,赚了一笔傻钱。但自从辛亥年起,化铸银两的生意越来越淡。拖到今天,也只有停掉。
长子两岁生日那天早晨,李玉亭赶到钱店,要亲手化铸最后一只整宝。主顾是事先说好的,但整宝还是得仔细相看。纯银色白,次者发青,下者色灰。李玉亭虽不敢说老于此道,但十年下来,多少也有了点眼力,尽管尚不能与赵明远比肩。他拿在手中,先朝外一摆,对光看看成色,然后再搁到跟前,仔细摩挲宝脸——整宝周围翘边,中间凸起的部分,是为宝脸——用心端详。
的确是上等成色的好银子。李玉亭微微点头,随手交给伙计拿去砍宝。这是落幕之作,伙计已在脑海中演习多次,因而动作比往常更加熟练,更有仪式感。右手将整宝放进大夹剪,似乎手尚未抬起,屁股已经坐下。在此期间,上身保持不动,就像跳国标交谊舞。此间若有歪斜,师傅非打即骂。
咔嚓一声,整宝破开。那个瞬间,李玉亭暗自许愿:如果的确成色上好,那就说明长子次子均能逢凶化吉,一切平安。如果稍有掺杂——那就不说了吧。还好,师傅接过整宝,仔细看过,虽然眉眼间表示认同,但嘴上却不肯说,也不能说。这也是行规。前来兑换的银子,你得使劲挑毛病才行。不用他们开口,李玉亭已经放下心来。等项克敏过完秤,他便着手化铸元宝。这是他给两个儿子的礼物。可怜他们一个天生有反骨,一个生来不足月。
炉火通红,银水沸腾,李玉亭来不及感慨。因为不欲流通,故而不再打猛子,否则他还真不行。但是打硝他早已出师。打好硝倒进银槽,左一摆右一摆印成双翅,再一转,中心的螺纹随即成型。
这只留给未来的整宝,连同先前备好的九只,按照规矩装进银鞘。那是新鲜杨柳截成的木头,中间掏出槽,放进银子后用铁条箍拢。照理不入藩库不必如此,但这批例外。在此之前,有个瞎眼的方士在钱店外盘桓不去,口出狂言。盲精哑毒,对于这种人,李玉亭向来礼遇看重,这次也不例外。经过好茶好酒的铺垫,他获得了一个禳解之法:宅内埋下十锭银子,用它们押住两个孩子的命直到成年,如此可保无虞。
李家那个可怜的早产儿究竟能否成活,大家心里许久没有把握。那年月,婴儿夭折实在算不上个事儿。究竟是把他们托付给信义医院还是胡泰运,李玉亭的思想斗争颇为激烈。信义医院方面照顾母婴的确很在行,但胡泰运毕竟行走信阳多年。他毫不客气地说:“玉亭兄,你要交给他们我也不反对,但是找他们就不要找我,找我就不要找他们。”李玉亭故意笑道:“汉贼不两立?”胡泰运一边捋袖子一边说:“亲兄弟明算账,丑话说在前头好些。”也难怪他如此激烈,因政府刚刚决定,将中医从国家医学教育体系中剔除。中医开设的只能叫诊所,不能称医院。如此被人强压一头,地头蛇怎能心服。
左思右想,还是选择了石膏大王。反正已无急症,只是日常调养。那段时间,李玉亭把生意完全托付给夏先生和项克敏,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不能化铸银子,生意的乐趣已无,不过是生计而已。而传宗接代的任务,远比生意艰巨。
忽一日,刘景向上山劝驾。此时他已不再经理《河南民报》,报馆已经关张。尽管段祺瑞曾经寄予厚望,但这份报纸自从上市始终未曾盈利。说到底还是信阳城小,报纸发行量不够,因而成本太高。中国最初的报纸是宫门抄,由内阁发行,主要内容是官员升迁调转消息,以及谕旨奏折。因有信息需求推动,后来东华门外出现白本报房,在白纸上小楷誊写宫门抄投递给订户,报费是一两二钱银子。对于普通人家,这价格未免昂贵,于是黄本报房又应运而生:采用活字印刷,仅需二钱银子。如果只要上谕部分,二十枚大子即可。
这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上海成熟报纸的价格,大体是十个铜板。过路广告费每字五枚大子。五六千份的发行量外加广告收入,自能盈利。《河南民报》发行主要仰仗信阳本地,周边辐射能力不够,订户从未突破五百,广告又少,每份成本几乎要到五厘银子。初期的亏损在意料之中,但他们俩都没想到,亏损期会如此之长,直到突破刘景向的极限。正巧新任县知事翟春昭要办劝学所,力邀他回归本行,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刘景向带来两个消息:世界大战爆发,撵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无处奔逃的国家,所谓八个犯边小鬼,多数卷入其中。这是春秋无义战,对中国理当没有坏处;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明年将在旧金山举办万国博览会,政府决定参加。刘景向建议李玉亭选择上好的鸡公山毛尖茶,前往参展。
怪不得当年旱灾严重。从信阳往南,东双河、谭家河相继枯水,李家寨前的九曲河虽未断流,但已经浅得藏不住鱼虾。天气大旱,二麦不登,米价涨到每斤八十文,饿殍不断。李玉亭一直没闹明白怎么回事,闻听爆发世界大战,这才恍然大悟。天象世象,亘古同理,自当有所照应。既然应在洋人身上,那就意味着信阳与李家寨可以暂时放心。
万国博览会一事,县署已经通知商会。参展与否,李玉亭尚未决定。他估计刘景向此来与赈灾有关,便主动表示,愿以儿子的名义施棺百口。李家是大户,行善施德义不容辞。宗祠除外,还办有义田会、义学会、水利会、维安会与节爱堂。维安会负责冬防,节爱堂负责施舍棺材医药。虽都号称举全村之力,但主要仰赖李家。有此基础,每遇灾年根据庄稼长势看青让课,施粥放赈,已成惯例。而今喜添贵子,只能增加,岂可减少。
然而刘景向依旧微笑摇头。他要李玉亭速速命驾进城,知事大人有请。
县知事翟春昭邀请头面人物齐聚县衙,的确有赈灾的考虑。遭此大旱,省里仅仅抚恤四千五百元,可谓杯水车薪。不过他找李玉亭还有别的事情。政府筹建信阳到浦口的铁路,因资金不足,决定官商合办。官方鼓励民资进入,但沿途各地绅商普遍反应冷淡。
翟春昭说:“此事实为难得商机,利国利己,造福桑梓。不过信阳本地绅商均无热情。他们思想保守,我并不意外。玉亭兄向来敢为风气之先,想来不会坐视?”
修铁路可比西餐新奇,比钱店风光,比报纸实在。李玉亭不觉眼前一亮。门前南来北往的火车,似乎又在耳边呼啸。他仿佛站在火车头上,胸前披着红色的绶带,上书“敢为风气之先”六字。风振衣袖,猎猎作响,沿途人如潮涌。那感觉比杠上开花自揭一条龙更加舒坦,革命时代嘛。他可不想坐在头排眼睁睁地看着重大历史发生,自己却不参与剧情。那不是他的性格。
虽然钱店的生意兴隆,但老板的兴趣却大不如前。那一炉红火的情景不再,李玉亭颇为失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化铸银子的愉悦,来自于掌控感。下通儿时和尿泥,上接治国平天下。所有这些,都是意愿得以施行的愉悦。当你看见成品诞生,自然会心有所动。无论那成品是只成色上等的整宝,还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