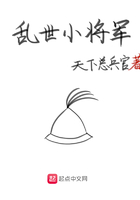刘秀:“我汉朝虽大,但向来以礼待人,尤其是尔等邻邦,更是如春风吹拂,无微不至。”
使者:“大汉宽仁我国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才知千真万确。”
OK,就此打住。
以上对话虽说是自行编排出来的,但我相信,即便是时空倒流回到两千年前的洛阳大殿,日本使者所说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至少,有两个字是铁定不会变的——我国。
别说是刘秀了,就算在当年西汉,日本人跑乐浪来送贡品,又有哪个不是说“这三百条鱼干乃是我国今年献给大汉的礼物”之类的话呢?
这个很容易明白过来吧?如果今天我和你就我本人为话题聊天,那我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多半就是“我”。
那么,在当年的日本,“我国”二字中的“我”怎么说?
“我”,在古日语中,读わ(wa挖),后来的各种第一人称代词大多都是从这个单音字节上衍生而来的,比如相当着名的“我辈”,读作わがはい(wagahai哇嘎哈依);我们,读作われわれ(wareware挖列挖列)等等。
说白了,这个“倭”,其实就是“我”的意思。
只是那年头日本人没有文字,中国也没有精通日语的人才,所以从秦汉的时候开始,但凡和日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以为他们国家的名字就叫“我”国,于是便非常顺口地跟着读音,将其翻译成了“倭国”,然后再一代一代地把这个名字往下传。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实那会儿日本并无国名,所以当他们拿到金印之后,还以为是刘秀赐名呢,个个都挺兴高采烈的。
至于那个奴,那就是部落名,单纯的是一个发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汉朝之所以要用“奴”字来对应这个发音,其实也是出于一番好意。
奴,在那时候的中国,虽然的确有奴才奴隶的意思,但常常也作昵称,用于人的小名,比如南北朝时期齐废帝刘子业,小名就叫阿奴;在淝水之战中大出风头的谢安,也叫阿奴;此外还有古代中国帅哥的总代表潘安,叫作檀奴;人称战神的冉闵,叫作棘奴;书法大家王献之,叫作官奴。
总之在汉朝看来,这次前来拜访的这个日本奴部落是非常可爱的,至少在倭国数百个部落里,算是顶顶可爱的一个,于是,便根据其读音昵称他们为“奴”。如果放到今天,那基本就等同于“小而可爱的日本”这样的称呼。
话说在顺利受封且有了自己的国名同时还拿到金印之后,倭奴国的使者便踏上了回家的路途,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更别说是国事访问了,而且相当奇怪的是,不光是倭奴这一个部落,其余村庄的家伙们似乎跟商量好了似的也都绝了迹,反正在史书上是找不到有任何一个日本部落或是日本人跑中国来朝贡或是访问的记录。不过好在汉朝也无所谓,毕竟对方不过是个穿兽皮光脚丫、石器时代级别的邻邦,又何苦跟这种人计较呢?
就这样,日本人整整五十年没了音讯,一直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安帝的时候,他们再度来到了洛阳城。
说起来这帮人还真的挺奇怪的,一连半个世纪都不来一次,这次一来就来一大帮子,更要命的是,这回的倭国使节团不但人数众多,达两百多人,而且级别也相当高,领头带队的是倭奴国的新首领:帅升。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记录在案的有确切名字的日本人。虽然他的名字相当不靠谱。
在那个时代,日本既没文字也没姓氏系统,无论是高贵的国王还是普通的田间老农,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口头上的简单称呼,眼前的这个帅升也一样,仅仅是一个音译,根本无法确定其究竟姓甚名谁。
话说帅升到了洛阳之后,和他的前辈倭奴使者一样,受到了皇帝的亲自接见,汉安帝的心地还算宽仁,并没有问“你们怎么那么多年都不来”之类煞风景的话,只是跟走过场一样照例寒暄了几句,比如你们倭奴国近况如何啊,倭奴的鱼干带来了没有啊等等。
帅升则根据问题逐一回话,只不过在他口中,并不再出现“奴”这个字眼,而是很清楚明白地表示,自己是倭国的国王。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倭地奴国的村长,亦非其他什么毛国鸟国的部落首领,而是整个倭国的最高统治者。
乍看之下会给人一种帅升已经统一日本的感觉,但实际上这是错觉。当时的日本依然四分五裂,只不过比起多年前要好很多,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他们已经拥有了铁制武器,打起仗来也自然带劲儿了许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原本九州的一百多个部落互相吞并到了四五十个,眼瞅着就要化零为整,天下一统了。
在这残存的四五十个幸存者里,倭奴国赫然名列其中,而且还算是混得挺好的一个,据说是九州岛北部最有力的部落,而且看起来还很有前途,俨然一副欲将九州全境纳入囊中的架势。
尽管离完全掌控日本这个目标还有那么一段距离,但帅升依然对汉安帝自称倭国国王,这种自夸行为最大的原因是他想在汉朝那里确立自己的唯一性——我代表全倭,只有我才是你们大汉的小弟,除我和我方人员之外,皆为山寨产品。
这似乎有些说不通,毕竟你连着五十年都不曾来拜过一次码头,干吗这回心急火燎地带着那么大一帮子人来洛阳确立唯一性?要想说明白这个问题,那就得往上看几行,之前我曾经提过,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日本已经拥有了铁制的武器。
关键就在这儿。
五十年前,日本的兵器基本是以石器为主的,铁器虽然有,可真的很少;五十年后,尽管石器并未全部淘汰,但相当多的部落都能用上铁家伙了。
纵观人类那么多年的历史,绝大多数国家或是地区的发展趋势基本上都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然后再是铁器时代。但日本却是个特例,虽然是有过不少铜器,但这个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青铜时代,而是直接从石器时代发展到了铁器时代,同时这发展速度相当快,几乎可以用穿越二字来形容。
不要跟我说日本人天生聪明,自主研发了打铁技术,这种神话打死我都不会信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日本得到了外来技术的支援,在日本列岛的附近,存在着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将自己的各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了过去。
这说的显然还是中国。
尽管官方之间的交流次数的确不多,但中日两地的民间交流,却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中断。
比方说当时在九州岛北部非常流行支石墓,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由齐国那边给传过去的。
还有干栏式房屋,日本那里叫高床,这一看就知道是中国南方的特产,早在河姆渡时期中国人就会盖这玩意儿了,传到日本的时代虽然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在汉朝之前。
至于铁器的冶炼,那更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先进玩意儿,从各种出土的铁质文物来看,日本当时从炼铁炉的打造到炼铁的方法,无一不带有MadeinChina的烙印,可说是中国原装技术,日本组装生产。
不过要说从中国传往日本的各类东西中,对后世日本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铁器,而是稻种,就是你现在吃的那白花花的大米饭。
作为日本人数千年来饭桌上最重要的主食,稻米是在三四千年前从中国的长江下游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不过后来也有人认为起发点是在山东一带,同时也有考古学家证实,日本种植稻米的历史超过了六千年,但无论是从哪儿来还是来了多久,有一点却一直是铁板钉钉,不曾被推翻过,那就是日本的稻种确实由中国而来,毫无疑问。
不过,虽然这大米饭是自中国而来,但日本人显然要比中国人拥有更深的米饭情结。
在日本人看来,大米这玩意儿,是宝贝,是珍珠,甚至是舍利。这也难怪,那年头日本穷,基本没啥好东西吃,能够嗑上一顿大白米饭,那已经是很高级的享受了。
所以日本人异常珍惜米饭,小时候吃饭在碗里漏了米粒,这是任谁也难以避免的自然之事,要是在中国一般父母也就说两句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再让你吃了它,可在日本却不同,那里有一句从古流传代代通用的谚语:“浪费一粒米就要瞎一只眼。”
这句狠话时至今日都有老一辈的日本人在说。
而关于米饭的传说,在日本也不少见。
比方日本人自古便相信在每一俵大米中都住着七位神灵;再比方说大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日本全国通用的流通货币,而且相当过硬,在战国时代以及之后的江户时代,大米的产量乃是衡量一方诸侯强弱的重要标准。
今天日本人也依旧固守着要吃就吃自家所产的大米这一铁则,尽管物资匮乏,食物需要大量进口,可唯独大米的自给率却是百分之百。
总而言之,大米对于日本人而言非常重要,就算将其称为日本人灵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不为过。
话说回来,中国的存在,大大推进了日本的历史进程,也大大加速了日本的生产力。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至少对于帅升而言是这样的。如果全日本得到中国援助的只有他这一个部落,那该多好啊,这样一来他就能拿他的铁矛铁枪去戳人家的木棍石斧。
帅升的基本心态多半就是如此,所以他才会特地带团来到洛阳,向汉朝政府郑重声明一个倭国原则,主要是为了能够独占来自中华的各种先进技术和文明物产。
当然,求人不能空手来,这个亘古不变的定理帅升也非常明白,所以他此次到访洛阳,还特地带了一份厚礼——“生口”一百六十名。
当时日本所处的时代在学术上被称作弥生时代,虽然在各方面依旧原始,但也总算渐渐有了一些文明的曙光,至少在社会阶级方面,因受中国方面的多年熏陶影响,已经有了相当鲜明的层次分化。
在每一个部落里,最大的那个叫大王;大王下面设有百官,人称大夫;普通的老百姓叫下户;比下户更为下贱的叫生口,也就是奴隶。
奴隶的待遇在世界各国应该都差不多,尽管是人类,但也仅仅只是生理上而已,只要主人愿意,可以随时打杀抑或是当成礼物送给别人。
帅升之所以要送中国生口,多半是因为那会儿的日本实在太穷,既然自称是倭国国王如果再送人三百条鱼干那实在是挺不合适的,干脆,送人吧。
不过你可千万别小看人,要知道那会儿的日本地少人寡,一个部落的人口了不起也就数千,能干活打仗的精壮汉子不过数百,能一下子给出生口一百六十人,而且还是健康活泼无病无灾的,那可是下了血本的行为。
但这种想吃独食的愿望似乎并未得到汉安帝的认可,虽然他微笑着收下了这些生口,然后亲切地对帅升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可除此之外却再无任何表示,帅升原本期待着汉朝能像五十年前一样赐金印一枚上刻汉倭国王之类的词儿,不过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帅升走了,留下了生口,带走了遗憾,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随后,又没了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