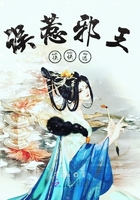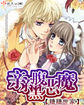乡村的冬夜,忽然“当当当”响起了急促的敲钟声。在打谷场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点燃了一堆篝火,呛人的烟雾后,火苗钻出来,跳跳的,照亮了女人的阴沉绝望的脸。女人就是小纯的母亲,小纯低着头,跪在篝火旁。等村民们围拢过来,小纯母亲也和女儿跪在了一起。
女人用撕心裂肺的哀求声音开口了:“各位叔叔大爷大婶嫂子,我生了个不要脸的闺女,她被村里的一个小伙子糟踏了,现在肚子里的孩子都五个月了。这孩子死活不说那个男人是谁,我这老脸也不要了,小纯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谁就积德,娶了她吧——”
女人说完了,人群开始骚动。妇女们幸灾乐祸,面露鄙夷之色,好像自己成了贞节烈妇,在这两个女人面前,刹时高大了。男人们垂涎地看着小纯,脑子里闪现着他婆娘无法容忍的龌龊场面。结婚的恨自己结婚早了,未婚的遗憾自己没有肇事,心里都痒得厉害。而那也许就站在人群中的两个人在想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人群散去,冬夜更加凄冷,只有寥落的星星陪两个女人瑟瑟发抖。
转天,母女二人又跪了一天,这两个神秘而胆怯的人依然沉默。
第三天也是如此。
十天过去了,没有一个男人站出来,小纯也绝望了,对那两个曾对她甜言蜜语的男人,对自己的母亲,都绝望了。后来,任凭母亲再问什么,她就是不开口了——从第一次被母亲强迫跪在场院里,小纯就开始恨母亲了。
第十一天,母女都没有露面。
过了些时日,小纯母亲在自家门框怯怯地贴了两个只有烧饼大的单“喜”字,放了挂小鞭炮。遇到乡亲,女人搭讪着解释:
“小纯嫁到河北山区啦,小纯结婚啦……”
村里一个鳏居多年的剃头匠张罗的这门亲事。
几年后。和小纯同龄的姑娘们大多已经抱上了吃奶的孩子。小纯的母亲当时也就四十多岁,由于一个人生活很艰难,就和剃头匠好上了。剃头匠的儿子娶媳妇之后,剃头匠也结婚了,小纯的母亲就搬进了剃头匠家。
据说,有一天,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来到了村里,当她告诉人们她就是小纯时,人们才从她粗糙、干涩的脸旁里回忆起昔日那个美女的一点样子。小纯哭诉着,告诉大家她嫁了个痴汉,她的第一个孩子被痴汉扔到了山谷里,她和痴汉生的两个孩子都傻呼呼的。她经常被痴汉毒打,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偷着跑回来了。好心的人们把她领到母亲的新家,小纯一见剃头匠就惊呆了,她扭头狂奔,被剃头匠拦腰拖住。
当天,就被剃头匠亲自把又哭又叫的小纯用绳子绑着送回了山里。
村里的人不知谁得知了真相:当年强奸小纯的两个男人,就是剃头匠父子俩!——当然,这只是捕风捉影的传言。
听说,小纯回去后,被一直锁在屋子里,再没有机会逃跑了。不到三十岁,小纯就病死了,痴汉家还算有良心,按照小纯的遗愿,把她送回家乡,埋在纺纱厂旁边的坟地里。
田野里的小纯的坟冢上,衰草萧瑟,寂寞荣枯。
人如庄稼,一茬顶一茬。多年过去,村子还是老样子,人却马不停蹄地完成着自己的生命过程。走完了,一切欢欣、痛苦,被黄土掩埋。逝者在人们心头被淡忘,在地下朽腐,直至剩不下任何印象与痕迹。
生命的痛苦要靠死亡掩埋,多少有些无奈啊。
瞎白话
几年前,我突然腰疼,不能扭身,憋了半口气般,痛不能寐。找到个名医,拍了X光片,说我腰椎错位。他叫来几个壮汉,绑架似的抱住我,拧水里洗出的大床罩般,想把腰椎扭过来。几个人呼哧带喘,我杀猪样地嚎叫。良久,名医也面露赧颜,打发走了众人,对我耳语:“你去找瞎白话吧,也许他能帮你。”
“瞎白话”三个字是方言,意思是一个人爱瞎说,爱胡侃。他说的“瞎白话”是一个老人的绰号。
我所居住的小城边缘,有个叫柳沽的地方,瞎白话就住在那里。我像个雕塑似的被朋友架上汽车。汽车出了城区,距离渤海更近了,呼吸有了淡淡的腥咸时,几排红砖平房便在眼前,红砖已经被海风剥蚀得没有了棱角。路边一条走驳盐船的盐沟边,一个老人手里握根短竹竿,蹲着钓鱼。朋友下车询问,我听着他们的对话。
“老人家,有个叫瞎白话的住哪儿啊?”
老人哈哈笑了:“找那个老不死的干啥啊?”
“我朋友腰扭了,找他看病啊。”
老人又笑了:“问我算问对啦,走,我给你们带路。”
走进一个破砖码成围墙的院子,老人把鱼竿、和铁丝穿着的一串海鲇鱼扔下,走进了屋子,然后向我们招手。
屋子里只有一个老婆婆,坐在马扎上,很安详地闭着眼睛。看到我们困惑的表情,老人说:“我就是瞎白话啊。”老婆婆也笑了:“你又跟别人白话啥去啦?”
让我趴到床上,老人用蒺藜般扎人的大手在我身上揉摸,他说:“我给扎扎针灸,不碍事的,就是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啊。”说完,老人点燃一只蜡烛,用烛火把银针简单消毒,看得我心惊肉跳。
晚上,我的肚子里像揣了群鸽子,咕咕作响。我开始抑制不住地放屁。屁声大而有力,连珠炮似的。我忽然想起老人说的会睡不着觉的话,心里暗自惊奇。一整夜,我都是在经久不息的虚恭声中度过的。天明时,腹内爽畅,很轻松就起床了。
我就是这样结识的这位老人。由于他就是不收我送的医疗费,逢年节,我会提着酒去看望他,他很高兴,和我无话不说,我多少知道了一些他的故事。
老人十八岁的时候,父母亡故,他加入了东北野战军。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负伤了。那个时候,他的大号叫李贵。
大约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李贵所在的连队被敌人伏击,战斗在一个山村打响。东野的战士骁勇善战,很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转守为攻,很快把敌人打散了。李贵胆子很大,为了追一个敌兵,摸黑跑了二十里,把这个敌人追得趴在地上,狗一样的喘气。当时天已经亮了,李贵用枪口顶住了对方脑壳,正为自己抓到个俘虏心花怒放,这个俘虏竟然开口了:“喂,你是贵子吧?”
李贵愣了,定睛看看,俘虏竟然是自己同村的李满。天下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
哥俩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坐在一起唠开来了。李满说自己前年闯关东,被抓了丁。李贵说自己爹妈死了后也参加了部队。告诉了李满家乡的情况,李贵忽然醒悟过来,抓起枪,对李满说:“哥哥,你是我的俘虏啊,你得跟我回去啊!”
李满忽然面如土色,扑通跪在地上:“好兄弟,你放了哥哥吧,我想回家打鱼,不当兵了。”李贵琢磨了一会,觉得也对,反正没有人看见,就点头:“那你把军服脱了,我就相信你了。”李满迅速脱下军装的上衣,扔给李贵,然后,一头钻进了旁边的高粱地。李贵拿着那件衣服往回走了十几米远,身后传来“嘭”的一声枪响,他腿一软,跪到了地上。
“兄弟,我是怕你再追我——别怪我啊——”身后传来李满的声音。
李贵就这样复员了。解放后,他不愿意当干部,自己申请到长芦盐场,当了工人。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李满由于渔民转工人的政策,和他分到了一个工区。李满整天惊惶地尾随着李贵,休息的时候,李贵白话起当兵的事,更让李满心惊肉跳。李满总抢着帮李贵干活,李贵挺感激,在李满张罗下,两个人杀了只鱼鹰,喝了鹰血,结拜为生死弟兄。几年后,李满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工区区长,李贵因为总爱说这说那,虽然有伤残军人证,也依然是工人。最让人感觉造化戏弄人的是文革中的一九七一年。李贵——这个时候已经被叫做瞎白话了——竞被怀疑为是林彪的死党,被送到杳无人迹的海边守水门,一守就是十年。他明白,这都是他义兄鼓捣的。十年间,分房子涨工资等好事都被遗忘了,他唯一的收获就是拣了个媳妇。一个要饭的河北妇女晕在了水门,天性善良的瞎白话收留女人,等大家发现这件事情,女人贴在玻璃上的喜字已经被阳光晒褪色了。
后来,瞎白话在柳沽分到两间平房,女人把自己的父亲接来了,瞎白话早掌握了捕鱼的各种手段,一年三季靠干咸鱼下饭,倒没有挨饿。瞎白话对与岳丈很投缘,亲哥俩一样,形影不离,嘻嘻哈哈。有时候岳丈就直接叫他“瞎白话”,他叫岳丈“老要饭”的,谁也不在乎,喝醉了,两个人就各自说自己的辉煌历史,谁也不听对方,都自说自话,和尚念经般。瞎白话一次扛盐扭了腰,死尸一样不能动,岳丈叹口气,让女儿买来银针,只扎了两次,瞎白话就下地了。岳丈这才告诉他自己是中医世家出身。岳丈的本领很快被瞎白话广播出去了,来求医的人越来越多,岳丈却开始闷闷不乐了。老人用了半年时间把正骨的医术悉数传授给了瞎白话,然后就不辞而别。只给瞎白话留下个字条:
尘归尘,土归土,我得回家啦。瞎白话,明年清明,别忘记给我烧纸啊。
瞎白话的女人就是那个时候哭瞎的眼睛。
时间飞快。他们这一代人快彻底退出这现世舞台了,但是,每个人的死法却不一样。那个后来从副场长位置退休的李满,在一个雨夜,一声炸雷后,心脏病发作,孤独地死在家里——他的老婆在场俱乐部正欢快地跳舞呢。
瞎白话的女人无疾而终,瞎白话给女人穿好装裹衣服,等大家注意到他,他坐在女人身边,也已仙逝多时。很多他医治过的病人为他守灵,瞎白话也算风光了一次。念悼词时,写悼词的人说,这是老喜丧,悼词里就叫他瞎白话吧。结果,悼词几次被笑声打断。
瞎白话下葬那天,我也去了,从坟地出来的半路上,忽然下起疾雨,等我们全身湿透,雨也停了。
有个人笑着说:“这个瞎白话,死了还和大伙闹着玩儿。”
人们都笑,大家也不知道哪里可笑。我也笑了——我想,反正大家都在笑,就跟着笑呗。
白叔
我少年时代生活在渤海边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那时,小镇上住着许多下放干部和在一家盐化工厂上班的工人。镇西面是周围几个农村的玉米地,东面就是汲海水晒盐的盐滩,一望无际的晒盐池阡陌纵横、水光潋滟,远远近近点缀着几座如白云般的大盐坨,晴天时,白云与盐坨相映成趣,很是好看。
汲海水晒盐,就是春天时把海水抽入盐池,经过自然的风吹日晒,海水晒成卤水,池底析出粗盐粒。所以,许多盐沟便野生了许多海鱼。这里的工人,许多都是捕鱼好手。
父亲是下放干部,也爱上了捕鱼,一来二去,与许多工人交上了朋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人与人相处也算和谐。父亲与白叔那时是要好的朋友。工人出身的白叔,大字不识,但却是个十足的鱼鹰子。白叔捕鱼本领有多大?这还真不好说,反正,不论谁和白叔一同出去捕鱼,白叔总是捕的最多。那些不会捕鱼的小镇人,谁家没吃过白叔送的鱼?
白叔、白婶都是山东人,每年回一次老家,带来的花生、大枣,总要分给大伙。平时白叔上班,白婶就在家织鱼网。我印象中,白婶家总是人最多、最热闹。白天是妇女们,晚上是老爷们儿们。山东人为人的憨厚、豪爽在白叔家体现得很充分。日子就这样单调的过,妇女们的乐趣就是到白婶家补鱼网、纳鞋底、拉家常;男人们则是喝酒、吃鱼、打百分。
白叔近三十五岁才得了个儿子。那一刻,热心肠的妇女都发动起来屋里屋外的忙。当婴儿一声啼鸣石破天惊般回荡在小院中,白叔只会裂开大嘴傻乐了。
白叔给儿子起名叫白喜。
喜子五岁时,我便领着他到镇西头的玉米地里找野菜。那时我上小学,学校常组织学工、学农,玉米再诱人,也不敢掰一个。但喜子天生胆大,回回都要偷几个。白叔白婶说不出个是非。我父亲有时皱皱眉头:这孩子随谁呢?
喜子八九岁常常纠集几个孩子一块逃学,到工厂里偷铁块铜丝。我见过他们把半个砖头缠上铜丝卖到十里外的收购站。卖了钱聚在一起偷偷抽烟。十一、二岁,他以能陪大人们喝酒、打牌了。父亲说:“你白叔太惯孩子了,有他吃苦头的时候。”
但白叔爱子心切,又没文化,并不以为然。
喜子十五岁时高低不上学了,整天游手好闲。渐渐的,白叔家串门的人少了,礼拜天大家打鱼,也不再叫上白叔。白叔打上好鱼请好友喝酒,大家也纷纷推脱,白叔百思不解,他不知道喜子发展到偶尔偷邻居家的鸡鸭到集市上去卖,大家碍于往日情面,不愿与之计较,但却避之犹恐不及了。
为人豪爽仗义的白叔便整日喝闷酒,人也就变得少言寡语。不久他退了休,好歹让喜子接了班,厂子知道白喜是个二流子,但白叔历来人缘好,喜子进厂并没有人作梗。
白叔的乐趣只有打鱼了。每天提着旋网,在盐沟边转来转去。
一个月后的一天,男人们照常上班。上午九点左右,一声巨响震得小镇的人心惊胆颤。不久,人们争先向工厂跑去。随后,就是妇女撕心扯肺的哀嚎。“出大事了!”人们暗暗转告着。
原来,上午全厂本来停电检修,有三个工人清洗乙炔气罐残液,一个青工想偷一截电线,拽掉了电闸,三个工人当场炸死,这个青工就是喜子,他安然无恙,但出事后就逃得无影无踪。小镇往日轻松恬淡的节奏突然凝重了,凝重的令人窒息。
白叔家,白叔白婶一脸歉疚、惶惑甚至惊恐的听着失去丈夫的三位妇女哭诉喜子的劣迹。
没有人再到白叔家,白叔家死寂得如同坟墓。白叔一下子苍老了,他不再出门,只是躲在家里喝酒,一个月不到,须发皆白。
一天夜里,一个妇女凄惨的哀号,惊退了人们的美梦,是白婶在哭。原来,早上,喜子蓬头垢面溜回家,被白叔带着出去打鱼,但爷俩都没回来。好心人打着手电到盐池边去找,什么也没找到。
一天、两天,连续几天过去了,仍不见父子俩的影子。一连几天夜里,人们枕边总是听到白婶的抽泣声。是不是跑回家去了?人们猜测着。直到有一天,几个人在驳盐沟打鱼,拖上两具严重浮肿的尸体。
公安局来人了,小镇又热闹了,不祥的预感笼罩在人们心头。
后来,父亲说起此事,他说,那天,老白把儿子引到盐沟边,他先把儿子打晕,用鱼网把儿子与自己裹住,然后滚下深深的盐沟。——公安局的人就这么说的。
老白这是为朋友赎罪啊,父亲说。
正是玉米成熟季节,镇西玉米地边,多了两个小土坟——白叔和他的喜子。从此,一个妇女常披头散发坐在这里织鱼网——白婶发疯了。
一年后,我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几年后,父亲回去看朋友。小镇上下放的干部全搬走了,许多新工人来到了那里。白婶已被老家来人接走,那两座坟上,早已长满了蒿草,白叔的事,已渐渐被人淡忘了。据说,那里的工人也不在打鱼,他们说鱼越来越少,有鱼的地方,已被人承包养虾了。
五万元
老方四十多岁了,在渤海边一座小县城的一所普通中学教书,工作马马虎虎,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先进称号。也难怪,他的收入不高,妻子所在的工厂一直不景气,儿子中专毕业,学了四年计算机,可是,除了会上网和美眉聊天,什么都不做,整天游手好闲。再晃荡几年,儿子就该搞对象结婚了,可是,现在娶个儿媳妇,没有十万二十万根本不行,这成了老方的一块心病,工作根本打不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