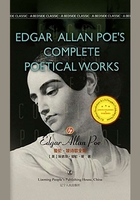邱正良示意乔新安在自己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然后说:“部机关近两年新调入的年轻干部比较多,对他们进行轮训很有必要。我征求了殷副部长的意见,他觉得现在工作比较忙,这件事最好放一放以后再说——”
“机关干部如果整天只知道忙忙碌碌,最后只能是平平庸庸。领导考察部属的工作,也不能满足他事倍功半的勤劳身影,而是要鼓励他事半功倍的办事成效。调到机关的干部大多数是从基层部队选拔上来的,总体上看素质还不错,年纪轻、学历高,工作积极、思维敏捷。但有一些人人心浮燥,好高骛远,机关和所属部队的基本情况还没有弄明白,上级领导是哪里人、有什么爱好,却了解得很清楚;谈起国际形势滔滔不绝,说起分管工作话语不多;微机上打出来的字很漂亮,手写的字与鸡爪子的脚印差不多;英语六级都过了,汉语的基本语法还没有搞清楚。”
乔新安急不可待地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邱正良听了乔新安的话,笑了笑说:“不要着急,我还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你就说那么多。提高机关干部素质,不仅是对新调入的年轻干部的要求,也是有些‘老机关’必须做的。有些老同志注重学习,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也有些老同志满足现状、不求进取,至今不会利用微机,甚至于不会上网、不会打字,写个几百字的稿子、修改几个标点符号,也要去找打字员。”
“您支持我的想法!”乔新安高兴地说。
“当然支持!”邱正良说,“机关里不管是新同志或是老同志,都有一个再学习的问题,我本人现在就觉有些跟不上形势,对有些新事物看不习惯,与年轻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利用相对空闲的时间对机关干部轮训应当作为一种常态,不但要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还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乔新安说:“您讲得对,干部的思想觉悟是要不断提高,起码不能滑坡。过去总是要求党员干部‘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以前这种革命的‘砖’特别多,可以让万里长城加长几千公里,现在这种革命的‘砖’非常少,垒几个岗楼都困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像地方人员,不愿意干了可以随便辞职、跳槽,但是在执行命令中向组织提条件的多了,什么个人的职务提升、家属的工作安排、子女的入托上学等等,到时候问题都来了。”
邱正良说:“有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和平时期不像战争年代,要讲究人性化和社会和谐。好了,这个问题就这样吧,你让职能部门写个报告,提出具体方案,下次开部办公会时讨论通过一下。”
乔新安刚要起身离开,邱正良又说:“你别着急走,有件事我还想跟你讲一下,新任部长人选的说法很多,你可能也都听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时候,你、你——”
乔新安看到邱正良欲言又止的样子,笑了笑说:“部长别说了,您的意思我明白,对这个问题,我准备坦然面对,顺其自然。有些人说,现在当官的路有很多条,找靠山这条最短,送礼品这条最快。这些话让人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要真是那样,还有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邱正良红了脸,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尊重你的想法和做法,现在的大环境有时候逼迫我们不得不违心地去做一些事情,这让人心里很纠结。”
“我很欣赏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改变不了环境,就首先改变自己;一个人如果觉得周围不够亮,就首先点燃手中的蜡烛。水围山转,兵随将走,当领导的,要为部下做表率,改变了自己,也就带动了一片,您和冯部长为我做出了好榜样,我也要为下边的人做好样子。”乔新安动情地说。
“你讲得很好!”邱正良说,“我相信上级首长会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另外,冯部长是你的老首长,也是我的老首长,有些事我无法与他相比,那是个好老头,我这几年对他照顾不够,你与他住楼上楼下,多关心他。”
乔新安点点头说:“冯部长虽然退休了,在机关干部中依然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威望不是因为职务,而是源自人品。”
“你讲得很对!”
邱正良赞许地对乔新安说。
金风送暑,树叶飘黄。
冯长平和方洁惬意地漫步在宿舍楼之间的甬道上。
走到鲍清彦楼前的时候,冯长平对方洁说:“这段时间没有看到老鲍,他不会这么早就去南方吧!”
方洁说:“应该不会,他和关大姐每年都是天气凉的时候才走,再说他们要走也会给我们打招呼的。”
“我们进楼去他家看看?”冯长平征求方洁的意见。
“不打招呼就去人家家里合适吗?”方洁说。
“我没带手机,没法先打招呼,再说去他家打不打招呼都没有关系。”
“要去你自己去,你们一见面又是山南海北的瞎聊,让别人插不上嘴,我回家接着去看电视连续剧。”
为冯长平开门的是老关,对冯长平表示欢迎的是欢欢,老关把欢欢赶到一边,朝书房呶呶嘴,对冯长平轻声说:“老鲍在里边正忙着呢!”
冯长平换上拖鞋,在书房门口看到鲍清彦爬在写字台上正摆弄电脑,便好奇地问:“这是搞什么名堂,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鲍清彦扭过头,笑着说:“不给你打招呼怎么能‘走’呢,我才七十来岁,即使排队现在也轮不到我‘走’。”
冯长平说:“我说你‘走’,指的是去南方,你想哪里去了。到八宝山去也用不着排队,真想走,加个塞就行了。”
“那不行,我一辈子循规蹈矩,在去往黄泉的路上加塞,那才是真正的晚节不保。”
“别讲废话了,给我说说,你这是在捣鼓什么玩艺?”冯长平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指着鲍清彦面前的电脑问。
“我那个在研究所工作的侄子怕我在家里寂寞,前几天给我买了一台电脑,他利用休假的时间,天天教我上网、聊天。”
小翠知道冯长平与自己是很近的老乡,给冯长平沏了一杯茶从客厅里端过来,又热情地招呼了一声:“冯爷爷好!”
冯长平很喜欢小翠,他听老关说,这个女孩子心地善良,手脚勤快,在老家读高中时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她有个读高一的弟弟学习成绩更好,是班里的尖子生。由于家里生活贫困,为了供养弟弟学习,她主动放弃高考外出打工。她每个月领了工资,除一少部分留作自己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寄给了弟弟。
冯长平接过茶杯,笑着对小翠说:“你去忙别的事吧,我和你鲍爷爷随便聊聊天。”
小翠出了屋门之后,冯长平对鲍清彦说:“你这个老东西,返老还童了,还会像年轻人一样网聊,你懂汉语拼音和那个什么、什么五笔字形吗?”
“五笔字形太难学,主要是字根记不住,我们小时候学的老汉语拼音玻、坡、摸、佛肯定也是用不上了,新汉语拼音我略懂一些,两个儿子上小学的时候,老关负责他们的生活,我负责辅导他们的学习,当时学习和掌握的汉语拼音方法现在派上了用场。我建议你也买一台电脑,有了电脑,既可以读书、看新闻,又能聊天、发邮件,老汉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冯长平不以为然地说:“天天黏在电脑上可不是什么好事,你应该多在室外活动,锻炼身体是第一位的。”
“我只是趁着侄子休假这一段时间在家里学习使用电脑,以后还要恢复室外锻炼,经常到太阳底下进行‘光合作用’。锻炼身体的重要性我当然知道,没有一个好身体,是人生最大的‘杯具’,财再多,物再广,像别人讲的,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自己住骨灰堂,老婆睡别人床,那就‘神马都是浮云’了。别看我现在七十岁了,还想为构建‘河蟹’社会再出点力,起码可以在网上交朋友、‘织围脖’,讲讲老传统,聊聊新形势,你说,我的话‘有木有’道理?”
“过去总是对有些新生事物看不惯,现在居然满口时尚名词,我这个本科毕业生在你这个初中未毕业生面前都成‘网盲’了。”冯长平笑着对鲍清彦说,“我知道电脑的作用是挺大的,听说双方聊天时还能互相看得见?”
“那叫视频,懂不懂!”鲍清彦卖弄地说。
“你可以与别人聊天,但是别用视频,要不然,别人会把你的形象录下来制成照片贴门上避邪;你与别人聊天也别通话,你当兵几十年乡音不改,一张嘴就是一股红薯萝卜味,睡觉打呼噜都是梆子腔,别人与你讲话,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还有一点,你可以网聊,但不要网恋,我听说有不少人与异性聊天聊出感情来,造成家庭婚姻危机,你要是把一个‘小三’引诱到家里来,关大姐往哪里摆?”冯长平揶揄鲍清彦说。
“我上网主要是看新闻,有时候查查资料,学习聊天也是想以后与远在国外的孩子叙家常。”鲍清彦正儿八经地说,“我这个德行,除了你关大姐,没有那个女人会看上。不像人家直政部的老林,自卫还击战时俘获了穷凶极恶敌人的一个班,跳舞厅里俘获了风韵犹存徐娘的一颗心,别人年老了脸上长皱纹,他年老了身上出绯闻。我们俩是从同一个部队调上来的,我知道他的根底,你对他可能还不太了解,他当了领导干部之后变化很大,说一句实在话,这个人不实在,脸皮比较厚,上战场都不用戴钢盔。脸皮厚的人一般都过于自信,别人对他有了意见,他依然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将来死了之后,骨灰里边都能扒拉出几粒舍利子来。”
冯长平听了鲍清彦的话,笑着说:“关大姐要是在跟前,肯定又会埋怨你,我们聊天,你总是扯上别人干什么?”
鲍清彦不服气地说:“我这个人见到看不惯的事就想说,我对老林说话也不客气,有一次我当着不少人的面,给他半开玩笑地说,老林同志要注意呢,你老婆是宫颈糜烂,你不要思想糜烂,说得他很不好意思。还有一次,他老伴向我抱怨说,老林这个人太不顾家,意思是说,老林这个人在外边不会酿蜜,还想采花。我与老林的老伴很熟,她是我和老林在基层工作时与老关同一年随的军,原来是个乡村的民办教师。我劝她说,老林在外边飞累了,就该归巢了,我希望你们老两口白头到老、长命百岁。他老伴伤感地说,我也想与他白头到老,可他总是染发;我也想与他长命百岁,可是他总让我心碎。后来他老伴也不再管他,没事了就去商场购物,你花你的心,我花你的钱。”
鲍清彦的话把冯长平逗乐了,他笑着说:“你这个老鲍可能是言过其实,我就不相信老林快七十岁的人了,还会去外边招惹女人。”
鲍清彦脖梗一挺说:“你这话讲得不对,有时候不是男人招惹女人,是女人引诱男人,关键是男人有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有些女人不在乎你脸上的折子多不多,只注重你口袋里的‘折子’多不多,以及每个折子上存了多少钱。我刚才讲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退休以后,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就好好在家呆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复杂,不要再在外边乱跑,特别是不要给别人找麻烦。还有机关第二干休所的秦霄汉,他是机关里的老人,你应该也认识,这个同志工作有魄力,能说会讲,政绩突出,但是,他退休后喜欢到下属单位和老部队去,在外边还犯过一次心脏病,住了几天医院。他对自己的身体好像是满不在乎,依然四处走动,有时还答应通过老关系帮人家协调解决问题。在职时说大话,那是餐中的响屁,退休了说大话,那是饭后的饱嗝,都不能当成歌曲去欣赏。去年冬天,阎王爷知道他喜欢到处乱跑,给了他一张去阴曹地府的旅游参观券,但是忘了给他订返程票,所以,他从总医院的急诊室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人间来。”
冯长平说:“你这个老鲍,就喜欢议论别人的不是,有些好人好事你怎么看不到,我们那栋楼的陈兴荣部长,给附近小学当了十几年的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小学生们讲光荣传统,他每年都要从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交学费,还长期资助两个山区女娃上学。徐元青副部长退休后参加了机关老年大学的绘画学习班,他开始时画的画,老虎和家猫一个样,兰花和茅草差不多,别人有的鼓励、有的嘲笑,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自己依然乐此不疲。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绘画技巧大有长进,有个书画店要收购他的作品,他说,我的画你们谁喜欢就拿走,但是不能与商品一样买来卖去。还有一个刚搬来住的老干部,我不太熟悉,好像是直属院校的教授,技术三级,他也是老年大学的学员,天天在营区的小公园里练小提琴,拉大锯一样紧着忙活,演奏水平可以为电影里屠宰牲畜的画面配音,一些从他身旁路过的人都捂着耳朵,他依然自我感觉良好地陶醉其中,他说自己的演奏水平提高了,就去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助兴。我已经给老年大学的崔校长说了,准备当个插班生,去他们那里学习书画。你刚才说有些人不该经常出去,不能一概而论,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有些人退休了喜欢猫在家里,有的人退休了喜欢四处走动,都无可非议,你不是每年也到南方去一趟吗!”
“我儿子怕我冬天在北京身体受不了,出钱给我在南方买了一套房子,那里也算是我的家,我不管到南方或是在北京,都是在自己家里,不像老林和老秦一样到别人的地盘上乱跑,给人家找麻烦。”
冯长平说:“你的有些观点我同意。我退休后就很少再到部队去,怕给人家添乱。我和方洁连城里都很少去,人老了,毛病多,容易讨人嫌,有时候你带一张热脸出去,能碰到不少冷屁股。我们俩即使出去,也是到公园散步,去超市购物,其他公共场合去得不多。”
鲍清彦听到冯长平对自己的有些话给予了肯定,高兴地说:“对嘛,老年人有时候出门在外不招人待见,有些人总是看你不顺眼,还有些人总想在你身上找点毛病出来。现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有屁大一点的权力,就可以蹶着腚乱放臭气,像我们这些退休的人,屁大一点权力没有,臀部刚一抬,就可能被说成尾气超标。”
冯长平笑了,说:“你这个老鲍,有些话说得非常刻薄,乔新安是不是跟你学的。”
“有些话说得刻薄并不是缺点,关键是看说给谁听。再说了,乔新安是你的老部下,说话刻薄是跟你学的,不会是跟我学的,这个功劳应当归于你。说实话,你有时候说话也够损人的,特别是对我。好了,咱们还把话说回来,过一段时间我还准备到南方去,你知道,老年人不抗冻,天气越冷,八宝山的炉子烧得越旺,我患有肺气肿,每年冬天去南方是想把身体养好,多活几年,给你做个伴。”
“我不指望你给我做伴,你还是给关大姐做伴吧,只有她,才能够细心体贴地照顾你一辈子。”
“你说的也对,没有她,我可能早就与秦霄汉同一个‘旅游团’走了,这几年老关经常看营养保健方面的书,一日三餐的饮食都是根据我的身体营养需要,出去购买原料,回家进行加工,好吃好喝地伺候我。除此之外,还让我早上起床后一杯鲜牛奶,晚上睡觉前一袋酸牛奶。”
“有关大姐的精心照料,有‘二奶’的有力保障,你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
冯长平给鲍清彦开玩笑说。
两个人正说得热闹,老关进屋来对冯长平说:“冯部长今天中午别走了,我跟小翠学会了摊你们老家人都爱吃的那种鸡蛋饼,你打电话让方洁也一块过来吃吧!”
冯长平站起身来对老关说:“谢谢您的好意,我和方洁说好了今天吃炸酱面,我回家去了,抽时间再过来与老鲍瞎聊。”
鲍清彦扭转上身,对准备出屋的冯长平说:“有事了给我打电话,没事了琢磨点事也给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