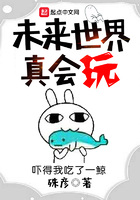朴山败讯来得太快,让天虞城内的姜素业一时手足无措。
“白宗……白宗怎么样了?”他对着探子追问。
那探子紧张得说话都气息不稳:“禀公子,白宗将军为宫让所擒,连……连同白成、贺阙二位将军,一齐投降,现留在洞庭王军中……”
姜素业彻底乱了方寸,目光茫然,跌坐在虎皮交椅上。
一旁姜鲁门、朱达二人连忙示意探子退下,又屏退左右。朱达对姜素业道:“公子,眼下须是守住天南连壁,不得有半点松懈。”
“如何守住?”姜素业竟有些丧气,“主战之将本就不多,一仗折损三员,还都投了敌,叫我如何守住?”
朱达分析道:“这是中都朝廷的诛心之计。三人性命如何犹是未知之数,没凭没据的事情,怎可轻信?依我看,他们三人忠肝义胆,断不会叛国投敌。敌人此举为的不过是动摇南国文武的信念罢了。”
姜素业这才有些缓过神来,自语道:“险些错信,犯下大错……”
朱达道:“眼下天南连壁尚有防御之力,这一带是丘陵地形,敌军虽多,铺展不开,倘若四座城池相互协防,犹能抵挡。但就怕内部先乱,不攻自破啊!”
“你是指这六道金牌吗?”
姜素业看了看桌案上陈列着的六面赤金之牌,不由有些触目惊心。
“然也。镇南将军竟然能连发六道金牌让公子撤兵,事态已不可谓不紧急。”
“决不能退兵撤防!”姜素业怒道,“我要去面见父亲,向他陈述利害,免受洛中平蛊惑!”
朱达压低了声音:“公子糊涂啊!如今南都方面的情况,如笼公超雾内,你我皆不得明,又怎能亲身犯险?”
姜素业不禁骇然:“你是说,我父亲他有可能……为洛中平所挟?不,这不可能……”
其实他心里也全然没底,这句“不可能”便讲得毫无硬气。沉默良久,他才缓缓开口道:“那该怎么办?”
朱达道:“一个字——拖。当下只能坚壁清野,伺机偷袭骚扰,以疲敌军。依我看,司隶前段时间才刚刚经历了平民叛乱、外敌入侵以及朝堂权争,百里中正新官上任,绝无持久作战的可能,若能拖到司隶先耗不住,便有和谈之机。”
“言之有理。”姜素业终于恢复了镇定,“将军临危不乱,真有大将之风。”
太守姜鲁门也接道:“我立即写信给洛氏三杰,让他们做好应战准备。”
姜素业沉吟道:“就怕他们不是和我们一条心的……”
就在此时,一员內侍在门外通报:“禀报公子,汉官仪求见公子,并说公子需要他的帮助。”
姜素业与朱达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汉官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
却说那厢公孙浒继续率军南压,并将总指挥所设置在柴坡镇。又留汉开边与徐猛二部驻扎在朴山作善后工作,表面上是让汉开边休养生息,实际上则是免得他再立下功劳。
白云儿解散了自己的手下,让他们各自逃回天虞,自己则偷偷躲在朴山一带,待到大军离去,她便趁着夜色潜入了首辅亲军的大营,直接摸向汉开边的大帐。岂料帐内空无一人,白云儿大呼上当,再想退出去却来不及,早被老刀、墨城二人拦住去路。白云儿见状,叹气道:“汉开边呢?”
“诶,还是个美女……这倒是出乎意料。”墨城道。
老刀紧盯着白云儿背后剑匣的位置,推断出对方武艺不足以威胁自己,便问道:“你来寻他有何贵干?”
“我是来讨债的。”
“他欠你什么?”墨城坏笑。
“我欠她人情。”
汉开边自帐外悠悠走来,笑着对老刀与墨城说道:“别为难她,她必是有事求我。”
白云儿见汉开边神色憔悴,忍不住问道:“你……你怎么还是这副样子?”
汉开边苦笑:“好得差不多了,不必担心。”
白云儿道:“谁担心你了。现在有个机会给你偿还之前的人情债了,你还也不还?”
汉开边道:“我知道你想救回你的两个哥哥,但是听我一句,没必要救。”
“你……”白云儿瞪大了眼睛。
“听我说,他们不会有事的。”汉开边正色道,“朝廷是不会伤害南国将领的,相反,只会加以优待。”
白云儿道:“为什么?为了笼络人心吗?可笑!无端侵入南国,不顾旧日立下的盟誓,殃及无辜百姓,还想得到人心吗?”
汉开边道:“这个问题很复杂,一时半刻说不清楚。但我可以保证,你的两个兄长现在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就在我的大营里。”
白云儿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真的?快带我去见他们!”
汉开边欣然应允,带着白云儿来到另一间营帐里,果见白宗、白成、贺阙三人坐在内中。他们尽管还是愁眉不展,但营帐内的环境却是很好,比汉开边的大帐还豪华不少,桌上酒肉果蔬一应俱全,还给他们准备了一副象棋,供他们解闷。
“哥哥!”白云儿见到至亲安然无恙,心头大石总算落地,再也抑制不住情感,飞扑到白宗与白成身边,眼泪连珠般滴落,哭得梨花带雨,叫人好不心疼。白氏兄弟见妹子出现在此,惊讶不已,白成一时语塞,还是白宗先开口道:“妹子为何来到此间?难道你也被捉了?”
白云儿摇摇头,擦了擦泪,说道:“不,是我找汉开边……”
白宗叫苦道:“你怎可自投罗网啊!你这一来,还能走得了吗?”
站在门外的汉开边冷冷道:“只要她想走,随时可以走。我不会为难她的。”
白宗看着汉开边,羞愤难当,道:“你休来假仁假义,想哄骗我投降!”
汉开边冷笑道:“你投不投降和我关系不大,我只是代为看管俘虏而已,对朝廷而言,你们也没什么利用价值。”
白宗涨红了脸,怒道:“前番真该将你擒杀,我家妹子就不该把你放了!”
汉开边道:“我也感念你家妹子的恩情,所以,你们现在毫发无伤,吃的还是我军营里最好的酒食。”
贺阙怒道:“谁稀罕你的酒食!”
墨城听了,讥笑道:“那你倒是别吃啊,就你吃得最多了。”
贺阙气得两眼圆睁,直欲扑出来杀了墨城,但脚上挂着铁镣铐,哪里走得出来?墨城又瞥了白宗一眼,笑道:“还想擒杀汉将军?若不是汉将军心存仁念,你现在还能在这大放厥词?”
白宗一口气被噎住,嘴里半天憋出个“你”字,又像皮球泄了气似的,没了下文。白成则一言不发,他觉得没有面子,却又不想逞口舌之利,当下有些灰心,只顾着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紧紧攥住白云儿的小手,以庆幸一家人尚能团聚。
真正经历过战乱的人,总会特别珍惜亲情。
白成想起了多年前就因战乱而失散的小妹,也不知她流落到了何处,心头一酸,不由得叹了口气。还好,大哥和云儿还在身边,还好,自己仍能牵着妹妹的手。他甚至有些埋怨大哥,怪他还有心思与汉开边斗嘴,败军之将,何足以言勇?
白云儿终究是女子,心细如尘,察觉到二哥的异样神色,便对白宗说道:“都别吵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说?”
汉开边道:“你现在确信他们没事了,可以选择回南都去,我会给你一匹马;也可以选择留,暂且在此住下。”
白云儿听了,笑道:“留下?难道你不怕我找机会把他们救了么?我终究是你的敌人,你就放心我留在这里?”
“哪有什么敌人?”汉开边道,“我们都是大国州人,都希望停战,为什么会是敌人?”
“巧舌如簧,你这个人太可怕。”白云儿皱了皱眉,“我想,你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吧?”
汉开边笑道:“果然瞒不过你。”
“可你还欠着我两个人情,不想着还,反要再欠一个?”白云儿道,“你的脸皮也太厚了。”
“这件事关乎我的性命,你必须帮。如果我死了,百里丞相就失去了代理人,也就没人能再限制住张时。风火连城破金阵,便是张时的策略,他可是打算一把火把你们烧个干干净净的。我想,你应该对此有所理解。”汉开边道。
白宗怒道:“你这厮又想耍什么阴谋诡计?”
汉开边道:“你们连朝廷里谁主战、谁主和都不知道么?百里丞相不希望战争继续下去,而经略王却相反。我和张时分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介入南国,自然是皇帝的意思,他希望取得一个平衡。但现在,有人一直想暗杀我。”
白云儿点头道:“这个我可以证明,而且派出的杀手是荆棘榜排名第三的失梦人,武功奇高,极难对付。”
白宗是知道这件事的,而白成与贺阙也听说过失梦人的名号,登时讶异不已。
“他已经对我发动了第二次袭击,若不是身边有老刀在,”汉开边的目光投向一旁的西门仰,“我这条小命就没了。”
白家三人与贺阙一齐朝老刀看去。白云儿惊道:“将军竟能对付得了失梦人?”
老刀淡淡道:“只是把他拦住。若要殊死搏斗,老夫没有必胜把握。”
南国诸将骇然。汉开边这一番话,除了巧妙辩解以外,还着实有些炫耀武力的意味。白宗等人暗自思忖,能抵挡住失梦人的老刀,该是有何等水平的武艺?
“张时一心要在南国建功立业,丝毫不顾生灵涂炭。若我在,尚能尽力让事情不走向极端。若没了我,张时怕是不计一切手段也要倾覆整个镇南将军府。”汉开边道,“到时候,你们就真的没什么存在的意义了。”
白云儿最终选择了留下。
兄长在哪,家就在哪,即便回去南都,她又无军衔官职,能有什么作用?
汉开边心下竟有一阵窃喜,甚至有些佩服自己胡说八道的能力了。他自然是希望白云儿留下的,因为几次接触下来,他对白云儿竟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产生了一种久违的情愫。但对于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来说,这种感情实在太过珍贵和脆弱,因为纷纷扰扰实在太多了些,要考虑的事情也太多了些。汉开边回首看了墨城一眼,忽然油然生出羡慕之意,墨城这个年纪,正是可以大胆热烈地表达爱意的时候,而自己却早已有些患得患失。
“如若官仪现在在我身边,怕是会狠狠地嘲笑我一番哟……”汉开边如此想。在他看来,汉官仪必然会指出,他是为了借金阵对付失梦人才留下了白云儿。
还好现在汉官仪并没有闲工夫管这种事。
他正端坐在姜素业的面前,神气沉静,等着对方先开口。
“先生,你到底能怎样帮我?”
姜素业这开口一问,便打开了连环计的最后一环。张时、汉开边、汉官仪三人的奔波劳累,为的就是最后这一环。
驿馆外是久违的明媚春日,南国的微风穿过厅堂,摇晃着茶杯上方的水汽。
汉官仪表情严肃,道:“公子,我是南国人。”
“当然,这个我当然知道。先生是韩城人,当然是土生土长的南国人。”
姜素业隐去了自己想到的另一层意思——韩城人轻农重商,多出富贾,热衷于交易。
“作为南国士人,我怎可坐视南国倾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