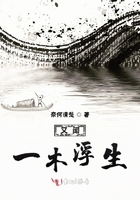他们的车出了哥大校区,达卡奇说,康,上我那里坐一会儿吧,有些事想跟你说。
车上说不好吗?
他摆了下头,眼睛看着前方,为了你的安全。
好吧。她微笑地看着他。
我们已很久没有单独聊聊了,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没有机会让你知道,达卡奇眼睛仍然看着前方,因为我不想干扰你,为的是让你顺顺利利戴上博士帽,这是你的心愿。
沫若的内心很享受。她为有这样一位挚友而欣慰,公司虽然打着她的名字,可她却一直没有时间来打理,资金是他的,管理也是他在顶着,到底经营得怎么样,她也不知道,她这两年一直忙于她的科研立项的工作,圈内人都知道,考博容易,毕业却很难,要想不被那些学术权威难倒,得到他们大多数人的肯定,不下真功夫没有真本领是过不了那一关又一关的。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别的事。他们很少见面,更没单独交流和沟通过,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她也一无所知,她跟亚拉他们也顶多发发短信,也没深聊过。她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点了下头说,我知道,真难为你了。
他们继续前行,没有再说话。沫若突然感觉到车子是向她的新住处方向行驶,便说,你改变主意送我回家哪?
不是的,是去我家。我搬了家,离你的住地也不远。
沫若并不知道他与艾丽斯之间发生的事,也不知道他从家里搬出来了,觉得惊讶,她跟亚拉他们去过他家,那是有前后院的宽敞别墅,在曼哈顿算得上是豪宅,价值有数千万。他为何要从那里搬出,有些不解地望着他,很想问,这是为什么。可她知道,美国人把那些属于个人的事称作隐私,不乐意别人窥视。这是他们的习惯。如果他觉得应该让她知道,就会主动地对她说的。她不去问他这是为什么,是对他的尊重。就在她心里这样想的时候,车子减速转弯了,不一会儿停在一幢二层别墅的院子里。他先下车,为她拉开车门,到了,下来吧。
她从车上下来,走到院中一棵她叫不出名字的大树下,打量起他的新居来。从外表看,这房子八成新的样子,有条宽阔的水泥路通向门前,路的两边,种有一种类似波斯菊样的草本花卉,像两条五彩绸带,在秋天的阳光下开得很灿烂。草坪修剪得很匀整,没有高大围墙,只用涂有白色涂料的低矮木条随意地圈了下,算是势力范围的标记吧。他走到她的身边,伸出手臂挽住她的肩,看什么呢,进屋吧。
他把她带到门前,开了门,亲昵地对她说,请吧。
她对他微微笑了下,就走在前面。
他顺手关上门,拉着她的手,我领你参观一下。
艾丽斯不在家?她仍然笑盈盈。
他停下步子说,你不知道我和艾丽斯之间发生的事?
她摆了下头。
亚拉和斯蒂文没有告诉你?
她又摆了下头。
我们边看房子我边告诉你吧。
她点了下头。
他牵着她的手从偏门下了三级台阶,下到有一亩大小的内院。内院花木扶疏,还有一个游泳池。他们绕过泳池,走到房屋的东边。
这房子设计独特,没有高大气派的门头、威严的大门和门厅,也就是普通的双合门,内院三面环绕。进门就是大客厅,开有几扇门,两扇通向院子。他挽着她边讲他和艾丽斯的悲欢离合,边带着她环绕院子从东面的门回到厅堂,偕着她走上旋转楼梯到楼上,参观他的书房、卧室和小会客厅。他们在小客厅坐下,从冰箱中拿出一瓶甜橙汁递给她说,将就一点吧,这家里没有女主人,打理花园泳池的事交给一家家庭服务公司,定期有人来打理,室内的清洁工作有人每周两次来清扫,我只是晚上来这里睡个觉,白天几乎都活动在外面。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男无女不成家,女无男不成室”,我这个家已不像个家了,没有一点人气。他很想说,我多么想你来做这个家的女主人啊。可他没敢说出口。他记得那次她的话,害怕再次遭到她的拒绝,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他深情地注视着她的眼睛,你不怜悯我吗?
她爱嗔地瞪了他一眼说,你这是自找的。好好的家,为什么要打碎呀!
他对她做了个苦笑,又摇了下头说,我想对自己好点,不想时时被人窥视,离婚对我来说,是对自己的爱。你应该懂的。
她无声地叹了口气。她不愿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就转向工作上。她说,你发来的策划书我读了,赞同你的构想,开办汉语培训班的提议太好了,我也有这个想法,不但可以让想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人有一个学习机会,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可以开办日班,还可以开夜班。我们早就有请一些中国当代的着名作家来参加一些交流活动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条件有限,一次只能请一两位来,先请和我们有过合作的人,我们出版了浮云的两部书,应该先邀请他,他的《花都》刚刚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我们再加印一版,加上这条新闻,肯定能让销售上个新台阶,或许会再次上榜。如果你也赞同,等我父母回去后,我就全力来做这件事。
这也是我的想法。
太好了。她喜形于色地说,我们再陆续选些书来做评估和市场论证,继续翻译出版中国小说和学术研究着作,还可以与中国的出版机构合作,把美国和欧洲的新锐作品介绍到中国去,把我们的事业逐渐做强做大。她充满向往的看着他,我们的俱乐部就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美文化交流的平台,两国读者相互了解的一扇窗户。美好的憧憬让她心驰神往,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靠向了他的肩头。他们的身体刚一挨近,在他的心里立刻放射出电石火光,像被电击了似的,他的手臂像接通了电源的电棒,紧紧控制了她的身体,强烈的电流击中了她,她的心脏狂跳起来,她的头深深地埋进他的胸前,他情不自禁地拦腰抱起她,把她抱进了卧室,放到了他的床上……
他们彼此相爱了很久,可是,阻碍着沫若的是心理因素。她不相信爱情,更不相信婚姻,但她却不是个禁欲主义者,因为她在心底深处喜欢他,她就特别害怕坠入情网,害怕又要重蹈覆辙,因而她尽量要远离他,那次在菜馆听了他的表白,她一下吓慌了,她连忙表述了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这之后,她尽量不与他单独接触,有事要商谈,除了电话和短信,就是通过邮箱,要见面也尽量趁有他人在场的时候。他们这两年合作创建的“康沫若中美文化交流俱乐部”,出版了六七种书,开展了很多活动,她都想办法不让他有任何与她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她信不过自己,因为她喜欢他,只要有机会,她可能就管不住自己,他们之间就会发生她不想发生的事,她的心很矛盾。害怕和渴望常常交织在一起。有了心中的这种绞杀,他们之间一直没有走到这一步。可今天,她和他在他的新居里,她修筑了多年的堤坝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崩溃了。她忘了她的坚守,她的恐惧,她的忌讳,不和她最爱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她可以不拒绝和亨利做爱,因为那只是生理的需要,没有心理负担,可她今天跨过了这道门栏,踏破了她心中的禁区。当她从快乐的天堂回到现实的地上的时候,她害怕了,她立即对他说,达卡奇,你可别对我存有婚姻的幻想啊!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不想再结婚,我不信任婚姻,也难相信长久的真爱。
达卡奇搂住她的颈项,含情脉脉地看着她的眼睛,没有认可也没有否定,只说,你真是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很多女孩子都希望用婚姻来把自己爱的人圈住,你却不要婚姻。
爱不会一成不变的,世间难得有永恒的爱情。一旦爱消失了,有婚姻还有什么价值?婚姻就会变成伤害彼此的锁链,而我也不能保证一生就只爱一个人。没有婚姻,就没有了禁锢自己的樊篱,我只要爱,不要爱以外的东西。对你没有爱以外的任何要求,你不用有任何精神和心理负担。
他向她俯下身去,用他的唇堵住她的唇,接通了激情电流的身体又一次难解难分地绞扭在了一起……